撰文丨镜陶
近日,青年作家林培源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和作家张忌的小说《南货店》出版。两位作家都是南方人,新作也都聚焦南方地区的风土人情。
两位作家为什么都在自己的小说中不约而同地花费一定篇幅来书写家乡美食?这和情节安排、人物命运有什么关系?故乡对他们的写作生涯意味着什么?如何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南方地区的方言并照顾听不懂方言的读者的感受?
8月15日下午,林培源和张忌做客上海书展大方现场分享活动“我们对‘南方’一无所知”,探讨了他们的作品与南方风土人情、文学记忆的关联。

活动现场。
对食物的书写,与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相连
林培源新作《小镇生活指南》中收录的作品,大多都写于2012年到2017年,故事大多发生在他家乡的一个小镇上,聚焦了一些小镇生活中比较底层和边缘的人物,有守庙老人、养蜂人、失独父母等。
林培源在十八岁之后,才离开潮汕小镇去外面读大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潮汕印象往往与潮汕美食相关,比如说潮汕砂锅粥、牛肉火锅等,但让他更有感觉的是当地的人际关系。潮汕有很多祠堂、榕树和池塘,也是一个非常鲜活的礼俗社会和乡野世界。后来他常年在外读书,去过深圳、广州、北京、美国,地理距离与故乡越来越远,发现自己的潮汕口音也在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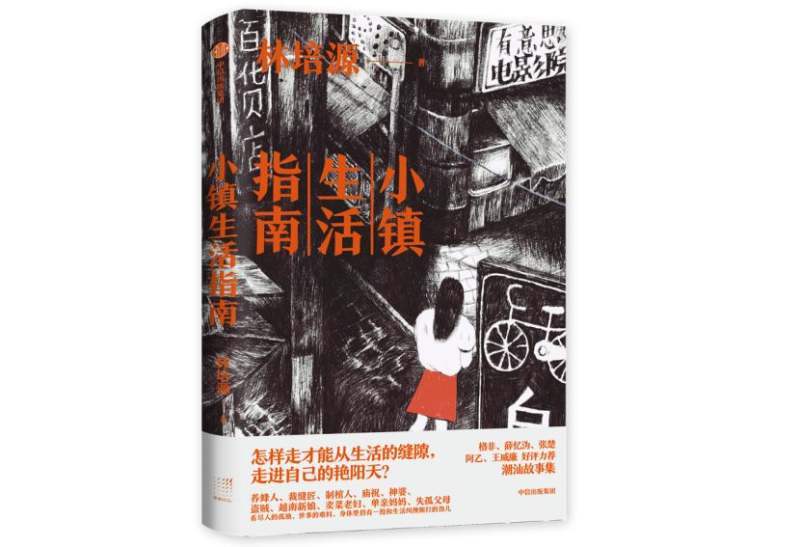
《小镇生活指南》,林培源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
张忌的《南货店》则书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故事,那时候大概他只有十几岁,这是对于父辈故事的追寻。《南货店》中的美食描写值得讨论。张忌提到,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人们从物质匮乏的阶段进入了物质丰富的阶段,食物匮乏的记忆一直缠绕着他的父辈,因此相对于物质生活丰富的当代人,过去的人对食物有一种特别的热爱。他提到,书中有多处对食物的详尽描写,跟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书中杜英的妈妈生了两个女儿,而老公的兄弟生了三个儿子,在给女儿办婚宴的时候,她觉得要把面子挣回来。于是作者张忌就安排了很多描写婚宴饭菜的内容,这和人物的心理是有关的。还有齐师傅,他在特殊的年代里经常被批斗,回来的时候每次都要自己吃一顿饭,这顿饭可以说是他在遭遇挫折后对于自己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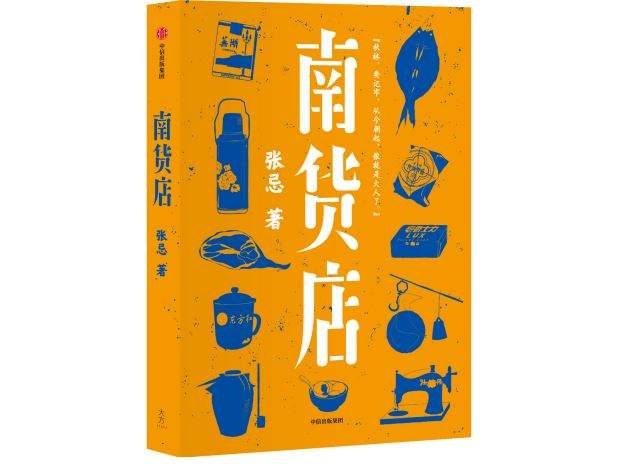
《南货店》,张忌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
林培源对张忌在《南货店》里的食物、宴席描写很有感触。中国传统小说也非常重视食物描写,比如说《红楼梦》和《金瓶梅》。长篇小说更有足够的空间让作者详尽写吃穿用度,能够提供一些舞台去盛放这些东西。但是在中短篇小说里,很难有这么大的空间写闲笔,因为要照顾到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和人物命运的走向,看到有关食物的描写,那一定有作者的用意,不可能像长篇小说那样花巨大的篇幅去渲染。《小镇生活指南》中有一篇小说《最后一次“普度”》,当地有“普度”的民俗传统,他写了其中卤鹅的过程,卤鹅的老式做法是把鹅泡入松香里褪毛,然后用镊子把褪不掉的毛夹掉,卤鹅工也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充满矛盾的故乡,有时会成为推动写作的动力
林培源提起自己第一次离开家乡的经历,大概在1995年还是1996年,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从镇上去深圳姑姑家过暑假。那时候交通不便,香港回归之前去深圳还要边防证。父亲和他一起坐在大货车的驾驶室里,从下午坐到晚上才到深圳。他和父亲的普通话都不好,司机很难听懂他们俩要去的“罗湖”,因为他父亲发音是“罗服”。
来到深圳后,他发现深圳有一个很大的书城,而他家乡连个书店都没有,因此,他的文学爱好和这次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林培源从上高中时开始写小说,那时候的写作都是从阅读开始的。在那个阶段,他最喜欢的就是卡夫卡的小说,他在学校的图书馆看见了一本《变形记》,他根本不知道卡夫卡是谁,更不知道卡夫卡的文学史地位,他经常下晚自习后蒙着被子在宿舍读《变形记》,不好意思跟室友说自己开夜车是在读小说,就说是在看教材。他第一次写作的教材,就是他最早阅读的文学经典。
直到现在,林培源和故乡的关系还是很矛盾,他对故乡又熟悉又陌生。去了大城市以后,他决定以后要好好读书,走出小镇。但是,选择了文学这条路后他又发现,虽然他在不断远离故乡,但又在不断用笔墨书写故乡。故乡是一个特别矛盾但立体的存在,这种矛盾带来的张力,反而在推动他的写作。

林培源。
林培源表示曾经读过张忌的小说《出家》,感到非常惊喜,还特意写了一篇评论。在《出家》当中,张忌还是在用非常标准的现代汉语写作,等到了《南货店》,他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宁波话,即使不懂宁波话,也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鲜活气息。
另外他提到,张忌的《南货店》对所谓的先锋文学或西方现代主义有一种反叛,他的背后有庞大的资源,首先是民间的叙事传统,包括习俗、食物、婚丧嫁娶等细节,活灵活现,有生活气息;第二个资源是,张忌在古典小说里找到了写小说的动力和燃料,比如《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等。这些小说作为燃料提供了巨大的能量,涉及的人物关系很庞杂,但读的时候,不使人觉得繁琐,反而会感到人与人关系的紧密,人物并不会突然出现,随后消失。这是非常正宗的中国小说的叙事。

张忌。
林培源在回应编辑有关“小说家残忍又仁慈”的问题时,以《南货店》作为例子,指出小说当中有两个写到死亡的情节,第一是小说写到齐师傅,他的大儿子并不是他亲生的,他和妻子两人不能生育。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跟齐师傅之间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父子关系。小说写到,他犯了流氓罪,判了死刑,张忌并没有写齐师傅的儿子齐海生死亡的过程,但是他用很多的笔墨写齐师傅怎么给他收尸,写得非常细。读者能感受到齐师傅溢于言表但又隐藏文字后面的悲痛。
张忌不会在书写死亡时,告诉读者这个人死得多么悲惨,他的写法隐忍又克制,背后又有情感的力量迸发,但处在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这很符合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第二段关于死亡的情节,是写到杜家妈妈的大女儿杜梅,她与丈夫的婚姻破裂了,又回到年轻时的裁缝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杜梅是一个非常好的裁缝,当时以为可以靠这门好手艺,一辈子衣食无忧。她用的料子很好,很多人都到她的裁缝铺买衣服。离婚以后,她的生命失去了光彩,引以为傲的手艺也逐渐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后的成衣店越来越多了。她想不开,属于她的时代和婚姻都结束了。
在她准备结束生命之前,张忌花了很大的笔墨写她怎么用店里剩下的布料做衣服。后来,杜家妈妈给杜梅送吃的,到裁缝铺的时候,门一推开,发现她吊死在裁缝铺里了。她做的衣服,被风吹着在飘荡。这种写法举重若轻,有一种“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失落感。林培源认为写小说有技巧,也是有法度的,有些时候就是“言有尽意无穷”。一些小说创作者的经历或经验有限,难以掌控小说的节奏,详略不得当,这样的写法很破坏小说的美感。
把南方方言大量用到小说写作中,有很大困难
张忌谈到自己为什么喜欢写作南方的民俗文化时说,早年的阅读经验对写作影响巨大。他早年喜欢读连环画,这也与他后来喜欢古典文学有关。他之前就很想用古典文学的语言来写作,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落脚点,所幸他是宁波人,宁波方言相对还是能落到文本上的。
林培源表示,在我们的汉语发展史上,现代标准汉语跟方言之间有很大差距,我们从小接触的语文教育基于一套现代汉语规范。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这种规范性会过滤掉很多非常鲜活的方言词汇。我们读金宇澄老师的《繁花》,或者是读一些古典的小说,会发现里面用了方言。比如读《金瓶梅》的时候,很多的方言词是通过注释才能了解的,但我们能感受到当时人物说话的腔调和语气。读《南货店》的时候,他很羡慕张忌的一点在于,张忌生活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只要经过一定的文学处理,就很容易进入到小说当中。
但是作为一个潮汕人,要把潮汕的方言用到小说,就会面临巨大的障碍,很多方言俚语没有对应的汉字。他只能做一种综合调配,涉及叙事部分就用通行的汉语,涉及到对话时,就模仿人物说话的语言、语气和腔调,用一些方言词。如此一来,小说读起来会形成陌生化的效果。读者不一定懂这种方言,可是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妙的阅读体验。
对于当地人来说,不论是阅读《小镇生活指南》还是《南货店》,都可以用方言把人物对话读出来。如果我们把方言文学的范围再扩大一些,去读马来西亚华语作家(比如黄锦树、张贵兴、李永平等作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使用的方言也是综合性的,他们把带有强烈的南洋气息的语言放到小说中,给人以一种非常生猛的南洋的野性体验。林培源当时就想,南洋比潮汕更加南方,他们能用方言去写作,那么作为中国大陆的作者,自然也可以尝试在写作中大面积使用方言。如果以后他再写长篇,也会尝试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历史、社会、人物的书写。《小镇生活指南》在这个层面,可以看成是他漫长的学徒期的作品集合。
撰文丨镜陶
编辑丨董牧孜 罗东
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