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平时会关注我们发表的一些书评吗?”
“现在谁还会看书评啊。”
作为书评编辑的从业者,不止一次从类似的对话中感受到尴尬。的确,现在读者们不是很需要书评了,他们有很多渠道能够选择新书,看看内容简介、宣传文案,感到有兴趣的就可以下单购买。除了少数对书籍内容关注的读者、业内人员、出版社编辑,外加我们编辑自己,没什么人在乎一篇书评的内容究竟怎么样。
曾经有很多读者在乎书评吗?
有的。或许就在四五年前,读者们还会从一篇媒体书评中感受作者思想的魅力,小说中引人入胜的才华,了解某段历史的扑朔迷离与某本艺术书为我们带来的新视野。但不知何时开始,书评开始逐渐远离了这个航线,它就像条驶向孤岛的船,硬着头皮驶向某个崇高的目标,却没注意到船上已经不再有人。
很关键的一点是,在今天的媒体书评里,我们基本见不到什么生命力了。因为一篇优秀的书评,必然要经历生命的消化,而后从自己内心的体悟出发描述它带给自己的感受。但现在的书评,几乎都是在作者们既成的语言框架中打转,没有思想的突破,也缺乏活泼亲切的风格。书评不是在与读者对话,而是在作者自己的语言和框架中做反反复复的瑜伽拉伸。
在书评冷落的时期中,不太能理解的一点还有精英解读者所做的“筛选”工作——“看不懂的话就回去补课”“理解不了就多咀嚼几遍”,诚然,很多书籍的确有着深刻的、不可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清的思想内涵,然而,如果上来就抱着这种提升读者智性和学术涵养的目标,那么大学教授或论文期刊会是更适合他们出现的位置。可以说,正是许多文化媒体刻意地提升内涵、提升读者素养的思路,在完成他们所期待的“筛选目标读者”的同时,也让书评或文化评论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生硬与疏远。
或许有人会说,很多哲学与社科书籍本身便有很高的门槛,需要啃着读是学科决定的。但是,本应向读者敞开的、以讲故事方式写就的文学作品,它们的评论也变得越来越僵硬,原本清晰可读的小说,反而在一篇评论中变得模糊不堪,趣味全无。
文学评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好的媒体书评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带着这些困惑,我们与文学评论家刘剑梅进行了一次对谈。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宫子

刘剑梅,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之女,香港科技大学文学教授。在新出版的著作《小说的越界》中,刘剑梅尝试回归文学审美本身并提出“越界”的观察视角,阐述小说如何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探讨不确定的边界、如何以讲故事的方式完成对社会权威与传统现实的挑战。因此与传统的文学评论集不同,《小说的越界》放弃了学院派的论述,用平易近人的口吻评论小说中的艺术魅力,收录了大量对当代小说的观察与剖析。
新京报:现在阅读书评的读者越来越少,你觉得问题主要是出在读者身上呢?还是出在媒体书评身上?
刘剑梅:我认为现在出现在媒体上的书评,总体来说,还停留在表层,也就是停留在大量的作者生平介绍和作品的内容概述上,还没有深入地对文本进行分析,或是还没有对文学传统和审美形式进行更多精彩的梳理和评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其作用就是把读者引进“阅读之门”,让我们把眼光投向一些以前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作家。只不过,我觉得许多关于作者的生平介绍和作品的内容概述的信息,在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寻找到。所以,除了信息以外,我会更期待“思想”能够带着充沛的活力浮现出来,直击我们的心灵。另外,我觉得,媒体上的文学评论还不够有力度,没有发挥批判、打击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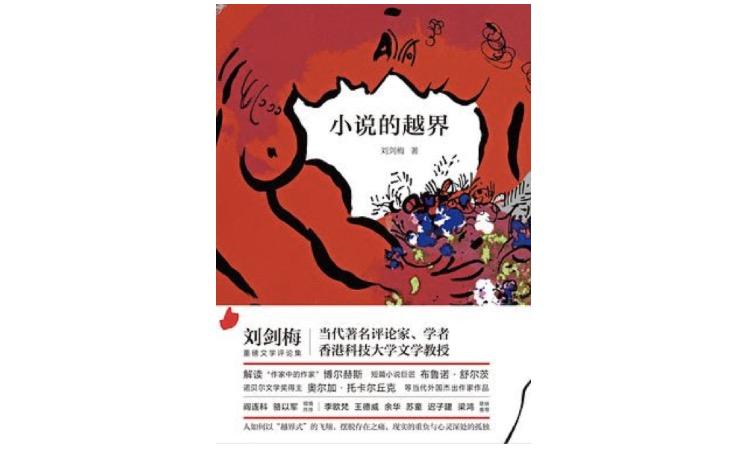
《小说的越界》作者: 刘剑梅,版本: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2020年8月
新京报:这种有力度的打击会得罪很多人。这个也和当下出版业、作者、书评者形成的圈子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作为文学评论者,你如何看待这种圈子文化?
刘剑梅:文学批评当然要有距离,那就是文学批评者应该跟当下的文学交际圈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敢于批评,不让友情和人情世故影响自己的文学判断能力,保持文学家的尊严。文学批评始于距离,有了距离,才会讲出真话,不被作品之外的因素干扰自己的文学直觉和判断,所以要做“文学中人”,而不是做“文坛中人”。
其实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形之中就包含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品格,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淘汰,过了多少年依旧还是“经典”,并不是靠“文学交际圈”的肯定而存活下来的。

《纽约书评》封面
新京报:另外还有个问题,不局限于表层的书评内容又通常晦涩难懂,很像一篇大学里的小论文。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它们非常吃力——没人愿意每天早晨起床后读一篇小论文。
刘剑梅:正如你所说的,今天的文学评论遭遇了一种尴尬,那就是在学院论文和向大众读者推荐的宣传广告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学院派的文学研究方向出现了偏差,在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那就是学院派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批评,各种主义和概念先行,却忽视了文学作品内在的美学特征,比如讲故事的艺术,文学的超越性等。
学院派的文学批评现在已经自成一体、自说自话,与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似乎完全不搭界。这种理论先行的批评,往往是对文学艺术的冒犯,有“削足适履”之嫌。我内心对这类粗暴的“政治”阐释或过度阐释是排斥的。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一篇评论应该起到什么样的功能?
刘剑梅:文学批评的功能其实很多,有阐释、品味、介绍、推荐、估量、批判、打击等功能,也有提升、教育的功能等。好的批评家能够发现和开掘文学作品的亮点,有一双天生的慧眼,有独特的文学感受力,就像别林斯基肯定果戈理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决定性地位,夏志清先生把张爱玲提升到跟鲁迅并驾齐驱的地位一样。文学批评的批判功能也很重要,比如对于一些污淫诋毁的下流作品,就必须打击和批判。

《文学回忆录:1989 - 1994》,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新京报:哈哈,有人这样做呀,比如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既有见地,也有温度,嬉笑怒骂。可批评他的人也不少,说他过于随性主观的评论完全是偏见,不是真理。(抱歉我不得不使用“真理”这个词)
刘剑梅:我个人很欣赏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一是因为他的学识极其广博,知识面覆盖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试问当代中国能有几个文人拥有他如此博大的世界视野、深厚的学识和宽广的人文胸襟呢?二是因为他纯粹献身艺术,多年积淀下来的文学艺术直觉极其敏锐,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真知灼见,常常一语道破掩藏在事物后面的真相。
当他娓娓道来全世界各地的文学经典时,你会发现他其实在那么多跨越时空的评述中,后面有一个厚实强大的精神上的血统,比如古希腊神话、耶稣、老子、庄子、杜甫、陶渊明、拜伦、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哈代、尼采等都是他文学艺术血脉相连的“亲人”。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血统,他只言片语的评价如点穴一般,直中要害,哪里还需要什么大的系统来支撑他的论述啊?
何况他在书中一再表述,他非常反对体系。读懂他的人,马上心领神会,知道其中的妙处,而且激赏不已,如遇见多年寻找的知音朋友一般。我很喜欢他的主观随性的论述,但是这样的论述,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因为那些中外一流的文学经典不仅要通读,而且要反复读,才能有这些独特的感悟。这是完全无法复制的。他的直觉不仅跟天生的艺术气质有关,而且跟他多年积累的文史哲功底有关,别忘了他对着陈丹青们讲世界文学史课程的时候,已经六十七岁了,不仅阅读了无数的书,也行了万里路,体会了多少起起伏伏的世态炎凉。倘若文化底蕴不深的人,随意去模仿木心那种主观、直觉、随性的表达风格,很可能只是“妄议”,有被人嘲笑成“妄人”的危险。
新京报:所以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评论的“话语权”问题。木心可以这样做,纳博科夫可以批评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布鲁姆或斯坦纳可能就更权威了,但如果一个普通读者——哪怕是很有造诣的读者——说出类似的话,就会被视为浅见。
刘剑梅: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文学评论一定存在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专业的“文学评论家”,学院派的文学教授有“话语权”,你们《新京报·书评周刊》有“话语权”,世界级的作家纳博科夫就更有“话语权”了。但是,拥有“话语权”,并不意味专业评论家的文学评论和判断就一定代表“真理”,就一定比业余的批评家——如普通的很有文学造诣的豆瓣读者——更接近“真理”。

《小说的艺术》,作者: [法]米兰·昆德拉,译者: 尉迟秀,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5月
其实,在文学世界里,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文学有宽广的慈悲心,去面对一大堆相互矛盾的不确定的真理,就像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经说过,“一个建立在唯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唯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寻,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
正因为此,文学批评的角度也一定是多元的,可以有各种阐释的角度。最可怕的就是树立唯一的“权威话语”,或是把文学批评纳入一个既定的固定的意义体系,那才是最大的“陷阱”。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知识体系和文学创作理念基础上的阐释和判断,我们可以认同和参考,也可以质疑。普通的豆瓣读者,在网上其实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有“真知灼见”,那就非常可贵。
新京报:同时直抒己见的批评还有另一种危险,它有可能真的是不客观的。例如《纽约时报》角谷美智子对作家诺曼·梅勒的批评一样。

角谷美智子在诺曼·梅勒每次出版新书后都会攻击作家是个粗俗的野蛮人,而梅勒也回击美智子是“神风特攻队队员的后代”。
刘剑梅:当然,这又涉及到批评标准的问题了。比如你举的例子,《纽约时报》的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批评诺曼·梅勒的小说《圣子福音》是“一本愚蠢的、自以为是的、漫不经心的漫画书”,确实有失公正。梅勒的《圣子福音》是对《圣经》的当代阐释,把耶稣“人性化”,让他在被钉上十字架时,在内心深处徘徊于善与恶之间。对于这样的耶稣“人性化”的当代重构,詹姆斯·伍德反而认为颠覆的力度还不够,而其他批评家如厄普代克则肯定小说中耶稣“平静”的声音和小说朴实的叙述语言,认为其中内含一种颠覆性。
的确,批评家评论一本新书肯定存在着危险性,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个人偏见的陷阱,这样的例子很多,这跟每位批评家选择的批评角度和立场有关。就像鲁迅评《红楼梦》时,曾经说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批评家的批评立场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但是如果从这一个视角出发,过度阐释,就会出现偏差、偏见。苏桑·桑塔格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批评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才会服务于艺术作品,而不是僭取其位置?”她主张批评家首先要恢复我们自身的感觉,以及自身的感知力,去体验事物自身的明晰。

《纽约时报书评》封面
新京报:评论时的感知力的确特别重要,那么,理论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刘剑梅:关于思想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那就太复杂了。文学批评家的身后如果没有思想理论支撑,会显得比较没有底气,所以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有各种流派,琳琅满目,比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可惜,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往往过于崇拜文学理论,反而走了歪路,本末倒置,很多研究文学的学者完全不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只关心如何拿文学作品来论证这些理论,经常断章取义,人云亦云。
我个人觉得文学批评家与其读那么多时髦的文学理论,还不如多读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大量阅读世界和中国文学经典,这样才能获得广阔的视野,对各个国家的文学传统了如指掌,所谓敏锐的文学直觉其实是靠大量的阅读积累下来的。另外,除了阅读作品之外,文史哲的经脉必须打通,这样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才有可能带来一种富有感染力、原创性和深度的思想。

《纽约时报书评》封面
新京报:所以——你如何理解评论中的“客观性”。
刘剑梅:评论一定有不可避免的主观因素,因为每个评论家(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的阅读背景、文学直觉和批评立场都不同,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批评路数和看问题的视角。但是,文学评论有没有客观性呢?当然有。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就是文学评论的客观性。文学经典像《伊利亚特》《哈姆雷特》就是好作品,任何有“话语权”的文学评论权威否认也徒劳,伟大的存在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文学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反之,任意拔高、任意吹捧也没用。
文学的精神内涵包括很广,也是文学批评着力最多之处,比如有的评论家非常重视文学的政治和社会内涵,有的非常重视心理内涵,有的重视文化实践的内涵,有的非常重视人性和情感内涵,有的重视思想和哲学内涵。我喜欢的精神内涵是那种拥有比较宽广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文学,在描述现实世界的人情世故的背后隐藏的是超越的宇宙境界、天地境界,不被政治和世俗伦理所羁绊,对是非、好坏、善恶都用慈悲心去同情和理解。

《洛丽塔》,作者: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译者: 主万,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12月
新京报:关于文学超越政治与伦理这个话题,接下来让我们转移到一些具体的例子上来吧。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现在不理解它的读者可太多了——大量读者表示对小说中以男性视角观看女性身体的段落表示反感,攻讦这本书的道德取向。在写文学评论时,你会关注当下对小说的道德诉求吗?
刘剑梅:如果一个文学批评者更重视文学艺术作品的超越性,就不会把社会道德标准凌驾于美学意义之上了。比如奥维德的《变形记》,由于《变形记》中充满了暴力的描写,不仅有残暴的殺戮,而且有许多男神对女性強暴等细节,到了我们当下女性主义崛起的后现代社会,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发生过是否应该把《变形记》从文学课堂中取缔的争议。如果从女性主义的眼光来看《变形记》,其中男神对女性強暴的细节,确实充满问题。同样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也一样属于“政治不正确”的。
然而,以性别和道德取向作为唯一的标准来阅读小说,其实很狭隘。性别政治和道德立场只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层面而已,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对美学意义和道德立场进行纯粹的划分,但是我在阅读和批评的过程中,会更重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比如奥维德的《变形记》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实在太丰富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把人性的复杂性和幽暗的心理深刻地揭示出来,这些都是文学经典的超越性价值,不能简单地用世俗伦理和政治话语来否定。

刘剑梅与父亲刘再复合影。
新京报:但如果仅仅关注审美的话,可能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例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从审美角度上来说,可能这本书并不会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但它的确具有很积极的影响力。这样的书籍,文学评论该如何去面对呢?
刘剑梅:我的好几位学生都特别喜欢《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可惜我自己还没有读过,以后会找时间读。不过,我看过林奕含生前的一个访谈,她提出这样的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小说中的男性强奸者其实是一位像胡兰成那样很有文学才情的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背叛那么浩浩荡荡的中国五千年的抒情传统和语境呢?艺术是否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懂得艺术之美的文人为什么心灵可以那么扭曲和破碎?会不会艺术从来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 林奕含,版本: 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她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对文学的功能提出质疑。我想她虽然非常热爱文学艺术本身,但是她对文学的美学观念产生了质疑,懂得欣赏美的人,一样可以做出令人不齿之事。但是她的这个大问题,其实也让我们知道,文学光有“美”还不够,还必须有“真”,有“善”,有美好的心灵。同时,她提出的质疑也让我联想起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提出的大哉问:“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集中营上班⋯⋯⋯⋯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
面对这样的大哉问,文学评论如果只是拥有美学的高度就不够用了,还必须有慈悲心、同情心,而且还要有勇气去面对黑暗的现实,比如鲁迅、波多尼奥、卡夫卡等都有面对深渊的勇气。波多尼奥在《2666》中不仅审视社会黑暗的环境,而且审视整个文化界或者文化人,是不是已然失去了“同情之心”,对暴力和残杀变得麻木。文化是否已经被“沙漠化”了,心灵变得荒芜了?就像卡尔维诺曾说过:“在地狱里寻找和学会认识谁和什么不是地狱,然后给他们忍耐,给他们空间。”这里就包含“善”的期待了。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不仅阅读书中的美学趣味,也阅读心灵境界和心灵方向,以及精神洞见。当我们感慨当下快失去的人文主义精神,一定是感慨人文知识中“善”的一面的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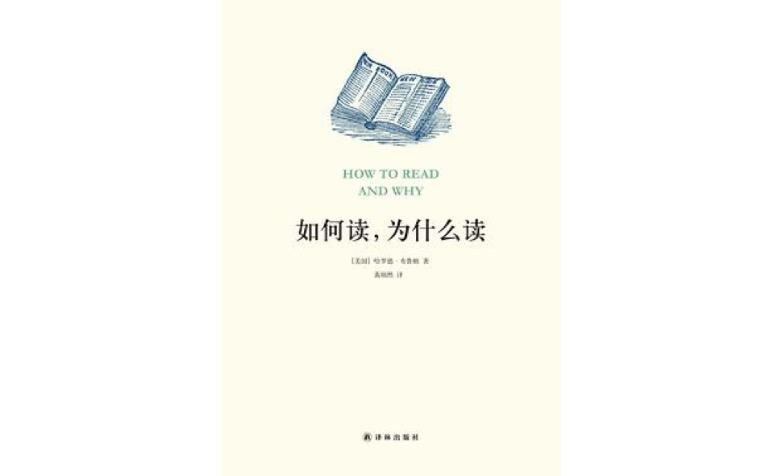
《如何读,为什么读》,作者: [美] 哈罗德·布鲁姆,译者: 黄灿然,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5年12月
新京报:可惜现在读者好像必须通过社会现实的角度切入,才能理解文学。最显著的一个表现是:已无人关心如何谈论一首诗歌。
刘剑梅:这个的确是我们当下的困境。不过,我认为,这个困境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评论变得过于政治化,大多从现实和社会科学角度去理解文学,而忽视文学的其他维度,尤其美学维度,比如表现形式、语言、风格、细节等,更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功利时代,人们的眼睛都“向钱看”,连读书的人都变得稀少了。
布鲁姆曾经引用过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这些诗句跟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一样不朽:“那些寂寞的群山有什么值得显露?/其光荣之眩目悲伤之痛切我无法说清:/那片唤醒一颗人心去感觉的土地,/可成为天堂和地狱两个世界的中央。”布鲁姆在这诗句中读到了激情,我读到的则是一种深刻的悲哀,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人会把目光投向那片寂寞的群山吗?恐怕天天都浪费在手机的社交群上了。
新京报:这也是为何做个优秀的书评人非常艰难。
刘剑梅:一个优秀的书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孤独的阅读者。阅读是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丰富的过程,这是一个庞大的心灵工程。通过阅读获得厚实的精神财富,就自然而然有了鉴别力和判断力,也就懂得如何“以心传心”了。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中,曾经说过:“我们阅读,往往是在追求一颗比我们自己的心灵更原创的心灵,尽管我们未必自知。”找到这样原创的心灵,一定会充满喜悦地试图分享给更多的读者。优秀的职业书评人,应该用非常清晰的语言,揭示出隐藏在书里的审美形式、精神内涵、文学血脉、个体风格,告诉读者这本书好在哪里,为什么值得花时间去读。
采写丨宫子
编辑丨走走 董牧孜 校对丨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