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让-克洛德·布洛涅
摘编丨董牧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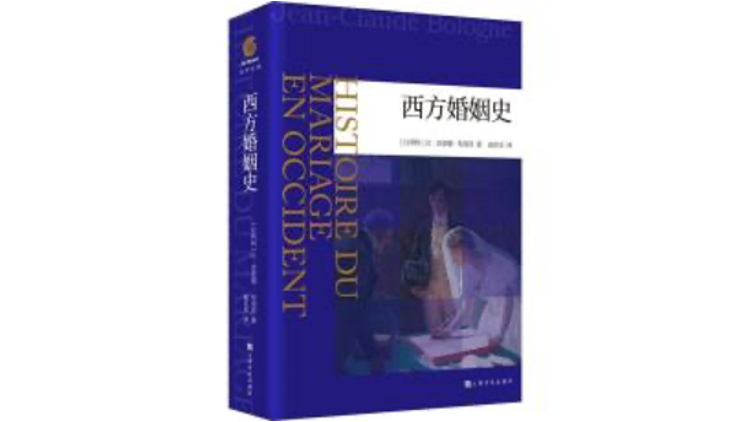
《西方婚姻史》,[法] 让-克洛德·布洛涅 ,赵克非 译 ,2020年8月
婚姻史,特别是在一种所受影响彼此矛盾的文明中,就是一部几种不同力量不断冲突的历史,这几种力量都企图控制婚姻这项根本制度。
要保留对婚姻的控制权的,首先是家庭。因为婚姻既关系到遗产和纯正血统的传承,也关系到贵族家庭的荣耀,以及与昔日祖先崇拜相联系的家庭崇拜。接纳一个外人总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会有各种抵触。为了使家庭放弃这方面的特权,必须使获得财产的方式改变,必须取消祖先崇拜,必须弱化出身荣耀的意识。这只能在一定的阶级(工人、农民)中,一定的制度(社会主义、共和)下,或者到了一定的时期(20世纪),才会成为可能。到了20世纪,决定财富多少的是劳动而不是继承,才能要胜于出身了。
其次是世俗权力,想控制在它周围织成的关系网,支持或反对它的,都要控制。封建时代,权力的分割使大家族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封臣的婚姻和主君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比较稳固的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国王们的管理监督权就局限于外交政策(和外国人联姻须得到国王的允许),或局限于宫廷这个小社会,主要是在那些作为王位推定继承人的亲王们身上。在民主政治和政治国际化的时代,世俗权力会变得更加审慎:如今,在有关婚姻障碍的问题上,世俗权力只在年龄(但法定成年年龄比平均结婚年龄低得多)和亲属关系(限制的范围很小)等问题上进行一些干涉。实际上,国家权力只局限于确定婚庆方式,以及让人遵守一夫一妻制这个欧洲传统。在西方历史中,世俗权力行使立法权, 这往往只是为了批准和统一家庭的权力。
最后是教权。教权创立了婚姻等级,分为精神婚姻和现世婚姻,与教会对世界和社会的总体看法相呼应;它要维持这个等级。“结婚在天,完婚在地”,这是卢瓦泽尔在16世纪收集到的古老民谣的说法。但是,如果说宗教作家是根据人间婚庆模式描摹出天上婚庆的(洛泰尔·德·塞尼写的《四种婚姻》就是一个范例),那么,这种根据人世间婚庆模式描摹出来的天上婚庆,却又反过来逐渐成了人世间婚庆宜于遵守的模式。

拿破仑一世的第二段婚姻
“婚姻制度”就这样确立下来了;这种“婚姻制度”,人不能稍加改动,因为那绝对属于神权。我们曾经看到过,连教皇本人都没有改动的权力。那是另一种婚姻理念,是超凡的,是人只能以高级存在的名义来接受的。一些人曾经试图使“婚姻制度”世俗化,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不过,这种使人类法律从属于“高级存在”(上帝、人类、父子关系、祖国……)的形而上观念,后来一直没有怎么发扬光大。
但是,教会自己也有控制婚姻的现世政策。面对异教徒世界或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于异族通婚(在确定亲属关系上日趋严格)有利,使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得以同化;与此同时,禁止混宗婚,起初只禁止基督徒与异教徒和犹太人的混宗婚,后来又加上了与新教教徒的混宗婚。在这一点上,教会与世俗权力对立,后者更喜欢民族内通婚(包括不同宗教之间的婚姻),而不喜欢不同种族间通婚。封建时代对婚姻的控制也能保证对封地的控制。只有教会能够决定孩子属于合法或私生,因而也就只有教会能够决定遗产的传承。
每种权力,
都在构想自己的理想婚姻
在婚姻史中始终维持着紧张态势的各种权力之间,不能忘记还有一个个人权力;在西方的双方自愿的制度里,最终在婚姻问题上有全权的是当事人。但是,由于社会对年轻人有种种压制手段,有经济的,也有强制性的,而且力量往往都非常强大,可以迫使年轻人做出一世不能更改的承诺。所以,这种所谓的当事人的全权常常也就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么多冲突,这些外部的权力依然不可或缺。教会强制推行严格自愿制的打算,接着是空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往这种古老制度中吹进一股自由空气的企图,都在同一块礁石上触了礁。暗中结婚和同居一样,根本得不到社会承认。所以,结婚并不仅仅是私人行为。
婚姻需要公示,需要庆典。家庭的、世俗的或教会的权力都要介入,以担保人的身份介入,作为确保婚姻具有稳定性的保护者介入。宗教婚姻比任何其他婚姻都更具有这种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它要求永久的承诺,给婚姻祝福(圣事),以便克服共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并通过多重隆重仪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总的说来,每种权力都根据自己的参照物对婚姻做出了构想。民法将婚姻归入它所管辖的契约(20世纪初走到了极端,甚至建议依据租赁契约法来签订婚约)之中。家庭法把婚姻变成了继承遗产的一种特殊情况。教会强制性地为婚姻搞了一套极具特色的结婚仪式,特别是上帝及其子民之间的基础结婚仪式——结合的本身被视为和《旧约》里的婚姻相似。建立盟约,从缺血为盟到饮酒为盟,就如同夫妻做出承诺时伴以领圣体一样; 盟约的条件记在十诫板上,犹如婚姻的条件记在婚约或陪嫁单上;立一块纪念碑,如同交出户口本;婚庆仪式的最后,是圣餐式或节日般的宴会……对比基督教神秘婚庆和人间婚庆,都扎根于一切神圣联盟所共有的仪式之中。
继续求助于外部权力,是因为需要外部权力保证婚姻的持续。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婚姻,都符合人们所期待于婚姻的不同类型的稳定性:财富的稳定性(家庭财富的传承或增加),家庭的稳定性(必须有时间教育孩子),情感的稳定性(能把爱情固定住吗?),政治的稳定性(用婚姻来保证的家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和平应该长久延续)……还有社会的稳定性(根据现代社会学家所做的心理分析,婚姻是把男人纳入传统的手段)。
婚姻是工具,使用这个工具,一户一户地,社会秩序就建立起来了,使共同生活有了方向。通过夫妻交谈,出于把“可能”变成“现实”的必需,婚姻获得了稳定性和保守性。男人摆脱了青少年时代的自我中心和无忧无虑,承担起了责任。因为结了婚,他周围的世界改变了。“这样一来,由婚姻所带来的稳定,就对这对夫妻生活于其间的整个现状产生了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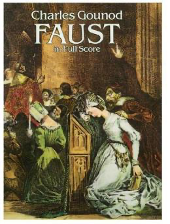
《浮士德》
其实,这种稳定纯粹是心理上的。在很多桩婚姻中,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大概就能发现,结婚的深层次原因是害怕孤独,即《圣经·传道书》里早就说过的:“孤独的人是不幸的!”玛尔特夫人在古诺作曲的《浮士德》中唱道:“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孤独地老去,是多么不幸啊!”为了避免这种不幸,她准备嫁给魔鬼……今天,那么多夫妇在寻找幸福中失败,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把爱情和恐惧混为一谈了吗?如果在怨恨消失之后,每个人还都想再体验一下婚姻,不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变得老成了吗?
我们在婚姻史中见到的第二类冲突,源于婚姻定下的不同目的之间的对立;确定下来的婚姻目的并非总能被要求结婚的人明确地体会到。爱情常常是用起来最方便的幌子。爱情与传宗接代之间的冲突(能够把不孕的妻子休了吗?拿破仑应该喜欢约瑟芬的爱情甚于喜欢玛丽-路易丝的生育能力吗?),传宗接代与金钱之间的冲突(如何使子女合法化?或如何剥夺子女的继承权?),金钱与爱情之间的冲突(暗中结婚),金钱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不同社会阶级之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爱情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包办婚姻和国王的情妇)……
这两大类型的冲突,一类是外在的,一类是内在的,构成了婚姻史。乍看起来,这些冲突似乎一环扣一环(爱情是个人维度上的事,金钱和传宗接代是家庭维度上的事,政治是国家维度上的事……),其实这几者之间的关系要错综复杂得多。
婚姻身份的观念,
萌生于古代社会
在早期的人类社会里,人的一生被分成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人按部就班地逐步融入社会。一般情况下,年龄就足以使一个人从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个阶段。罗马人第一次刮胡子,日耳曼人发给年轻战士兵器,都是成年的标志。这种象征意义很强的接纳仪式常常具有宗教性质,教会不能容忍就那样下去,要把它夺过来一例如青年骑士的授甲礼。
于是,教会就通过做圣事把教徒一生的种种过渡仪式都掌握起来了。主要的圣事有:洗礼,初领圣体,坚振礼,婚礼,临终涂油礼。在所有的圣事中,结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结婚和过渡到成年是一致的。通过结婚仪式,年轻男子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成为父亲之后)都有了自己的地位。自从新道德禁止婚外性关系以来,他同时也获得了完美地成为一个男人的权利。1546年为根特市起草的习惯法草案,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身份: “不结婚不解除监护,不到25岁不升为骑士,不升为神职人员,不取得显职高位,不在国君或城市首领那里得到身份或官职,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同样,公开经商的人也不能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唯有社会地位(神职人员、骑士)与公职可赋予成年(当时已经提高到25岁)之前的男子以独立,而婚姻即被当作社会地位与公职看待。
这种“婚姻身份”的观念萌生于古代社会,是自古罗马实行朱利亚法以来就有的。朱利亚法赋予已婚男人种种权利,是单身汉、鳏夫或离了婚的男人享受不到的。可是,罗马的一切组织结构仍然以年龄为依据,只有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升到某种尊贵地位。
婚姻依然是私人范畴里的事,结婚的目的主要是给孩子一种身份,就是说,是为了能够合法地转让遗产。十分自然,没有财产要转让的人(奴隶),不需要这种“符合规定的婚姻”。同居,即跟一个不指望她生孩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两人关系稳定,虽然不合法,却也并非什么不名誉的事。离婚和领养,为不孕这个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解决办法。男人通奸,为爱情和受制度压抑的性欲打开了一条出路;女人通奸,则是把后代的合法地位拿来冒险,会受到严厉惩处。这一内部逻辑引人注目。

名画《阿尔诺芬尼夫妇像》。
基督教要把这种原始的逻辑联系拿出来重新讨论。社会不平等理论的逐渐消失,实际上使不同类型的婚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了奴隶(取而代之的农奴,后来在婚姻问题上得到了和农奴主同样的权利),也就不再需要奴隶与奴隶之间或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那种“低级婚姻”;如果没有了社会阶级(代替社会阶级的等级已经开始出现),也就不再需要同居。单一的婚姻符合单一的人的理想见解。当然,社会总是分层的,但阐释这个社会的那些模型不分层,而婚姻再也不能分层了。
从宗教的角度看,婚姻也失去了指定合法继承人的法律作用。当我们要求另一种类型的占有即在精神上继承亚伯拉罕时,物质财富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笃信宗教的人蔑视婚姻,因为婚姻只传承物质而不考虑精神:人间婚姻的遗产,是亚当的罪恶,是肉体凡胎(在摩尼教教徒看来,肉体凡胎把神光永远幽闭起来了)的后代,或者是世俗财富。为了追随基督,应该把这些财富卖掉或者送给穷人。
婚姻切断了基督徒与其真正教父的关系。当新改宗的人发现他“真正的家”时,婚姻可以打破, 以便重新建立这种真正教父的关系(“圣保罗特许”就是这个意思)。婚姻充其量也只能因为可以防止性泛滥而得到容忍。圣奥古斯丁虽然确定了婚姻的三项好处,传宗接代却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因为不孕而领养或离婚, 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灵魂与耶稣基督神秘的婚姻,也可以按照婚礼的仪式(修女的戒指和面纱)缔结,也可以有合法的后代(信徒、圣书)。
婚姻变成了
爱情故事的结局
大革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彻底。爱情是占据了重要地位,可是,人们依然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它。爱情被形象地比作烧着的干草,瞬息即灭,而伉俪之情则能够慢慢燃烧,这样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恋爱结婚,可以,但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从此提出要求,要在20岁就带着这种绝对激情死去,或者,如果没有这份勇气,就靠离婚或一次次与人同居的办法, 让绝对激情重新开始。也许,不恢复离婚,恋爱结婚也能在我们民族的行为方式中获胜?没有什么人还要求从一而终,还要求婚姻里那种感情专一持久不变,虽然幸福且长久的夫妻并未因此而绝迹。教会也对伉俪之情做出了新的阐释:教会此后之所以接受婚前爱情,是因为,要使爱情持续一生,爱即使不要求牺牲,至少也要求深化,要求改变。
婚姻变成了爱情故事的结局,而不是一种新身份的开始,有变成一种行为而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趋势。男人立足于社会,靠的不再是婚姻,而是他的社会地位、他的职务。要想承认一个孩子并让这个孩子成为自己的继承人,不再非结婚不可了。至于性事,自从发明避孕方法和预防传染性病的有效手段以来,就不再需要只局限在婚姻里了。从前所说的需要结婚的种种理由,都已经一个接一个消失,剩下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关系,一种社会传统,虽依然保留着吸引力,却没有了必要性。

那么,婚姻是应该做些相应的改变,还是应该消失呢?当前,婚姻所遭遇的危机好像很严重,虽然现在还为时尚早,难以估计出其严重程度。但自相矛盾的是,婚姻存在的条件很少像今天这样齐全过。社会心态宽容了,年轻人经济独立了,住房多了,家庭联系松散了,都使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成为可能,这样的生活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也依然是一种理想。恋爱变成了文明行为,没有人再为爱情设置不可克服的障碍了。如果说婚姻的传统形式受到了损害,把一男一女结合到一起的关系却依然是深厚而诚挚的;如果害怕或讨厌隆重的仪式,就采取同居的形式。
自20世纪初以来,此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广泛。面对这一现象,主张承认不同等级婚姻形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说到底,这只是朝着罗马和日耳曼早期观念的回归,虽然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均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演变。 早在1936年,保罗·埃斯曼就号召,缔结不举行隆重仪式、只住到一起的 “二级或二流”婚姻。他可能希望这样的婚姻和举行隆重仪式的婚姻一样稳固和难以破坏,用来抵制越来越多的同居。不过,从那时起,另有一些人却要求将婚姻形式放宽,承认同居,不要再对同居横加限制。
“看来,多种'婚姻'形式似乎将会并存,”罗歇·热罗写道,婚姻“在这样一个多元但包含着冲突的社会里,靠尽可能少的法规并存。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使用法律过度的社会里,而私人的幸与不幸必须逃避法典与律法”。不过,热罗的主张失之于过分宽容:他希望在同居和不可分离的婚姻之间,出现一种由契约限制的可以重订的婚姻,每十年必须重订一次, 并重新举行结婚仪式。这样的解决办法不能不使人想起20世纪的乌托邦思想,遭遇的也是同样的现实:婚姻破裂常常就发生在最初的几年里,十年的契约似乎和不可分离的婚姻一样长。至于孩子的教育,很难有机会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完成。
然而,承认同居者和已婚人士在很多方面有同等权利,却也是朝着这同一个方向走的。难道这是社会于无意之中选择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样说可能失之于武断。我们还没有掌握能够使我们对当前危机原因做出分析的素材,因此也就无法说出危机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我们能够做的,充其量也只是对危机加以描绘。路易·鲁塞尔写道:“如果我们明显地察觉到了现在的紧张和举棋不定,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曾预见到新式的紧密结合的形式,连大致的形式也没有预见到……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不过,也许这就是真正被放到历史亦即演化中去观察的婚姻的全部可贵之处。
本文摘编自让-克洛德·布洛涅的《西方婚姻史》一书,由出版社授权转载,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作者丨让-克洛德·布洛涅
摘编丨董牧孜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