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黄家光
当一个人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做事时,我们似乎只能赞同它,支持它,而没有理由去批评它,指责它。因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只是依据明白无误的事实,表达一些常识,这是正常人都应当接受的,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诸众缺乏常识,所以由有良心的人表达出来。而对良心的意见表达批评或反省,就理应被看作是恶德或无知的表现。
但真如此吗?在《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一书中,斯塔罗宾斯基笔下的让·雅克·卢梭,给了我们一个“病例”,来反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批评良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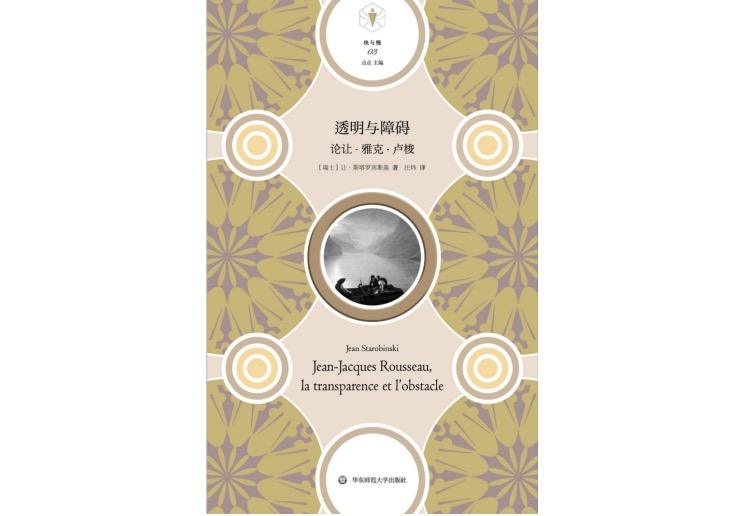
《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汪炜 译,版本: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这本书是关于卢梭思想的一份全新诊断书,为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让·斯塔罗宾斯基的博士论文和成名作,1957年一经出版旋即成为卢梭研究、观念史研究、文艺批评和理论等领域的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包括德里达、福柯等人在内的众多杰出的卢梭读者。
一、“心灵如水晶般透明”
卢梭相信自己“心灵如水晶般透明”,他总是宣称“我是清白的”,他按照如此这般的心灵指引行动,他的行为无往而不是善的。他相信自己与世界(这里的世界主要是“德性之城”)处在一种透明的关系之中,即自己的内心意愿与行动是同一的。但这种透明性因为私欲阻断,使得“我”与世界之间隔着一层面纱,他要做的就是“力求保卫或修复被损害的透明性”,这“关乎善良意志和良心的伦理道义”。
他为这种透明性的阻断提供了一个历史哲学的叙事。在他看来,所谓人类历史进程,是一个堕落的过程,一个本真的自然的人失却了他的天性,是劳动和社会化导致人之堕落,“一切都在人的双手而非心灵中开始堕落”。堕落之人隔着面纱所看到的世界不过是表象,而非真相。可是社会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中,如何超越表象,而重新与事实和真相建立联系?他似乎相信自我与社会是对立的,只有在遗世的孤独之中,才能获得拯救:“我与社会对立。……孤独的让·雅克则是对社会的个体化否定”。在此他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他必须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对公众的拒斥,“他依然以其反叛行为和反社会激情而与这个社会相连”。这个个人凭借自己的良心“与真理之本质融为一体”,站在社会之外观察社会,“伫立在社会面前,见证着它的一切”。他相信自己见证的不是隔着面纱的表象,而是直接的事实与真相。
这种见证活动好像使他介入到了世界之中,但正如斯塔罗宾斯基在讨论卢梭的植物学研究时指出的那样,“让-雅克不是作为博物学家,而是作为收藏家采集植物标本”的。这意味着,卢梭并不是向科学家一样以自己真实的行动介入到世界的运行之中,他的行动仅仅是“一项消遣,一个乐趣”,“这种活动并不试图获取任何知识或实践能力”。这些标本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记忆符号,使得过去的理想化的不在场在回忆中直接在场,也就是通过一个物件,沉浸在美好回忆之中。
卢梭认为,“当下感觉的直接性贫瘠而脆弱”,“而被记忆的直接性,其丰富程度和强烈程度都远超当下感觉的直接性”。所以,我们应当生活在回忆之中。这导致的结果是他的行动并未真正向世界敞开,而是自我循环中耗尽自身的能量。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
卢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在回忆的世界中,即影像世界(其按照理念构想出来的理想化的世界)中,世界才能如其所愿的运行,而当其行动一旦介入真实世界,其后果就不会如其所愿的展开,因为世界有不按照其意愿展开的逻辑,“他害怕生活在一个行动后果非其本愿的世界当中”。有时候良知的持有者,好像是以事实为依归,对他而言,事实是“原初的给予性。……一切都在当下发生;它如此纯粹,以至于连过去都在此重现为当下的感受”,但归根到底,他并不关心客观事实,“本质不是客观事实,而就是感受”,这种感受,不过是影像世界中的事物,他关心的是“道德的而非知识层面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卢梭例示这样一类人,他认定自己代表良心发言,而实际生活在自己的影像世界之中。他所见的就不再是外在于自我的世界之中的事物,而仅仅是通过标本构想出来的影像世界。
二、“反思是根本恶”
对卢梭而言,当他说“我是清白无辜的”时候,“我是谁”,我代表谁的良心?
当卢梭写作,尤其是写作自传时,他宣称“自己的意识和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他“不只是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灵魂、一个拥有纯洁心灵的受害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没有贵族家室的异乡人”。
这里的普通人实际是说他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又凭借自己的才华而出入上层社会,他说自己不属于任何基层,却了解所有阶层,“从最底层到最顶层,除了王权以外,我在所有阶层都待过”,这使得他可以“观察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不会将自己限于其中之一”,因此,“他的经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就此而言“我即人类”,“我”的经验是最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自然地,他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勾画一幅具备普遍有效性的人类画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的经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生存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在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的,而是一种情感经验,“更伟大的情感、更鲜活的观念”。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倒转,既然“我”的情感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我就不需要通过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就可以通过内省获得的“我”的情感,通达普遍的人类情感。又因为与世界打交道获得的经验难免出错,而“‘我感受着我的心灵’,此乃直观知识之特权,它直接向自身显现”,是直接真实的,不会出错的。就此而言,心灵知识具有一种自发的明证性,和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相比,它具有优越性。
不过这种明证性似乎是成问题的。主要有二,一个是这种直接的自我知识似乎排斥反思活动;一个是当卢梭以自传的方式谈论自己,使自己对象化的同时,也使自己处在一种被判决的位置上,“而他拒不接受这样的判决”。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卢梭对反思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它曾经持有一个更健康的反思观,后来被抛弃了。在他的主导性思路中,反思活动作为一个中介环节,使得主体(我)与良心之间有了面纱,不再具有直接的确定性,就此而言,“反思变成了一种有害的力量、一种罪恶的根源”,良心反对反思,“反思使我们偏离真是的目标”。甚至可以说“反思是根本恶”。
卢梭相信,通过某种情感记忆这种不会出错的内省方式,他可以建构“真实自我”,但这个真实不是对传记事实的刻画,而是“陶醉于直接冲动之中”,这是一种原初给予性,用更抽象的表达即:“我们不再身处于真实性的世界(即真实的历史);我们身处于本真性的王国(即本真的话语)”,本真性指“无间距、非反思”。反思活动割裂了原初统一性,使得意识出现了不可还原的分裂,卢梭期望用非反思的纯粹感受来克服分裂。依赖对良知的纯粹感受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但若陷入卢梭式的良心之中,把对”良心之举“的反思都看作是对本真性的偏离,实际上拒斥了对它的任何反思,而且认为,就算那些”正义的呼声“偶尔有错,也应当被原谅,因为这一切都“源自他那纯真无邪的意向和感受、温柔的激情、被辜负的善心以及他对友爱的强烈需求”。但这样一种美好的灵魂,作为最好的事物,就应当终止了我们的反思了吗?
三、“美好的灵魂”
上面我们提到卢梭在自我表白时,使自己处在被审判的位置上,而它似乎有拒斥这种审判。正如译者汪炜指出的,斯塔罗宾斯基对卢梭在此问题上困境之批评,主要借助于黑格尔对卢梭的“美好的灵魂”的批评来完成。美好的灵魂是说无视真实世界中的残破与自己行为的恶,而仅沉浸在自己美好意愿的世界之中。这种“美好的灵魂创造了一个纯洁的世界,这世界就是它的言语以及它直接听到的言语回音”。因为作为对象的纯洁的世界不过是自我的回音,对象与自我之间就是透明的,这个自我“自以为把握到它面前的对象,然而这对象其实还是它自己”。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
在这个世界中,它越确认自己的“清白无辜”,就越确认另一个真实世界是“暗无天地的敌对世界”。卢梭遁世于如此的纯洁的影像世界之中,就像后来的湖畔派诗人一样,对社会现实抱持着激烈的批评态度。此时他以不再关心世界之复杂运作,所有的善都在纯洁世界之中,在湖畔派诗人那里,就是理想化的自然界,而恶留给了在“我”之外的整个社会,不论是湖畔派所谓的工业社会,还是卢梭所谓的不平等的社会。“敌对世界的黑暗在场同样是卢梭需要的一个支点,他由此便可更彻底地委身于自己的透明性”,即自己的美好灵魂。他们已无意于面对社会或世界的复杂性,而期望用道德判断,取代复杂的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活动。也许应该说道德判断就是他的认识判断,完成了道德判断,他也就无需再完成认识判断了,“对世界中的行动的拒斥,这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荷尔德林对卢梭的解读不同,这里我们选择黑格尔的解读)
出路何在?对黑格尔来说,良知是“直接确知自己是绝对真理和绝对存在的精神”,但是当卢梭“遁世绝俗,逃避反思”时,这样的良知,不过是哀怨无力的“美好的灵魂”,只有当它放弃纯粹的世界,而“回归(真实)世界”,在粗糙的世界中存在,我们扬弃这一阶段,进入更高阶段。也许我们可以借此说,我们应当超越在《武汉日记》现在讨论的阶段,不论是以良心为它辩护,还是指责作者的并非清白无辜之人,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单凭良心,我们无法见证历史。
撰文丨黄家光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