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考研报名的季节,也是新一届研究生入学选导师的季节。博士研究生一般在备考前已经预定好了导师,硕士研究生则多在录取之后选择。无论在何种求学阶段,选导师都不是一件小事。不知从何时起,研究生在选导师这件事上越来越谨慎。在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导师少,学生多,学生和导师的结缘往往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考研人的自嘲表情包。
高校师生的关系在这些年尤其受关注,屡屡出现让全网热议的事件,在此背景之下,学生选导师小心翼翼,以至于在考研群体中有“前怕考不上,后怕选错师”的说法。同样,学生与导师相处也难免如履薄冰,小到发邮件如何选词,大到合作论文如何署名,再到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怎样处理关系,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增加压力。这一切再加上发表论文、撰写毕业论文的科研压力,以及毕业求职的现实压力,如何使人不压抑。导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学生的选择。
而本文作者李钧鹏提到他在国外读博时,见过“太多成绩优秀的中国学生因精神压力而产生心理问题,也认识不少性格活泼的同学因抑郁症而长期服药”。同样的焦虑在国内研究生中也存在。去年,他成为一位大学教师,开始带研究生。
李钧鹏是社会学大家查尔斯·蒂利生前指导的最后一位学生,目前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任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学术兼职包括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GYA Connections主编。他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关注者,在那里,他几乎每周都在分享与学生的沟通日常,有时会聊如何和学生写论文,有时会开玩笑又发现哪位同学关注他了。在下文,他要聊的是开始教书这一年多是如何和学生相处的,从学生怎样缓解压力谈到学生怎样阅读。有意思的是,从他的讲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缓解压力还是做研究,不少最有效且最持续的努力都来自于日常的互动,即便是“吵架”或“散步”。
撰文丨李钧鹏
1
当大男孩成为大学教书匠
成为一名大学教书匠是我从小就有的理想。在这一梦想实现之前,我一直希望成为哲学家约翰·罗尔斯那样的老师。吴咏慧(即黄进兴)在《哈佛琐记》中有这样的回忆:“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一场景令我神往。我当然从未奢望成为罗尔斯那般名垂青史的学者。读博士时,每次上导师查尔斯·蒂利的课,我必坐在离他最近的座位,生怕错过他说的一个字。罗尔斯和蒂利的人格与学识显然是我这种凡夫俗子所望尘莫及的。但我周围也有一些老师,甚至年轻老师,举手投足都散发着魅力。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大男孩性情使我永远成不了这样的老师。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顶尖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他被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国内已翻译出版其作品《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为什么》等。
回国教书一年多以来,我逐步认识到,培养学生显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最佳模式,每个老师也都有适合自身的教学方法。作为学生不太畏惧的那一类老师,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的同时,依据每个人的特点,尽量在学习上给他们有针对性的指导,向他们展现做学术的纯粹乐趣。
2
多跟人交流,哪怕是“吵架”
无论是博士生还是硕士生,无论是理工科还是文科,今天的研究生们普遍面临较大的压力。写论文思路不畅,人生道路难以选择,就业和深造之路皆面临重重挑战,遇到老师战战兢兢,和父母代沟越来越深……这些都让研究生们焦虑万分。我在国外求学多年,见过太多成绩优秀的中国学生因精神压力而产生心理问题,也认识不少性格活泼的同学因抑郁症而长期服药。我自己虽有幸经受住了考验,但写论文的过程也不是一般的苦闷。不同于在国外独自生活的留学生,国内研究生普遍住集体宿舍,凡事都有个照应。尽管如此,精神压力仍困扰不少中国学生。心理问题当然要找专业医生,但就学术而言,我对学生强调,一定不能孤军奋战,一定要多跟人交流。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的最后三年住在布鲁克林最南端,远离学校所在的曼哈顿上西区,差不多一年去一次学校。有一次偶然翻到入学后不久的课程论文,我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当年那般质量和野心的文章,因为它们源于“大剂量”阅读之后的灵感,完成于上课时和同学“吵架”、下课后和朋友喝咖啡的学术思维“沸腾期”。

电影《怪兽大学》(Monsters University 2013)剧照。
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学术本身就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我始终认为,读书和写作不应当是一个人的事,而应该是一种社会活动,一定要在一个志同道合的小群体里共同学习、互相讨论,一定要多跟老师和同学讨论,争取把做学术当成一件开开心心的事,所以我把自己和学生的微信群命名为“快乐群学”。一个学生的原话是:“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事实上,我和学生的许多学术讨论是在饭桌上和散步的路上进行的。
当然,一个只跟学生吃吃喝喝却在学习上缺乏有效指导的老师肯定是不合格的。在学术上,我对自己的学生有比较高的期待。硕士生将来当然未必走学术道路,但在学校的三年理应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读书和求知上,而导师应该当好学术的领路人。
具体而言,我是这样来做的。
 憋论文憋出内伤的博士。漫画来自于《念书,还是工作?》(作者:[法]蒂菲娜·里维埃尔 ;译者:潘霓;版本:拜德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憋论文憋出内伤的博士。漫画来自于《念书,还是工作?》(作者:[法]蒂菲娜·里维埃尔 ;译者:潘霓;版本:拜德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3
开列书单,提供阅读结构
在国内高校(或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对硕士生的学术要求和期待缺乏明确的界定。一方面,对硕士生当然不能有对博士生那样高的学术要求,毕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毕业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打算,而是要走向实际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学术型硕士又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就业为导向的一年制或两年制硕士,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人攻读博士之前的必经阶段,虽然许多学校已经取消了硕士毕业的发表要求,但对硕士论文的学术水准仍有较为严格的要求。
对于我所在的社会学专业来说,读书仍然是硕士阶段最重要的训练。我所指导的硕士生有相当一部分为跨专业报考,而且许多学生坦承之前并未读过任何专业原著,只是在考前背了几遍教材。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是本专业考上来的学生,往往也没有读过几本原著。因此,我不得不让自己的硕士生在第一年补上他们所缺乏的学术训练,具体做法是不要求他们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而是给他们开出经典阅读书单,让他们先进行一年的密集阅读。
说到开书单,有的老师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但面对只背过几本教科书的学生,我实在无法放任自流,而且觉得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一定的阅读结构是自己的职责。
开列书单其实很考验老师的学术功底,因为它要求不仅对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有娴熟的掌握,而且对不同中译本的版本优劣以及相关著作的难易程度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开书单不是报菜名,因为学生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经典著作从头读到尾。因此,对于开给学生的必读书单,我一般会给出要求重点阅读的页码或章节。不仅如此,我还对书单采取分级处理,将经典书单开给研一的学生,将特定领域的详细书单开给正在构思硕士论文的研二学生,将以英文著作和文章为主的专业书单开给博士生。
书单开好后,我会让学生尽快将书单上的文献过一遍,以此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如果这一分类下的几本书读起来都味同嚼蜡,那你很可能对这一领域没什么兴趣;如果某一领域的书读起来过瘾,那你可以考虑以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我这样告诉自己的学生。

电影《你好,之华》(2018)剧照。图为周迅饰演的袁之华。
4
以“抽屉式阅读”建立学术对话意识
就社会学来说,学生的普遍问题是不知道自己的经验问题属于哪一个研究领域,更不知道如何与该领域的经典与前沿问题进行对话。事实上,不少读到第二年的硕士生仍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兴趣是什么。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当然值得肯定,许多知名学者也力图打破学科之间与学科内部的藩篱,但这必须建立在对不同领域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如果抛开已有的经典研究谈“淡化边界”,那只能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我的做法是按照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几个我较有心得的研究领域,在硕士生入学时给他们开列分类书单,每个书单分别列出几本或十几本专著和论文。这些书和文章未必是传世名作,但能让学生对这一领域的基本理论、重要问题以及研究风格产生初步的了解。在每个领域,我分别列出十几个自认为有望写出优秀硕士论文的选题,并给学生逐一讲解如何开展相应的研究。
学生在写论文时往往从具体的经验材料写起,不清楚自己的论文属于哪一个研究领域,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写完经验研究部分后再绞尽脑汁地往论文塞进去一点理论,再想该用什么理论框架,这直接导致了我在论文评审过程中屡屡发现的理论框架和经验材料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是学生缺乏系统的阅读和训练,尤其是理论被大部分学生视为需要死记硬背的、和经验材料没有关联的内容。
对此,我的解决方案是“抽屉式阅读”。换言之,阅读不可盲目,而应在老师指导下按照已有的学科框架进行“大剂量”的分领域阅读;只有把一个“抽屉”里的重要文献全面而快速地过一遍,我们才能举一反三地用这一领域的“想象力”来审视看似互无关联的现象。学术灵感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想象,而是一边海量阅读一边积极思考的自然产物。
在选题上,我始终强调研究的理论趣味。在我看来,理论和经验不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而是互相映照、互为补充的两个维度。理论不是思想史,不能死记硬背韦伯说了什么,涂尔干说了什么,而应该随时指导经验研究;同理,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一定是来自于研究者的生命体验,而不是苦思冥想的空中楼阁。因此,我要求学生在阅读理论性著作的过程中时刻以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来辅助理解,并以理论来反哺经验研究。唯有如此,我们的文章才能兼具丰富的理论趣味和扎实的经验材料,我们的研究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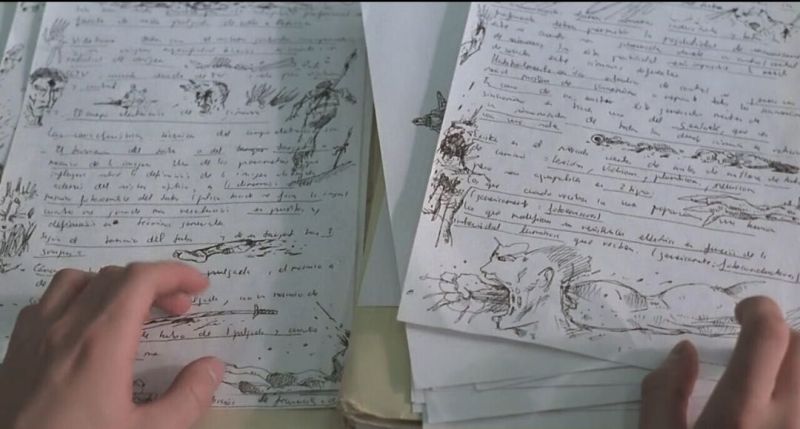
电影《死亡论文》(Tesis 1996)剧照。
5
与学生合作研究、办读书会
我从不主张学生以论文发表本身为目标,更不鼓励学生为了奖学金或就业而炮制低水准论文,但我也深知,学术能力不是仅靠阅读文献就能获得的,而需要从切身实践中得到提高。我从不要求学生给我做项目,而是希望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独立开展研究;但我也会结合学生的研究兴趣,积极创造与学生合作的机会,因为这是手把手教他们做科研的好办法。
在合作过程中,我和学生通常有明确的角色分工,一般由我提出总体思路、写作大纲、理论框架和重要文献,学生写作初稿(有时我本人负责理论部分的初稿),其间经历多轮的讨论和修改,最后由我定稿。如果是英文论文,则一般由我承担执笔工作。这一年多以来,我已经和研究生完成了两篇中文论文,其中一篇已经发表在C刊上;正在写作中的论文有五篇,包括四篇英文论文。我非常享受这种合作模式。
其实,国内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学生的真实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不完善的课程体系导致研究生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现状,我的应对之策是以读书会的形式弥补课程方面的欠缺。每学期的读书会都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这个学期是古典社会学理论,下个学期计划侧重于文化社会学,以后还计划以历史社会学、抗争政治或布尔迪厄、蒂利等大家为主题。
读书会每2—3周一次,每次选一本学生在课堂上读不到的好书,且每学期所读的书构成一个主题连贯的整体。
以这学期的古典理论读书会为例,选读的书目包括《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社会科学的兴起:1642—1792》以及以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等人著作相关章节,意在对研究生第一学期的社会学理论课程形成有益的补充,让学生对社会理论的起源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合作的论文,那更是锦上添花了。

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2001)剧照。
6
“必须陪他们走好这三年”
在平常的交流过程中,我随时推荐相应的阅读材料,有时甚至通过在豆瓣网上观察学生的阅读轨迹以了解学生的阅读偏好。
我自己所在的社会学是一个包容度极高的学科,不同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都能和平共存。有两个学生明确说自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不喜欢做田野,只喜欢读理论性著作。我一方面要求他们掌握必要的量化方法和田野技能,一方面结合他们的兴趣帮他们确定研究选题。例如,对于今年入学的博士生,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初步拟定以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但更多的学生对理论(其中涉及大量哲学)并无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会相应地启发他们对有趣的经验现象进行分析。看到学生们从事主题和方法各异的研究,我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一年多以来,指导学生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开夜车修改学生论文属于家常便饭。由于指导的研究生在数量上远超平均水平,我自己常常要付出额外的心血,也确实牺牲了自己的科研时间。包括学生在内,经常有人提醒我:“你这样带学生,会把自己搞得很累。”确实很辛苦,但也乐在其中。
对于我来说,每个学生都是与众不同的个体,我对每个人都有真实的感情;他们带着求知的热情来到学校,来到我面前,我必须陪他们走好这三年。在生活中,我对学生宽厚包容;在学术上,我却不希望降低标准。正如我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做人要脚踏实地,治学要仰望星空。”对我来说,如此指导学生固然会燃尽自己,但如果能成就学生,那我将无怨无悔。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钧鹏;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