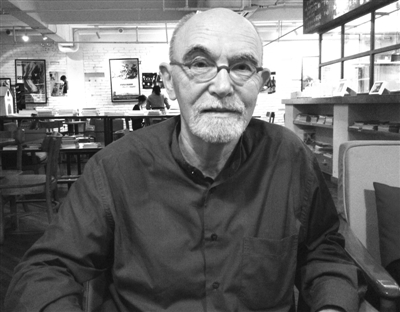
采访法国诗人、散文家热拉尔·马瑟(Gérard Macé)的傍晚,上海下起了今夏最大的一场雨。武康路上水深过膝,车游泳般驶过,扬起翅膀一样的水花。马瑟先生举着照相机,一路咔嚓个不停。此时你会忘记他是一位已然六十七岁的老人。他只是一个对异国好奇的旅人。这已是热拉尔·马瑟第四次来到中国。他的中译本新书《简单的思想》(Pensées simples)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全书以断章片语的形式,对文学、艺术、人类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跳跃式的思考。这位2008年法兰西学院诗歌奖得主的散文中同样充满了诗意,他以一种令人艳羡的博学游走于文字之间,打破学科的分野及文化的疆界,以简单的形式呈现深入的思考。
热拉尔·马瑟 1946年出生于巴黎。法国当代重要的散文家、诗人、文论家,1974年出版首部散文诗集《语言的花园》,2008年获法兰西学院诗歌奖。迄今共出版了四十多部散文及诗歌作品。此前,马瑟的散文集《量身定制的幻想》和《行脚商》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早在中学时代,热拉尔便因谢阁兰引发了对中国的兴趣。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谢阁兰研讨会上结识了程抱一,甚至试图学习中文。当然,他对异国或“他者”的兴趣绝不仅限于中国——日本、非洲、甚至动物世界都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如果你只关注自身,世界就会很小,你的自我也会缩小,” 热拉尔·马瑟说道:“在语言中,一个词的意思是通过与其他词的关系来定义的;同样的,一个人也是在与他人、别国的关系中定义自我的。我对远方、他人、其他世界都很感兴趣,因为它们能够令我更好地回到自身。”
在热拉尔·马瑟看来,这是一种既“向内”又“向外”的思想方式。他举例说道:“法国作家Michel Leiris早年便写了自传《人的年纪》,几乎是一种自我精神分析,是向内的;但之后他去了黑非洲,成为了一名人类学家,便创作了《幽灵非洲》,而那是一部既面向自己又面朝世界的作品。”
在《简单的思想》里,热拉尔·马瑟用引文、用记忆、用只言片语建造了自我的居所。“我不知道什么是自我,自我不是已完成的、一成不变的,不然它就成了雕塑。自我是一个满身洞眼、不充分的、摇晃的、总是需要重新生成的东西。所以我的书也没有结尾,它总是重新开始。”或者可以借用马瑟先生喜爱的诗人儒贝尔在《随思录》中的说法,这本书“不是绑在一起的思想,而是断了线的珍珠。”
■ 对话马瑟
谈书名 我不追求哲学的思想
Q:为什么书名要叫做《简单的思想》?
A:所谓“简单的思想”,是为了区分另一种思想,即哲学的思想。我并不追求哲学的思想,因为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可以用概念来表述。我想表达的不仅是思想本身,还包括思想的状态;使用的也不是哲学家的语言,而是所有人的语言,或至少是文学语言。“简单的思想”是思想的一种形式——文学是一种思想的形式,特别是诗歌,当然小说也是,这种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
另外,通常以“思想”为题的著作,往往先有了一个思想的结论,再步步论证;而我想表现思想的过程:它是如何萌生、发展、变化、跳跃的。
Q:本书与书中引用的儒贝尔《随思录》有什么关联吗?
A:有一天我在书架上偶然看见了《随思录》,便取下翻阅,发现我四十年前就已读过那本书,因为书上有我做的标记——对于“思想”,儒贝尔有一种特殊的定义,我将它画了出来。这样看起来,本书的写作四十年前就已萌芽,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写。儒贝尔令我感兴趣的是文字的联结方式,很轻盈、灵活,并非要证明什么,而只是文字的行走,是一种“时刻”或“瞬间”。四十年后重新找回从前的一个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有时候,人是走在自己前面的。
Q:书中有不少引用,有少数段落甚至是纯粹引用而未加评论。请问为何做这样的安排?
A:首先,当我与引用的观点绝对一致时,我毋庸再添加任何话语就能表达我的想法。其次,我不相信有绝对的“原创性”。第三,记忆既包含生活中的时刻也包含了阅读时刻。对我来说,阅读就是我的生活,阅读的记忆浮现在我脑海,如同生活的瞬间一样。蒙田在他的随笔中也有很多引用——虽然当时文学记忆主要来自希腊及拉丁文学,但属于同样的现象。对我来说,文学就是世界的声音。我的阅读生涯已有六十多年,我是被阅读所塑造的。对我来说,阅读不是外在的,而是每天的生活。
Q:书中有一段,只有一句“大象会打呼噜”。该作何解释?
A: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刚刚得知大象会打呼噜。我想,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呢?而且,前面正好有一个较长的段落,正好需要一段短文来将之打破。当然,我对动物本身也很感兴趣,所以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对我来说,思想也可以是很轻松、甚至无用的东西。生活中充满了这类不显眼、无足轻重的东西,思想并不一定是思考“幸福是什么”之类的。
谈作家 我不是一个小说家
Q:您在书中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诗人不可能不同时是个评论家”。在您看来,对于小说家是否同样适用?
A:我不是一个小说家,所以只能以读者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小说家来说会有所不同,因为小说家的评论一般会纳入到小说创作之中。比如说,普鲁斯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也可以看作美学论文;当然也有一类小说家,如莫泊桑,他的小说要简单得多,讲好故事就是它的目的。但一个作家是不可能没有对于文学的思考的,因此小说也好、诗歌也好,其中总有评论的成分。
Q:谈到小说家,您在书中也有对于艾什诺兹的几部小说,如《拉威尔》及《奔跑》的精辟评论。请谈谈对这位当代重要的法国小说家的看法。
A:我和艾什诺兹是好朋友,我家与他家只有两百米之遥,所以我们经常一起吃吃饭,我很了解他。首先,作为一个人,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很简单,一点也不骄傲、不虚荣。当然,他的作品与我完全不同,艾什诺兹不太读诗歌,我们的阅读趣味也有差异,但我们仍然彼此欣赏。对于艾什诺兹的小说,我喜欢的是它的简洁,不夸张也不悲情,这是一种文学的“道德”(moral)或对自身的要求(exigence)。我最喜欢他的两本书就是《拉威尔》和《奔跑》,我喜欢他书写人物的方式——并非传记式的书写,不是面面俱到的,我们并不需要面面俱到地去了解一个人,把一些重要的事件串起,就能呈现一个人的个性,这就足够了。我欣赏艾什诺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总是在讲述我们的时代,但又并不像社会学家那样,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我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都不喜欢塞利纳。
谈节奏 事先没提纲,也没预设框架
Q:《简单的思想》全书由连续的短章构成,段落与段落之间连接的方式有点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您是如何处理段落之间的连接,并控制全书的节奏感的?
A:这些短章的连接之所以像蒙太奇,是因为它们是某种“后来的安排”。我事先并没有拟定提纲,也没有预设的框架,全书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成形的,对于材料的组织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不是一本思想日记,写作时也并非按时序,我会在已完成的部分中插入一些段落,而这也是蒙田《随笔集》的组织方式,蒙田甚至在出版之后还不断加入内容。
全书的节奏是逐渐形成的。慢慢地,段落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和谐。这种和谐一方面是主题性的,但不能总围绕一个主题,不然会变成演说或论证。因此,主题之外还要有联想,或刻意地偏离,就好像船在河上的漂流,又如同我们的日常谈话一般。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大人谈话,我对谈话如何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很感兴趣,只隔了二十分钟,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题,但当中却又没有停顿。
另外,我也想找到一种足够灵活的书写形式,令我能够一直不停地写下去。我已经将《简单的思想》第二卷交给伽利玛出版社,之后还会有第三卷。这样一卷卷写,我希望当中有一些主题或作家会重新出现,就好像小说中的人物又在续集中出现一样。我希望我的散文书写中有这样一种小说的侧面,而不是像论证观点那样的写法。
本版采写、摄影/新京报特约记者 华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