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里,宋晓梧裹了件厚棉衣,为了拍摄,里面还穿着西装和小马甲。年近古稀,宋晓梧外貌上却没有多少改变。1980年,32岁的他进入北京经济学院读研,便踏上了研究劳动经济之路,历任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等职务。
“劳动经济”、“社会保障”、“振兴东北”,是宋晓梧人生的关键词。
48年来,令他骄傲的是,参与了两件“雪中送炭”的事:一是新农合改革,二是棚户区改造。尽管“投资不过山海关”、“唱衰东北”的论调甚嚣尘上,他仍对东北有信心。
作为经济学者,宋晓梧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调研、写文、著书上,没挣上几个钱。但他从未后悔。“世上成功之路并非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条”,宋晓梧说。
 宋晓梧,历任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劳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兼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宏观体制司司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等职。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宋晓梧,历任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劳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兼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宏观体制司司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等职。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属于我的路,只有一条”
到今年为止,宋晓梧已经退休十年了,他精神仍旧矍铄,黑发里只藏了几根银丝,皱纹也爬得缓慢。聊天时,思维清晰,反应极快,总是爽朗地笑。
但退休后的生活却变得更加忙碌了,因为身兼许多社会职务,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总有参加不完的活动。前一天,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邀请他去天津参加收入分配的会议,再往前,他在北戴河出差了十几天。
刚退休时,宋晓梧来者不拒,希望能“发挥余热”。2013年,生了一场病,他开始想“金盆洗手”,集中精力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和老伴去祖国各地转转,却总是抹不开面子。有人找上门来,他从不好意思拒绝。
闲下来的时间里,宋晓梧最喜欢写诗。好友马役军评价宋晓梧和他的诗,用了“坦诚”二字。“为官者善诗,但许多当官的人却不能把真实的心境、感受融入到诗里。宋晓梧做到了。”看到农村破败的卫生院,他会写“城乡异,云泥判”。
有朋友认为他“能站在客观的角度看待社会、人生”;也有人激他,“你写文、著书忙活一辈子,拿了几块钱稿费啊?”
宋晓梧想起来,自己确实错过了一个大富大贵的机会。
早年间,宋晓梧在内燃厂当电工时,曾经想开一家电器维修部。几位师傅拉着宋晓梧到化工路西口的小饭馆喝酒,让他牵头,“你技术好人缘好,不耍滑不贪钱”。二两酒下肚,宋晓梧一拍桌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考不上研究生,这辈子就和你们一起干这事儿了。”
“如果搞电器维修公司,再伺机进军房地产,现在腰缠万贯也未可知”,30多年后,宋晓梧在自己尚未出版的13万字自传中写道。但他现在并不后悔,“世上成功之路并非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条。”
宋晓梧:70岁以后不担任职务 要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 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命中注定”的经济学者
于宋晓梧而言,成为经济学者似乎是命中注定。
在北京五十六中上中学时,宋晓梧就表现出了对数字的敏感。他连获校数学竞赛第一名。到高三,老师对他说:“不用上数学课了,直接看北大数学系的教科书吧。”
1966年毕业数学考试,宋晓梧45分钟交了卷。老师看了一眼,写上“标准答案”4个字,让他贴到楼道里。
正在宋晓梧纠结报考北大数学系还是哈工大工程物理系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梦被击得粉碎。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30岁的宋晓梧报了名。同事听说后,聚在一起打赌,一位师傅掐指一算,说,“百里挑一你也能考上,这个不用赌啊,我算你考上了也上不了,谁跟我赌?”
成绩公布了,宋晓梧考了360分,比报考的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录取标准还高20分。可招生办的人告诉他,“你年龄大了,学理工科没有发展前途,分配你到北京师范学院白纸坊分院,去不去自己考虑吧。”
宋晓梧不服,耗了大半年的时间四处申诉,却无疾而终,只得回到内燃厂继续工作。
两年后,有消息传来,能以同等学力资格直接报考研究生。宋晓梧决定“最后挣扎一把”,这次,他成功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专业的研究生。
读研期间,宋晓梧开始到国家经委企业局实习。他跟着调研组到黑龙江调研,发现大多数国企存在“大锅饭”、“铁饭碗”,人浮于事。有企业为安置职工子女就业,一个澡堂安排20多人打扫。
问题存在已久。1957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便定下了“中国不存在失业”的论调,连“失业”这个词都不允许提。
宋晓梧想,如果没有“失业”,企业很难消化冗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相应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在参加某次国企改革研讨会时,宋晓梧提出了这个观点。反对的声音占据主流,有人让他别跑题,有人讽刺他讲外行话。甚至有劳动部门的老领导严厉批评,“你们知道失业是什么滋味吗?有的年轻人在那里写文章提倡失业保险,瞎搞,那还是社会主义吗?”
宋晓梧仍旧坚持,不断撰写相关文章。1988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宋晓梧讲了句,“中国面临失业问题”。国外的一些报纸借此刊登消息,“中国学者公开承认中国也有失业”。
一位老师特地打电话叮嘱,“暂时先用’待业’一词,等中央文件明确了失业一词再用不晚”。但宋晓梧说,改革把企业推向市场,自负盈亏,实行劳动合同制,不可能没有失业。
这是宋晓梧第一次参与经济理论争论。
在宋晓梧的学术生涯中,像这样的争论层出不穷:“劳务市场”是否该更名为“劳动力市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不应当搞双轨制?是否只有GDP增长8%以上才能保就业……
每当面临争议时,宋晓梧常想起南宋“朱张嘉会”,张拭和朱熹二人并肩论理,辩疑不绝,和而不同,成为千古佳话。“学术研究,贵在和而不同,有不同意见才更能激发深入研究问题”,宋晓梧说。

2015年08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某大型综合性医院市民在印有新农合医保的窗口办理医保手续。据了解,我国正逐步改善就医环境并完善医疗保险报销制度。
新农合的设想
2000年,国务院八个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先后到八省农村地区进行医疗卫生体制专题调研。宋晓梧是国务院农村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工作班子负责人。
调研前,宋晓梧从报纸电视里了解的是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到农村后,眼前的景象出乎预料。在湖南张家界的某个乡镇卫生院里,存放疫苗的冰箱已经锈迹斑斑,冰箱腿儿也断了,拿了几块砖头支着。用来做外科小手术的床上,还残留着不少血迹。医生是专业水平极低的赤脚医生。有农民告诉宋晓梧,“进城看一次病,就是一头牛(的钱)。”
当时,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非常严重。
据此,宋晓梧提出设想,构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由农村医疗救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商业医疗保险三层次组成。
八部委对此大方向达成一致,但具体的政策却争议不断。2002年秋,在北京杏林山庄讨论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宋晓梧主持会议,争论到清晨2点,部门之间也没达成统一意见。
散会后,卫生部一位司长一夜失眠,犯了病。宋晓梧也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填了一首词《望江东—农村卫生调研》:“城市豪华大医院,挤不进,人满患。乡村破败卫生站,可罗雀,多以散。调研八省仰天叹,城乡异,云泥判。合作医疗应立案,为耕者,还心愿。”。
好不容易确定改革初稿,在文件正式会签过程中,财政部和卫生部又发生分歧。关于农村卫生院的经费问题,财政部门的意见是按事拨款,补需方,卫生部门认为必须保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才能提供服务,财政应按定编定员保证经费。
文件拿到卫生部会签时,有位老同志指着宋晓梧的鼻子说:“你不把文件上这条改了,你就是破坏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历史罪人。”卫生部强烈要求按照定编定员保证经费。
国办那边也一直来催,“马上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怎么稿子还没会签下来?”时间紧迫,宋晓梧只好自己开车,带着文件一会儿跑到中南海找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一会儿跑到西直门找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到处沟通协商签字。
最终定下来按卫生部的意见为准。200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正式发布。
2003年,初型新农合制度开始建立。起始筹资标准是中央财政每人每年补助10元,地方财政每人每年补助10元,个人每人每年缴费10元。2017年,新农合总体筹资规模已经达到每人每年630元,是2003年的21倍。其中,财政补助标准由2003年的20元提高到450元,是当年的22.5倍,个人缴费由2003年的10块钱提高到180元,是当年的18倍。
 2007年11月23日,辽宁阜新,矿区附近的棚户区。
2007年11月23日,辽宁阜新,矿区附近的棚户区。
雪中送炭的棚户区改造
2004年,宋晓梧被调到了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具体负责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在抚顺调研时,时任市委书记周忠轩向他们汇报了当地棚户区的问题。
棚户区的房子大多都是50年代初盖的半地下小窝棚,另一部分是伪满洲国时开矿盖的,约有14万人集中连片居住,绝大多数都是大集体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周忠轩说,“我不带你们去了,你们随便去看,不然还以为是我安排的。”
宋晓梧到了棚户区,遍地都是垃圾,污水横流。随机进了一家门,屋里阴暗、潮湿,床上散着床破棉絮。主人见了他,“咯噔”就跪下了,拿出一份上诉状,说自己以前是劳模,企业破产后生活困难,希望能有政策帮扶。
屋外聚了好几个男青年,冲着宋晓梧大喊:“又来调研!调什么研?来了这么多次,管什么用?”
和居民座谈时,宋晓梧了解到,煤矿枯竭以后,多数下岗职工在外打工,很多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在小学,老师不能教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老师带着一唱,小孩们哭成一片。
棚户区的犯罪率也比其他区域要高十几倍。当地政府想了很多办法,组织下岗工人自谋职业,但一直也发展不起来。
在调研中,宋晓梧发现,资源枯竭城市普遍存在棚户区现象。于是,他们提出棚户区改造应当立项。
如今,棚户区改造不断扩展。2018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提到,“五年来,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上亿人喜迁新居。”
 2017年12月8日, 北京2017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展台。
2017年12月8日, 北京2017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展台。
绕不开的“振兴东北”
从2004年开始,“振兴东北”是宋晓梧绕不开的话题。
今年年初,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录制视频称,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侵占其公司23万平方米土地。一时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尘嚣直上。
“东北是大政府、弱市场”。宋晓梧坦言,“政府”这只手起的作用要比其他地方大一些。
像亚布力这样的情况,宋晓梧也遇到过,有企业在某市建了个厂,市里要改造这个区域,让厂子迁走,也答应补偿。但是厂子迁走后,补偿金迟迟落实不了,以各种理由推脱。
厂里的人告到宋晓梧那儿。但当时,整个东北办也才二十余人,这类事情多了,宋晓梧也没辙儿。
2005年,在香港召开港澳企业家东北投资座谈会。宋晓梧问企业家们:“你们认为东北有什么问题?”
企业家们普遍反映,东北地区官员一上来非常痛快,特别是喝了酒以后,大包大揽,“你这全能解决”。可一旦项目落实了,各种情况就出来了。而在珠三角投资,是“丑话说在前头”,虽然一开始跟政府谈得很细,但最后基本都能够按条款来办。
宋晓梧说,无论是新兴产业培育还是传统产业升级,都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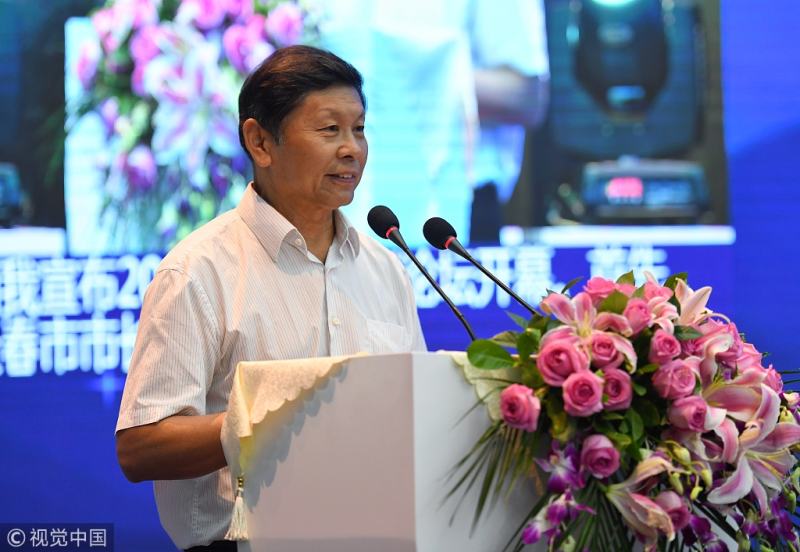
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宋晓梧主持会议。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地区企业养老负担特别重。
十二五期间,黑龙江的养老金企业缴费率是22%,广东平均只有13%,深圳甚至只有6%。宋晓梧打了个比方:如果投资一个10000人的企业,平均每人月工资5000元,年工资总成本6个亿。如果在广东投资,跟黑龙江比,一年可以节省人工成本5400万。很不公平。
宋晓梧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全国应统一缴费率和缴费基数,实现全国共济。”但他也说,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始终下不了决心。这也牵涉到我们的财税体制。基本社会保障的事权、财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理顺,现在改革也没到位。
尽管如此,宋晓梧仍不赞成唱衰东北。从2004年到2013年,东北的GDP增长全国领先。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背景下,钢铁、石油等需求非常大,与东北的产业结构相契合。
2015年,全国政协到黑龙江调研,宋晓梧也被邀请。参观了多家工厂后,他发现,东北的工业生产技术在全球都是顶尖的,产品能销往德国、日本等地。“东北经济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是因为国内整体经济下行,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减少,东北没有国内订单了”。
宋晓梧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直是改革的重点。2007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如今已过去十年时间。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这种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宋晓梧说,目前,东北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经济结构已经有较大的改善。以前,东北国有企业能占所有企业的百分之七八十,现在,黑龙江的民营企业占比到了百分之四五十,辽宁的民营企业占比到了百分之六十。
“东北经济已经开始反弹。国家目前也给了很多支持,只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东北一定会有所发展。”他说。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宋晓梧:年龄过了70岁了,按照有关规定,不能再担任任何社会组织职务,自己更加超脱了,可以有更多的精力用在学术研究方面。
新京报:这15年你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和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宋晓梧:美好的事得分成两个阶段,我在最后的行政工作岗位上,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还是尽了力的。特别是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民生问题,比如棚户区改造。退下来以后,这十年在全国政协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工作,一直在为改革呼吁和研究,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公司化、区域协调等方面。对十三五时期的社会保障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
最遗憾的是,我觉得这些年来自己很想集中精力去研究一些问题,但是由于承担了一些社会职务,很难集中起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宋晓梧: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了,现在身体状况还可以。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就是进一步集中精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研究,比如说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再一个就是和自己的老伴到祖国大好山河,以前工作忙没有去过的地方,都一块去看一看。
新京报: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宋晓梧: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国力的发展不用说,整个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动摇。这是一个伟大的探索,探索成了,我们就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治理国家,或者是向前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的完善起来,为人类做出中华民族的独到的贡献。
■微言
公共语言的更新使命当有后来人承接
提及宋晓梧,更多人对他的认识可能是 “振兴东北”。他曾担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是东北振兴许多政策的设计者和东北振兴实践的推动者。
而抛开政绩和学术成就,我更想从推动公共语言变化的角度来理解他。
例如,“失业”这个词我们现在耳熟能详,但这个词语进入我国公共政策讨论领域却颇费了一番周章。如今才知道,这个词语能进入官方文件,与宋晓梧先生有莫大的关系。
社会经济变革,也是公共语言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难度超过一般人想象。不是局里人,不知道伴随这个变化的酸甜苦辣。公共语言变化的背后是思想的变化。一种思想的的生成与推开,与一代人的生活体验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公共部门开始扩大,得益于新的高考制度的一批人进入了国家机构。这批人有基层社会的体验,进了大学后开始学习新知识,有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公共语言。这批人当然不会是一个格调,但其中的大部分开始用新的语言思考国家改革事务。
类似“待业”还是“失业”的词语选择,实际上反映了新旧公共知识的对垒。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也基本退休了。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及大学课程设置发生重大变化,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杰出政治家举起改革开放大旗,其麾下也难聚集起来拥有新知识的推进改革的新队伍。
在这个过程中,新生代力量补充到国家机关,带来新思想和公共语言,具有助力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思想家十分重视语言逻辑改善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公共语言的似是而非会诱导人们对现实问题的不求甚解,使装神弄鬼、装腔作势、空话套话充斥公共生活,严重妨碍人类文明进步。
在我国,如宋晓梧先生这一代人退休了,公共语言的更新使命当有后来人承接。扩大改革开放步伐与公共语言更新相互促进,是极有意义的国家进步机制。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侯轶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郭利琴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