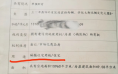2018年11月5日,李斌戴上机场发的耳塞,坐上一架只能承载十几人的小飞机。他要从挪威的朗伊尔城(Longyearbyen)出发,飞往北极圈内的另一座挪威小城新奥尔松(Ny-Ålesund)。
那是李斌坐过的最小的飞机,一眼就能看见机长的后背和仪表盘,除了坐在前面的乘客外,飞机后部还有被送往新奥尔松与人做伴的流浪狗。飞行途中一路踉跄,螺旋桨轰鸣,冷风从窗缝中钻进来,窗外白雪皑皑。

极光下,李斌开着极地摩托车。受访者供图
李斌大高个,圆脸平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时吐字清晰、慢条斯理。他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研究空间物理。他到北极的目的只有一个——“看极光、看极光、还是看极光”。他看极光的地方是新奥尔松的黄河站,一个人,一下子看了117天。
作为2004年中国在北极建起的第一个科考站,最近两年的秋冬季节,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都专门派出人员去那里看极光。今年10月28日,新一拨科考人员又出发了,他们或许也会经历李斌口中的小城极夜故事。
以下为李斌的口述。
“翻译”极光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2012年第一次看到极光时的场景。
那时我还是空间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在朗伊尔城坐着车,沿着雪地开到观测站观测极光。透光车窗,我看到了朦朦胧胧的一片,之前见过极光的同学确认,那就是极光。但真到了观测站,那点朦胧的极光也退下去了。
在观测站等了很久,突然有同学喊“极光出来了”,我们穿上衣服、扛着相机就往外冲。因为注意力全在天上,没留神脚下,我掉进了一条两米深的雪沟里。不过当时根本顾不上疼,从雪里爬起来继续拍极光。
你亲眼见到的极光,有时就像一场天幕电影,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极光。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层层叠加在一起,像用大毛笔在黑色的宣纸上作画。你可以想象一下,毛笔里浸满了淡绿色的墨水,笔锋处是一点亮绿,然后一笔下纸,不同的绿色层次分明,一直延伸到天空深处。
而且极光是会动的。有时候就像一条条舞动起来的绿绸带,边缘处渐渐呈现出红色、紫色。那种舞动时而轻柔,时而激烈,颜色也会发生变化,若隐若现。有时候一部分暗下去了,另一部分又突然亮起来;有时候又会有那种轻柔的、淡淡的极光,你还以为只是天空中飘来了一朵棉花一样的淡红色的云。

在新奥尔松,有时极光就像雪山中冒出的烟。受访者供图
除了好看之外,极光反映的是地球的磁场变化,看极光是空间物理学实验观测的一项。
从科学的角度讲,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在磁场导引下撞击大气,和大气中的氧气、氮气发生碰撞,就会产生发光现象,也就是极光。如果带电粒子撞上的是氧气,就会释放出绿色或棕红色的光;要是撞上氮气,就会释放出红光或蓝光。
极光变色,其实是地球磁场在变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能量非常大。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领域。对我们这些研究者而言,舞动的极光就像地球和太阳的对话,我们的工作就是试图读懂这种自然现象,把它背后的物理过程翻译给大家。不过我认为,研究极光最本质的意义还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我们会把极光分成几类,比如那种以绿色为主、有明显边界的极光叫分立式极光,你多在当地时间夜晚看见。像云一样模糊、颜色发红的,叫弥散型极光,一般出现在当地时间的正午左右。所以只有那些正午时刻依然是黑夜的地区,才能看到弥散型极光。地球上这样的地方非常有限,除了南极大陆冰盖上的高磁纬度地区外,最合适的位置就是黄河站所在地——北纬79度的新奥尔松了。

在新奥尔松,可以观测到旋转而上的极光。受访者供图
过去五六年,我看过各种各样的极光。一次,极光就像远处的雪山里冒出的烟:接近雪山的那头是亮绿色,亮得发黄,渐渐地旋转“升起”变成浅绿色,尾部的淡绿色又和云彩融合到一起。当时星辰漫天,极光映得湖面一片碧绿。
2019年2月,我见到了一种很奇特的绿色极光,一排一排的,又短又小,既不旋转,也不舞动。我给它起名叫“指头”极光。它和我之前看到的极光都不一样,我和南极中山站的同事一讨论,他们也发现过一次。就像人的手指头一样又短又小。
黄河站上的“小阁楼”
我是2018年11月5日到达新奥尔松的。这座极地小镇上,几幢科考站的小房子星星点点,散发着晕黄的灯光,四处一片宁静,远处传来几声狗吠。
那幢几十米长、上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就是黄河站了,门口还蹲着两只醒目的石狮子。
1925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加入《斯瓦尔巴条约》,因此中国人可以自由进出新奥尔松,进行科研和经济活动。2004年黄河站落成,成为中国在北极建立的第一个考察站。
到达黄河站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启几套极光观测设备。它们在楼顶的5个“小阁楼”里,是一些像黑色望远镜一样的东西,镜头口径有碗口大小,整体长度超过1米,学名叫极光成像仪。成像仪要在控温控湿的环境下才能工作,你可能在电视里看到过,有人戴着顶灯上房顶检查仪器,那其实是非常不专业的。
我到的时候,这些极光成像仪已经休息了一整个夏天了。一连几天,我都要不停地调试硬件、软件,直到它们可以正常拍摄极光。
设备调试好,后面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里点点鼠标,远程开机、设置好参数后机器就开始记录极光数据和现场天气了。这些资料会被打包好,上传、发布到中国南北极数据中心的网站上,全世界的研究者、爱好者都可以申请下载。

2018年,李斌站在黄河站前。受访者供图
极光成像仪传送到电脑屏幕上的极光,和肉眼看到的不一样——数据是黑白的,形状有点像燃烧的火焰。成像仪会准确记录每时每刻特定波长的极光分布,比如24小时内,紫色、绿色、红色三个波段的极光在南北方向上的活动变化。另一种图像是极光全天空图像,你看到的是一个球,极光出现的地方,球体相应位置发白,其他地方都是黑的。
掌握这些数据,是为了可以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极光。因为极光会对与磁有关的各种设备产生影响,比如地面和卫星通讯、北斗或者GPS导航。极光越亮、范围越大、越好看,这些设备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极其严重的时候,磁场变化产生的电流和能量,可能摧毁高铁铁轨、电网线缆之类与电相关的系统。
像1859年的太阳风暴事件,当时世界大部分地方都看到了极光,欧洲、北美洲的电报系统因此全部失效,电报机自燃,还有的发报员触电。
不过,我们目前对极光的预测还处在初级阶段,只能告诉一个大致时间和强度,准确率很低。这是因为我们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但科学卫星满打满算不超过10颗,和地面上密布的气象台没法比。所以我们对极光还有很多未知。
一个人,夜以继夜
虽然属于北极圈内的高纬度地区,但新奥尔松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冷。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这边二月最冷的气温也只是零下14摄氏度。而随着最近几年全球变暖严重,2018年二月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4摄氏度。
最直观的感觉是那里的湖水现在不怎么结冰了,我蒸完桑拿,可以热气腾腾地裸奔几百米跳进去蘸一蘸,还能在里面游泳——因为那里没人,黑夜里也看不到人。但据说新奥尔松的海湾以前是结冰封冻的,雪地车都可以开上去。
在新奥尔松,夏至过后就慢慢进入极夜了,24小时都是黑的。如何适应这种漫长的黑夜与黑暗,是对人精神的一种巨大挑战。

在新奥尔松黄河站旁拍摄的极光。受访者供图
在极夜里,钟表除了与吃饭有关,其实是没意义的。所以我把每天的生活强行和饭点联系起来,制定出一套自己的生物钟。
比如我会把灯光当成阳光,睡醒后先不开灯,摸黑穿好衣服,然后在7点30分到黄河站外50米的挪威王湾公司食堂吃早饭,他们专门为各国科考站提供食品、管理等基础服务。早饭回来后,我才把站内的所有灯全都打开,屋子里一下亮了,就像到了白天。
傍晚5点,我会模拟太阳下山,先关掉一部分灯,制造黄昏的效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熬夜的,因为极光在半夜时才比较容易观测,后半夜,随着极光慢慢退去,我会把所有的灯关掉,意味着黑夜要入睡了。
去年冬天,除了我在黄河站越冬外,新奥尔松还有一些法国、德国等国的科考站队员和王湾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共二十几个,还没有北极熊多。
因为人数太少,那里连理发店都没有,头发长了,只能是不同国家的科考队员间互相剪头发。我的头发是一个挪威极地所的法国小姑娘帮忙剪的,当时她到了我们考察站,特别热情地给我剪了一小时。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在法国剪子卖得很贵,所以她只有一把简单的小剪子。后来我回国专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托夏天到黄河站观测的队员给她带过去了。
遇到特殊情况也只能自己应对。去年12月时,我听说会新奥尔松会来一场十几级的暴风雪,整个小城都进入警戒状态,所有人必须待在屋里。暴风雪到来前,我把黄河站所有门窗都检查了一遍,领导担心停在门口的面包车被风雪吹走,我就用一根缆绳把面包车和两辆雪地摩托车拴到了一起。还好,后来它们都没被吹走。
在那种没什么人的地方,动物也是一种陪伴。有一对王湾公司的小情侣领养了一些挪威的流浪狗,通过我开头说的小飞机把它们送到了新奥尔松。这些爱斯基摩犬很厉害,那么冷的天气里就住在外边的一个小棚子里,等着小情侣去喂养。也许在新奥尔松真的比较孤独吧。
今年3月,那里的天开始蒙蒙亮了,极光慢慢比较难看到了,我也坐上了返程的飞机。回国后回想起这段时光,突然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享受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只与自己相处。
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编辑 滑璇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