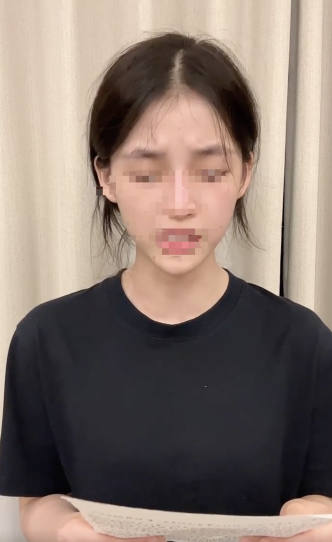何青一行人已经进山六天了。
领头的张老师对着名册几番确认说:“这是最后一家了。”
他又看了看何青。
何青还是那样,温柔而坚定地朝他笑笑。
于是张老师败了似的,朝着队尾忙个不停的身影喊道:“李大娘,这次你和何老师一起去吧。”
李大娘是学校的掌勺师傅,面孔黝黑,做事干练、厨艺老道,是典型的农家出身、勤恳可靠的人。
张老师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口中呼出的热气顺着鼻梁模糊了眼镜:“汽车只能到这儿了,我们会在这等你们。你们也年纪不轻了,小心上路。”
李大娘信心满满,一边将那几叠书本捆扎好,一边打包票:“放心,这几道山,我们可熟着哪!”
清晨的露珠尚未蒸发,他们就上路了。
何青很细心地用塑料袋包缠了个严严实实,才放心地放入背篓出发。这可都是学生的课本啊,一定要簇新簇新地送达。她心道。
前天来了场小雨,亏得他们早给书披上防尘的油布才没弄潮,她也就此长了心眼。
耳畔的雀儿啁啾,细密起伏,好听极了,脚底的路还是泥泞的、湿滑滑的。
倒不是误踩青苔后那种会让人心慌慌的、难以控制平衡的滑,而是一种无间的亲密感:泥在挽留你抬起的脚,泥在亲吻你落下的鞋底。
“噗呲噗呲”的足音和裤角的泥星都是泥土的耳语和书信。 眼前一派嫩而勃发的绿,她促然觉察:哦,早就是春天了。
何青气喘吁吁,恍惚间简直想摘下口罩呼吸大山的空气。
李大娘的声音透过口罩和薄薄的晨雾传来,气息稳健:“何老师慢点走,不急,权当是在山里旅游。”
看着何青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她叹息道:“唉,您是大城市的高级教师,何必来干进山送教材这样的苦差事呢?”
说完,又生怕她灰心似地,鼓励道:“别看这最后一家入山最深路最远,景色可是最好!那几家近的去了要蹚几条溪,只有年轻人适合,咱可受不住那凉冰冰的水。这条路不难走,就当锻炼了……”
李大娘的话匣子打开了就难收住了:“这课本还有点斤两呢。嗨,这开学推迟了又推迟,我不上班不打紧,娃娃们功课可得落下了!这病毒什么时候才能被消灭啊,日子什么时候才回正轨?”
何青喘着气儿,回答却很清晰:“孩子们的学习可不会落下。还有网课呢,也不会让疫情阻碍了课堂。这不,我们在送课本,病毒可挡不住求知。”
不过思及疫情防控,何青的神思就飘忽起来。
李大娘的话头顿时止住了,她明白何青在思念她远在“前线”的女儿。
林间顿时寂静了,只有鸟儿还在窃私语。
口罩包不住的热气一圈圈上涌。女儿面对被病痛折磨的父亲掉的眼泪,报考医科大学的倔强,穿上白大褂的喜悦……以及,微信视频通话中,被口罩护目镜勒红磨破的算梁和耳根。
她又害怕,又心疼,却又骄傲。
何青又回想起最近的视频通话中,女儿逐渐放松的眉头,脸上渐多的笑容和雀跃着道出的捷报。
今天又出院了多少例,重症的病人有哪些转回了普通病房,疑似确诊又下降了多少……进山前一晚,女儿在电话里的欢呼:“妈!方舱医院清空啦!任务完成了!我就要回来啦!”
她当场就哽咽了。
病毒很可怕,隔离很无助,停工停产让人心慌,但有许许多多的白衣执甲者、逆行者守在最前方,日子一定会渐渐好起来的。
想到这,何青紧绷着说:“会的,很快,就好起来了。”
她背着背篓,努力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口罩随着呼吸,一鼓一陷,一鼓一陷,仿若坚定的心跳。
日上三竿时,他们终于瞧见那幢房子。
一个孩子远远地就跑跳着迎上来:“老师!老师!我在这儿!”跟在后面的细犬也摇头晃脑,尾巴招摇。
作者 张颖 编辑 陈静
该文系“以写作之名——新京报·新声代第二届中学生写作创造营”投稿摘登。投稿请发至xjbpl2009@sina.com邮箱。更多活动信息请关注本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