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傅国涌(《金庸传》作者)
整理: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金庸去世了,这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情,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他的时代早在30年前就开始谢幕,但无论他的肉身的存在与否,仍然牵动着千千万万读者。
作为在近百年历史中生活过、努力过,对这个民族和世界怀抱过梦想,并且将这些梦想付诸过实践的一代报人和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离去将引起人们对他更多的追问、关心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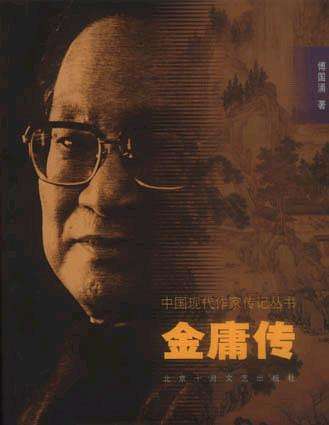
《金庸传》
作者:傅国涌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
“文人论政”最后的一抹余光
15年前那个酷热的夏天,在杭州,金庸对中央电视台“新闻夜话”的主持人说,将来他的墓碑上会写着这样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如果认真考究的话,应该改为这样更合适,“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遥望当年,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写下的14部武侠小说,让无数人如痴如醉。但更重要的是,在1959年到1989年的30年间,他所创办的香港《明报》曾经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中文世界。虽然,大陆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知道有《明报》,也没有看过《明报》,但是《明报》却关心着那个时代的大陆,关心着那个时代的两岸三地,乃至整个世界。金庸亲手执笔写的社评,影响过许多读者。
他的语言干净、朴素、明白,也常有深刻之处。早在少年时代,他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就显示出他在写作上的出色才能。他的文字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相当成熟老练,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就开始成形。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经过了内战的时光,他从1948年来到香港,进入新闻界,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或者说最宝贵的黄金时光,都在从事报业。
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大半个世纪,金庸奔波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新闻报》,自己创立《明报》,并把《明报》办成报业集团,成为华人世界傲然独立的一位报人。所以,他留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留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影响一样重要。虽然,今日大众更关心的是他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甚至连他本人在晚年也把武侠小说看得极为重要,但当年创作武侠小说不过是办报的副产品,办报才是他的正业。

由金庸创办的《明报》
金庸在报纸上发表武侠小说,是为了吸引读者,扩大报纸的销量。他真正想传递给大众的,是他在社评中表达出来的对两岸三地、国计民生和世界风云的关切。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评论家,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在那个动荡时代,他提供了清醒且成熟的声音。他不是莽撞的人,在任何风云激荡中,他总有深思熟虑的声音传递给读者。无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的震荡当中,还是在80年代末大陆的风云变幻中,金庸始终坚持自己作为独立报人的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他把自己看成是“文人论政”最后的一抹余光。
金庸的文学堪称母语的典范
金庸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在康熙年间达到科甲最辉煌的位置,他的爷爷出身进士,所以,他是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阶层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身上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但从小读的是新式学校,饱受了民国中西贯通的教育的滋润。他生逢乱世,少年时代遭遇抗日战争,流亡到浙江南部的丽水碧湖,在那里继续念完初中。开始念高中的时候,差一点被开除,所以又转学到衢州中学。
虽然,金庸没有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但无论是在重庆中央政治大学,还是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他都有幸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也有幸遇到了那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环境。在成长的年代,他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也显示出对人类文明热切的向往。他读了很多书,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在内,都曾是他最爱读的读物。
他年纪轻轻便进入杭州的《东南日报》,成为电讯翻译和记者。后来又考入上海《大公报》,成为电讯翻译,后来还有幸跟随胡政之先生一起创立香港《大公报》。一路走来,他亲眼目睹,亲身见证了民国在大陆谢幕前文人办报的最后时光。所以,当他后来亲自办报的时候,他把这种“文人论政”的传统发扬广大,在香港延续了百年中国言论史上的最后一脉香火。
他的武侠小说虽然是娱乐作品,但同样延续了中国历史传统,这种传统近可追溯到清代的“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更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和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更不用说民国时期他读得如痴如醉的那些新武侠。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香港殖民地环境中,他将这一新武侠小说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了武侠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的文字如此干净,如此生动,完全堪称母语的典范。即便放在一百年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金庸也可以毫无争议地排进前一百名。无论是他的社评,还是武侠小说,皆如此。

金庸的孤寂和落寞
一个作家,一个报人,无论他有多大的雄心壮志,或者有多少梦想,最终他的生命都要归于尘土。这一点,金庸从来都知道。1979年,当他的儿子在遥远的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他就对人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把握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就已经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有一次,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他的作品,当人们知道金庸也在现场,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他自己说,“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里一样。”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他毕竟是一个血肉之躯,他人生中有无数的缺陷和遗憾,也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但是,他同样有非常真实诚恳的一面。
有人说金庸是韦小宝,而不是乔峰或者令狐冲。但他却说,自己肯定不是乔峰,但也不是韦小宝或者陈家洛。活生生的金庸,又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一份狡黠,他身上有许多的复杂性。
他年轻时在重庆读的是外交系,后来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念的是国际法,在生命的黄昏,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念博士。在他香港宽大的书房里,放满了各种外文的精装书,但从骨子里,他其实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也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
他说他写的政论之所以常常能一语中的,只不过是从《资治通鉴》中读出来了对人性恶的基本把握。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也有香港商业社会带给他的特质,毫无疑问,它也是香港神话和香港奇迹的一部分。没有殖民地香港给他带来的这些环境,他不可能创造出明报集团,也不可能写出十四部风靡华人世界的武侠小说。

他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创造的江湖世界也是风云跌宕,是是非非如同现实世界一样变幻莫测。有人说,金庸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和《鹿鼎记》,都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其实,在荣华富贵、掌声和鲜花后面,作为一个个体生命,金庸也同样有他的孤寂和落寞,有他的惘然和茫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天龙八部》里照样有“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说,人生不可能永远美满,因而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即便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会空虚。
我常想,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过去,变成茫然。金庸,一个几乎拥有了世上一切的人,他给出的人生关键词竟然是“茫然”。
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样本
今天当金庸离世的时候,想起他一生留下的作品,包括武侠小说和那些尚未结集成书的成千上万的社评,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做的,他几乎达到了极限。在百年白话文学史上,他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
尽管,我对金庸的为人处事和他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那样认同,但是我仍然深深地感念,作为生在20世纪到21世纪这个特定时空中的金庸,他的故事仍然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非常重要的范例。他让世人知道一个人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极限,他可以两手写文章,两手都成为时代和众人的祝福。

他的武侠小说多少年来一直是无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乃至有人可以靠着金庸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成就一番自己的话语世界。虽然金庸自称是小人物,但他是做过大事业的小人物,他是在母语的时空中“射过雕”的英雄。我想起钱穆先生对他的学生辛意云教授说的一句话,“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大事中把握,评价历史人物主要应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和影响,而不能只看小事。”这正是钱穆先生常常念兹在兹的“同情之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说,金庸先生的一生,还真的是要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的离去,只是肉身的离去,他的文字不会淹没。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他给百年来中国母语时空留下的那些痕迹,都不会被抹掉。我们将继续地追问和寻找他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所怀抱的理想,最终也并未完成。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个成功者,但是在他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几分悲凉之气。
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的时候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一人而已。”也许金庸并不是那个“呼吸而领会”到悲凉之雾的宝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怀抱的那种对大中国的理想,仍然会被后世之人长久地追寻和讨论。
金庸曾在1973年4月22号的《明报》发表题为《最伟大的三结合》的社评,提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我想,他心中自有对现实忧患的清晰判断和危机感,并且也常有承担。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光阴,我们世人对他的要求可能更多,而他所做的已经力不从心,但就凭他在母语领域所做的贡献,他在中国历史上足以传世。
纪念和哀悼金庸的离去,愿他的灵魂安息!读他的文字,感念他的人,思想他的故事,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原标题:金庸是在母语时空中“射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