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由是枝裕和任编剧和导演、在戛纳斩获金棕榈奖的《小偷家族》(2018)在中国内地的上映,让这位日本导演走进了中国大众的视野。实际上,自他首部电影《幻之光》(1995)起,就有评论者给予是枝裕和“当代小津安二郎”的盛誉。
在历时八年完成的首部自传性作品《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中,是枝裕和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以下篇章即选自这本书的中译本,经新经典授权,由《新京报》发布。
三十二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
因拍摄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我和侯孝贤导演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每次来东京,我们都会见上一面。
这次见面,我向侯导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我即将执导第一部电影,不知您能不能把《恋恋风尘》的配乐人陈明章先生介绍给我?”侯导听后,爽快地将陈明章的联系方式给了我。他还告诉我:“你这个故事很适合送到威尼斯电影节。”因此电影尚未开机的时候,我就决定将《幻之光》送到威尼斯参展。
确定江角小姐为主演之后,一亿日元的资金依然迟迟未能筹集到。这个时候,TV MAN UNION 为纪念公司创立二十五周年,正在内部招募纪念企划项目。当我提出《幻之光》的拍摄计划时,重延浩社长对这个提议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提供了五千万日元的资金。
然而,剩余的五千万怎么也筹措不到。我甚至将企划书拿到东宝、松竹以及富士电视台,但都被拒之门外。现在或许难以想象,在影院和发行方都未确定的情况下,我就草草地开机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深信“只要看到完成的作品,大家肯定会竞相购买”,所以五千万日元先赊着,硬着头皮花了一亿日元拍摄。

《幻之光》分镜图
影片拍摄完后,我们信心满满地举办了试映会,但出于“由无名新人导演执导”、“无名新人女演员主演”、“讲述关于死亡的灰暗故事”这三重原因,没有一家发行方愿意投资。我这才意识到问题严峻,不免焦虑起来:“情况很糟糕啊,这样下去要是电影被雪藏,剩下的五千万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那时制片人心里肯定比我更加不安。
最终,我们等来了奇迹,三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当时参加试映会的TBS 制片人远藤环非常看好江角小姐,提拔她出演在东芝周日剧场播放的电视剧《光辉的邻太郎》。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东京剧场的制片人很喜欢《幻之光》,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影院上映,但CINE AMUSE 涩谷店很快将会开业,运营方之一是Cine Qua Non 电影公司,如果李凤宇社长喜欢你的电影,就能在他们的影院放映,这比在我们的影院放效果好很多。你不妨请他看看。”并将我介绍给了李社长。李社长来到位于调布的东京现象所观看了试映,一结束放映,他就对我说:“影院预计十二月开业,我想将这部电影作为影院的第一部影片放映。”
之后没过多久,又收到《幻之光》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的消息。对电影来说,和煦的风开始吹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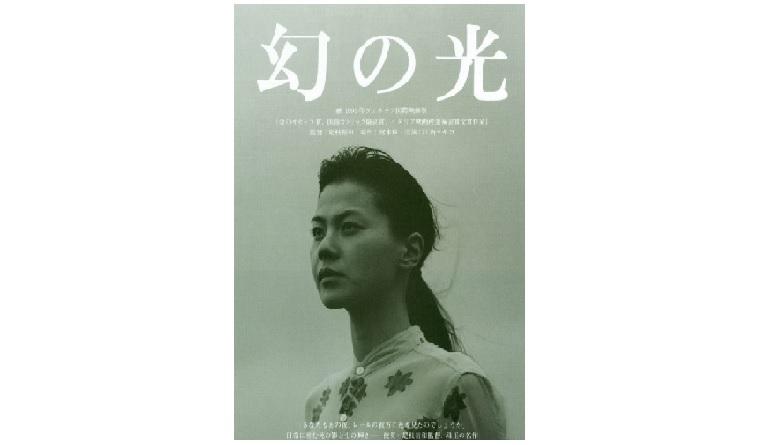
《幻之光》(1995)海报。《幻之光》入围第52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金狮奖提名。
毫无疑问,当时我有点自鸣得意。周围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喜极而泣。而我的心中却有一股毫无根据的自信,觉得这不过是循着自己的既定路线走,本来就会达到这个高度,甚至认为:“电影一旦公映,以后就能拍自己编剧的电影了。”
三十二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没有经验其实很危险。如果第一部电影有任何闪失,那第二部就毫无可能了。因此即便别人说我“不过是运气好”,也无可奈何。
母亲一直为我的前途担心
《步履不停》剧本的第一稿是在二○○六年秋天完成的,事实上五年前我已经写好了同名剧本的大纲。当时我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一九六九年,内容中自传色彩更为浓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一栋有点倾斜的老长屋中,家里有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爷爷,父亲整日沉迷于赌博,母亲要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那时正是石田亚由美的《蓝色街灯下的横滨》红遍街头巷尾的时候。平时在家里毫无存在感的父亲,在台风来临之际,用绳索将屋顶固定住不让风吹走,然后在所有的窗户外钉上白铁皮。原先的剧本写的就是这一天发生的故事。
但是,制片人安田先生说:“这个故事你到六十岁再拍也无妨,不用急着拍。”所以先开始了《花之武者》(2006)的拍摄。
制作《花之武者》期间,母亲生病住进了医院。我只能利用拍摄和剪辑的间隙去医院看她。在二○○五年电影即将上映的时候,母亲去世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即使不是自传,如果此刻不讲一讲母亲的故事,我就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母亲从生病倒下到去世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一个逐渐走向死亡的亲人,精神上承受的折磨是非常残酷的。母亲刚住院的时候,我正在拍摄与医疗相关的纪录片,所以认识一些医院方面的人,也懂一点医疗常识,相信母亲可以很快恢复往日的健康——只要她换到更好的医院,好好做康复训练,就可以回到家里继续健康地生活下去。然而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来得及为她做。
母亲一直为我的前途担心。《下一站,天国》(1998)上映后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我的名字开始被观众熟知,可她依然为我的生计担忧。《幻之光》和《下一站,天国》她都看过,但她在《无人知晓》(2004)杀青前便病倒了,没能看到。我将《无人知晓》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新闻报道贴在了母亲病房的墙上,但她大概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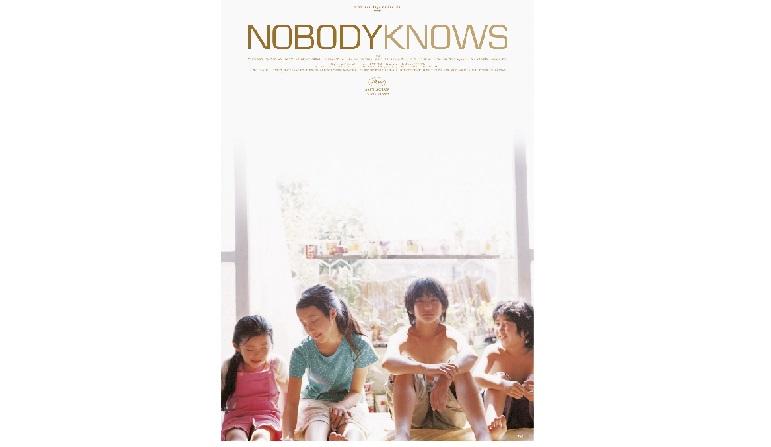
《无人知晓》(2004)海报。电影入围第57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金棕榈奖提名;柳乐优弥则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我本该再为她做点什么。至少应该让她看完《无人知晓》,这样她或许会走得安心点。如果她再晚半年病倒的话……我内心的悔恨酝酿出了《步履不停》(2008)的主题——“人生总是有点来不及”。
我将这句话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开始创作剧本。
家人难以替代,却很麻烦
由自己来评论自己的电影,有点难开口,但《步履不停》制作完成的时候,我自认为“拍了一部很满意的作品”。这是我迄今为止拍得最轻松、最流畅的电影。
在《步履不停》之前,我身上多多少少还带着出身于电视行业的自卑情结,“电影究竟是什么”,会不自觉地把这类追问电影类别和方法论的思考带入作品中,不免有“形而上学式的思考”的倾向。但是在《步履不停》中,我没有追求任何方法论。

《步履不停》(2008)台湾上映时译为《横山家之味》,影片获第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
我内心有一套判断影片是否属于家庭电影的标准。
人们常说“正因为是家人才互相理解”、“正因为是家人才无话不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是家人才不想让他们知道”、“正因为是家人才无法理解”反而更符合现实。山田太一先生的家庭剧讲述的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向田邦子女士描绘的家庭故事中,男人的安栖之处往往也在家庭之外。因此,我想试着讲述自己独有的真实的家庭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难以替代,却很麻烦”。拍摄家庭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是同时讲述这两方面,《步履不停》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做到了这一点。
创作者的生命
来到大学里,经常会有学生问我:“影像是自我表现,还是传达信息?”
至少对从拍摄纪录片进入影像世界的我来说,作品绝不是产生于自我之中,而是产生于“我”与“世界”相接的地方。尤其是通过摄影机这种机器生成的影像,这个特质就更加明显。纪录片的基础不是为了传达自己的信息,而是“为了与世界相遇才打开摄影机”,这大概也是与剧情片最大的区别。
大岛渚导演在年仅三十二岁的时候说过:“一个创作者能创作出对一个时代产生意义的虚构作品的时间,至多不过十年。我的十年已经拍完了。”所以不久后,他宣布开始拍摄纪录片。如果没看准该在何时如何更换血液,维持新陈代谢,创作者和电影导演就会陷入自我模仿的窠臼,作品也会越来越无聊。大岛渚导演的这番话,我一直引以为戒。
当然,像埃里克· 侯麦这样长寿的导演是例外。他不管是在七十岁还是八十岁的时候,都在拍摄新颖而充满朝气的作品。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在这一点上与他非常相似。
也有像杨德昌导演这样的类型,在拍完《恐怖分子》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两部杰作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完成了集大成之作《一一》。我感动于创作者竟然可以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
侯孝贤导演则属于一鸣惊人型。侯导早期拍的基本是田园牧歌式的作品,之后也拍摄了不少讲述青春的片子,其间陆续拍摄出了《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和《悲情城市》这样成熟的杰作,在亚洲甚至出现了“八十年代是侯孝贤的时代”的评价。之后,他仍不断尝试改变,丝毫不畏惧转变自己的风格,这也是我无比敬佩他的地方。

左起:贾樟柯、侯孝贤、是枝裕和。
大岛渚导演的话如果是正确的,那放在我身上看,我是否已经经历了那“十年”呢?如果正在经历,今年又是哪个年头呢,抑或是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我时常在思考这些事情。不管是好是坏,所幸我没有固化自己的风格,我丝毫不担心因为丧失想象力而拍不出东西的情况。
《比海更深》(2016)倾注了我那时全部的爱
在《步履不停》和《比海更深》这两部作品之间,我和阿部宽都成了父亲,也都迈入了五十岁的年纪。而且影片的主人公是儿子和丈夫的同时,也是一位父亲,相比《步履不停》,处于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导演和演员能像这样随着角色的人生成长和老去,应该算是难得的幸事吧。在步入六十岁的时候,希望能跟阿部宽再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电影导演究竟是作家还是职人?不同的导演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于我而言,电影不是产生于自我的内部,而是经由与世界的邂逅诞生的。
借用前面的比喻,在拍摄《奇迹》、《如父如子》、《海街日记》的时候,我作为“料理人”的意识很强。拍摄《比海更深》时,我感到自己回归了“作家”的角色。通过前三部作品,我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宽广,但一味拍摄那种电影会累积很多压力。因此,能拍摄这样朴素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如果还能继续享受这份奢侈,作为电影导演也能积累更多宝贵的经验(但愿能持续下去)。
在《比海更深》中,我倾注了对“家庭剧”所有的思考。不是源自这二十年来作为电影导演的经历,是出于对孩提时代喜爱的电视剧的偏爱和尊敬,才有了这部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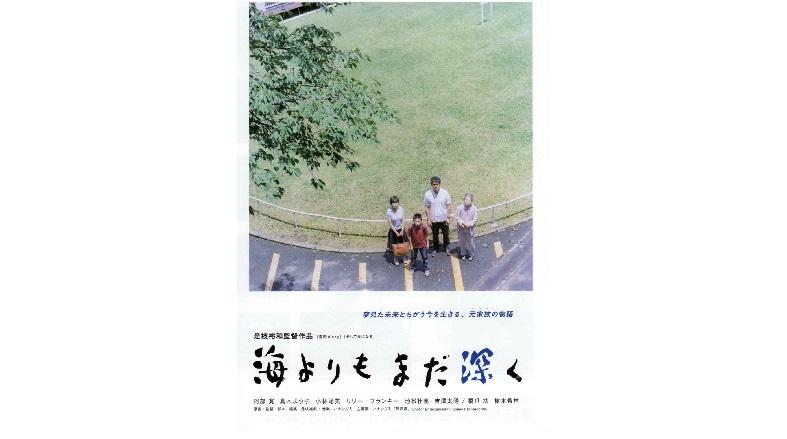
《比海更深》(2016)海报。影片入围第69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获一种关注大奖提名。
这是我基因中个人色彩最浓厚的部分,我有这样的认知,同时也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或许这也是自负的表现。这部电影大概不适合用“集大成”或者“代表作”这样看起来全力以赴的字眼形容。相反,作为创作者,我从头到尾都被一种放松的力量指引,才能让某些东西显露出来。
这或许就是爱吧,是我对家庭剧、对福利房社区、对生活在那儿直到去世的母亲,还有对主人公因无法过上想要的生活而后悔和灰心的爱。这一半也算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能带着这样的感情去观赏。
爱是可以通过影像传播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大学时代,在早稻田的ACT 小剧场看完费德里科·费里尼导演的《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之后,那时我十九岁。爱的多少、质量和纯度或许无法与他人比较,但这部《比海更深》倾注了我当下全部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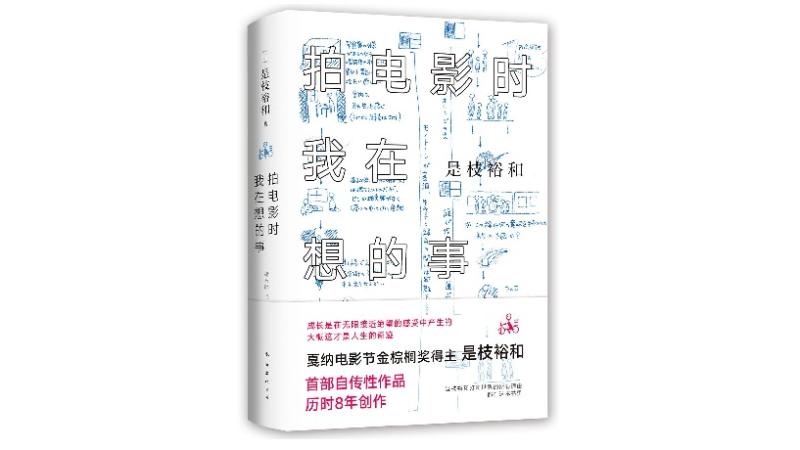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日)是枝裕和,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11月
本文选自是枝裕和《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中译本。
编辑:寇淮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