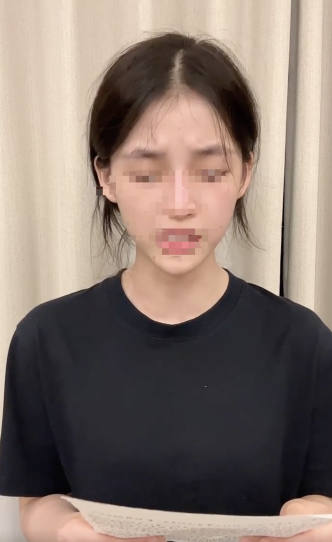作为一名自认“走在时代前列”的90后,邱小燕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封建”挂上钩。春节前与同事们聊起过年习俗时,邱小燕无意中提到自己每年会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引来了众多好奇的目光。
“怎么磕?”“什么时候磕?”“顺序有什么讲究?”
“今年磕头的时候能不能拍个照片发来看看?”邱小燕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习以为常的这种拜年礼仪如今越来越“小众”,甚至在不少人看来难以接受。“感觉不舒服甚至有点屈辱”“只能接受给逝者磕头”“这种封建落后的形式该取消了”……
早在两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过年时给长辈磕头的习俗,长辈一般要给磕头的儿童压岁钱或是糖果、玩具等小物件作为“赏赐”。如今,拜年的方式越来越简易,但山东、河北等地仍然保留着较大规模的磕头拜年礼节。大年初一,人们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到村里或者家族里辈分大、威望高的人家里磕头,从凌晨4、5点持续到中午。有网友表示,自己辈分太小,亲戚太多,算算要磕100多个头。
尽管有人认为磕头这种方式奇葩、过时,但支持将之延续下去的声音也有不少。有人单纯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哄老人开心;有人觉得磕头能够更好地表达对长辈的尊重和感恩;有人则表示这是一种民族传统,需要传承。而对于邱小燕来说,磕头拜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拿红包前的固定步骤。
“去给爷爷磕个头,然后爷爷给红包。”邱小燕记得,小时候自己在红包的“诱惑”下懵懵懂懂地就照做了,并不知道磕头是什么意思。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众人的注视下“五体投地”变得有些尴尬。高中时,邱小燕一度觉得,宁可不要红包了也不磕头。然而大年初一,面对爷爷奶奶期待的目光和父母的催促,邱小燕还是扭扭捏捏地顺从了。她回忆说:“虽然算不上被强迫吧,但也不太情愿。”
与听话的邱小燕不同,她的妹妹邱小莲在青春期时表现出对磕头拜年明显的排斥。常常嘟着嘴站得远远的,谁劝也没用。最后爷爷奶奶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没事儿,不用了。”然后把红包塞到邱小莲手里。邱小燕每每为此愤愤不平。
好在家族里有位表叔大飞,每年磕头磕得敞亮,让邱小燕心里稍感平衡。自她有记忆起,这位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每年大年初一进屋便冲到长辈面前,咣咣咣三个响头磕下去,还会配上一句响亮的“过年好”。邱小燕的父亲回忆,当年大飞的父亲便是如此,一直到50多岁都郑重地给父母磕头拜年,言传身教之下,大飞做起来也不含糊。他感叹:“这是一种家庭教育,是一种家风的传承。”
也正因如此,每个不同的家庭都可能有不同的拜年方式,有的磕头,有的鞠躬,有的问候,有的共同举杯,无须追求统一。邱小燕的妈妈就从不跟着磕头拜年,她从小习惯了和父母互相问好的方式,觉得磕头过于形式化,对长辈的尊重不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倒是邱小燕在成年后,对磕头拜年有了新的体会。“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现在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长辈的感恩。”由于在外地工作,邱小燕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每次都觉得父母老了不少。“平时工作忙,和父母的沟通交流不是特别多,对他们的感激和愧疚也不知道怎么说。过年了真心地磕个头,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表达吧。”
邱小燕觉得,等自己将来有了孩子,可能还是会鼓励他磕头拜年,但一定不会忘了给予他解释和引导。比如这种传统礼节的历史和演变,比如大飞叔的故事,比如自己对于磕头的理解。“至少不能让他觉得,磕头就是为了换个红包。”
(文中邱小燕、邱小莲、大飞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倓秋 编辑 潘灿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