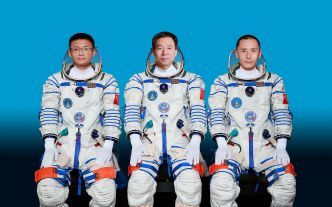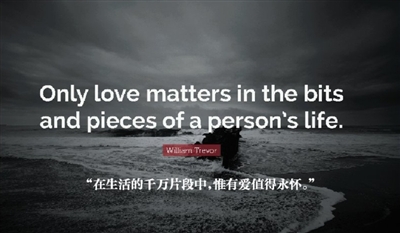

威廉·特雷弗(1928-2016)
爱尔兰当代文学大师,被《纽约客》称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威廉·特雷弗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雨后》、《出轨》等集子展示了大师级短篇小说家的素养。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在这须臾中,他描绘出各色人物的纠结心灵,同时给予怜悯与宽解,故事因此有了温度。这些短篇让特雷弗跻身契诃夫、莫泊桑等人的行列,被《纽约客》称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爱尔兰的契诃夫”这一头衔也成为人们对他的共识。这些称谓表达了人们对特雷弗短篇小说造诣的认同,也在无意间造成了某种忽略——特雷弗也曾写下不少出色长篇,《费丽西娅的旅行》便是其中之一。
失望聚成石头
“爱”掩盖不了黑暗真相
关于长篇和短篇,特雷弗有自己的明确见解。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他说:“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幅复杂精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短篇小说就是一幅印象派绘画……长篇小说模仿生活,短篇小说是骨感的,不能东拉西扯。它是浓缩的艺术。”
两者有不同,特雷弗没有“厚此薄彼”,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写下无数短篇,也写下大量长篇,生前出版了16部短篇小说集,也有29部长篇面世,《费丽西娅的旅行》便是代表作之一。
即便26岁就移居英国,特雷弗“骨子里永远都是爱尔兰人”,这在他的小说中有鲜明印记,《费丽西娅的旅行》也不例外。费丽西娅,一个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小镇姑娘,未谙世事,只身前往英国伯明翰寻人。“她一个劲地恶心呕吐。”小说的第一句为后来的一切埋下刺痛的伏笔。当然,这次旅行的初衷可被形容为怀有身孕的未婚姑娘的寻爱之旅,但其中的绝望与无助并不能被“爱”掩盖。
在哥哥的婚礼上,伴娘费丽西娅与回乡探望母亲的约翰尼·莱斯特偶然相遇,陷入爱河。英俊的脸庞,悦耳的声调,意料之外却滚滚而来的爱的誓言,费丽西娅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那时,身体的欢愉只是爱情的附庸。而当小伙子再次远走,没留下任何明确的联系方式,自己的身体又有了变化时,身体带来的恐慌浮上水面。在费丽西娅看来,爱情没有逝去,也许怀孕这一事实还曾让她的爱情更坚固,可恐慌和羞耻已在所难免,正如父亲的咒骂:臭婊子。
在遭遇无望,遍寻而不得爱人身影的间歇,费丽西娅时常回想起生活原本的样子。在那个经济萧条的爱尔兰小镇,她与曾祖母挤在一屋,每天面对的是性格强硬、沉湎于爱尔兰反英战争的父亲,流连酒吧、大大咧咧的三个哥哥,还有早早死去的母亲——她的身影更多地在梦中出现。这些活着或死去的人组成的不是温馨,而是孤独。这一人类命题或许每个人都难逃脱,费丽西娅只是众生中的一个。心灵无依,上班的肉厂倒闭,爱人的离去,这一切叠成厚密的黑暗,让她的出走成为必然。
如果没有一丝光,就去寻找,或者说,不得不去寻找。费丽西娅的光,如果有的话,只能是约翰尼·莱斯特。但事实上,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一个贪得一时欢愉便想销声匿迹的年轻士兵。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寻找,费丽西娅执着过,在小伙子给出的半真半假的地理位置的指示下,在各个小镇的街道上急切奔走,见人便问“割草机制造厂”在哪里,最终,失望聚成石头,阻住了前路,她意识到,是时候回去了。可惜,回去的路已被堵死。
“我并不相信黑与白,我相信灰色的阴影和朦胧。”
阴影靠拢内心
阳光照亮塌陷的生活
像复调的另一声部,小说的第二章出现的是一个名叫希尔迪奇的人,五十四岁,迷恋美食,满身肥肉,针孔般的眼睛,标准的笑容,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他笑容可掬,展现了外向达观的秉性。可是,在他孤寂之时,希尔迪奇先生往往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阴暗面靠拢。”这时,他变成地道的猎人,具有洞悉猎物心理的高超本领。他用谎言缜密布局,慢慢端起枪口,一个个迷失的羔羊——那些失意的女人——在瞄准镜下游走而不自知。她们都曾在尘世生活中挣扎,最无助时看到了那副标准的笑容,得到宽慰和依赖,也得到捆绑。等想挣脱绳索时才知道,事情已变了样,至少在希尔迪奇那里已经变了样。
一个心理变态者的内心难以捕捉。特雷弗不动声色,平静叙述,用精准的对话和心理描写渐渐抵达真实,一个杀人者的样貌逐渐清晰。从谎言的编造,到对费丽西娅心理上的强烈需求,特雷弗像个心理学家,把希尔迪奇的内心完全展示给了读者。
面对这样一个杀害多名妇女的凶手,特雷弗给予的不是道德批判,而是理解和怜悯。小说家V.S.普里切特说:“如同他的榜样契诃夫,威廉·特雷弗简洁、耐心而真诚地展现生活真相,不加任何道德说教。”在洞悉了人性之复杂、世事之艰难后,道德说教能带给我们的东西实在不多。特雷弗向我们展示了希尔迪奇,一个杀人犯,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父亲一无所知的孩子,一个被浮夸放荡的母亲嘲笑的少年,一个心怀军官梦想而因身体缺陷被刷掉的小伙子。他不择手段想得到的,只是一段可依靠的关系,正如他在通过花言巧语说服费丽西娅打胎时想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无论如何都否认不了。”
问题在于,他一心想确定的“关系”却非她们所想。他带她们去医院治疗上一个男人用皮扣抽打出的伤口,替她们还债,而她们要的只是暂时的安慰,擦干眼泪的一只手,等泪痕干了,她们就要去重新过一种没有他的新生活。“他为她们做了这一切,把她们留在身边,这让他感到快乐。”曾经,一个杀人者的快乐是付出。
特雷弗说:“我并不相信黑与白,我相信灰色的阴影和朦胧。”费丽西娅不是绝对的“白”,希尔迪奇也非绝对的“黑”,二者都是灰色的阴影。
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特雷弗却生于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家庭,对宗教的思考是他小说中的重要议题。费丽西娅无路可去时,曾遇到兜售宗教的黑人妇女卡利加里。这个宣称人死后的世界极其美妙的妇女每日清晨都会敲响镇上人家的门,劝人入教:“我们的圣父希冀建造一座人间天堂。我们的圣父承诺永生。回报仅是我们的顺服。”这些话没有打动费丽西娅,打动她的是那人可以给自己提供睡觉的一席之地。教徒聚集的地方叫聚会堂,里面白人、黑人、女人、孩子,不一而足,初见费丽西娅时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友善,听说她的遭遇时展示出无限的宽容与爱怜。这些曾让费丽西娅心怀感激,可当她发现钱被偷而去询问时,那些人的脸顿时阴沉,卡利加里开始觉得她“不怎么样”。误解随随便便就击垮了那群拥有崇高信仰的人。
吊诡的是,当费丽西娅成为唯一一个在希尔迪奇手中逃走的人后,卡利加里带着她的宗教宣言前来宽慰他。她认为,是这个爱尔兰姑娘搅扰了他的正常生活,而希尔迪奇最害怕的,正是有人知道自己曾和费丽西娅产生过交集,从而受到非议,损坏自己的声誉。卡利加里三番五次送去慰藉,却不知她反复提及的“爱尔兰姑娘”成为希尔迪奇的梦魇。那些被他杀掉的女人在眼前一一滑过,母亲遭到的背叛涌回脑海,一个梦魇牵出所有梦魇。最终,希尔迪奇上吊自杀。当一个人的心灵无法得到丝毫慰藉,死亡便成了唯一出路。然而,这一场景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宗教本应拯救灵魂,却适得其反。宗教真的能给人类带来安宁?特雷弗似乎不这么认为。
面对生活的塌陷,面对孤独与生死,特雷弗克制沉稳,忧伤但不绝望。在费丽西娅选择流浪街头度日后,特雷弗把她带去大海,使她微微仰起头,“让阳光温暖另一侧脸颊”。
《费丽西娅的旅行》
作者:(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译者:郭国良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3月
一个未婚先孕的爱尔兰少女,一趟绝望的寻人之旅,演绎了一场人性中良善与压抑的欲望纠缠的生命悲剧。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