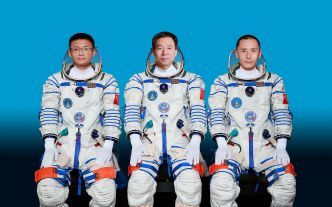撰文 | 楚若冰
随着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胜利,一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也传遍了世界。特朗普团队卖掉了数千万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帽子,无论在哪个选举集会中都能看到民众戴着相同的红帽子。有专家分析,特朗普的成功“上位”,离不开“让美国再次伟大”起到的巨大影响力。这句仅由四个英文单词构成的简单口号,究竟凭借什么发挥了作用?

特朗普戴着写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红帽子
在英国文化学者约翰·斯道雷看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其实唤起了美国大众对于美国历史的某个“黄金时代”的集体性缅怀。特朗普让人们相信,美国曾经伟大过,而他则会带领美国回到那个时代。但是,所谓的“黄金时代”真的存在吗?在斯道雷看来,这不过是存在于美国人幻想中的一个乌托邦。
大多数中国人或许都熟悉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而与“桃花源”含义相近的“乌托邦”这一概念,在西方世界引领着从未停止过的讨论。那么,“乌托邦主义”究竟是什么?在今天,它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和思考?
7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徐德林和刘方喜研究员联合主持,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斯道雷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斯道雷先生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激进乌托邦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
列侬和小野洋子的“激进乌托邦主义”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人们便从未停止对于神秘而美丽的乌托邦的探索。发展到今天,乌托邦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议题与研究领域,也由此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主义和乌托邦式实践。
在乌托邦的世界中,人们或是展望未来,期望在未来找到一个完美之地;或是回顾历史,怀念一个永远只存在于过去的“黄金时代”。而约翰·斯道雷先生关注的“激进乌托邦主义”,相较于“过去”或“未来”,更重视“现在”, 即“此时此地”(here and now)。
那么,“激进乌托邦主义”究竟指什么?斯道雷表示,相比于我们更常见到的“蓝图乌托邦主义”对于未来世界的无尽畅想,“激进乌托邦主义”致力于把我们的当下“陌生化”,从而破坏人们心中对于“真实”的认知,打碎人们生活中的那些“必然”和“不可避免”。
激进乌托邦主义者们相信,当我们明白,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只是当权者为我们编织的一个“真实”,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生活并非不可改变。激进乌托邦主义希望我们相信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是可能的,改变现状也是可能的。只要人们相信并向往改变,人们就会愿意行动起来。
为了进一步阐释“激进乌托邦主义”,斯道雷讲述了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作为例子。为了抗议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他们在美国各地展出了一系列反战海报。
他们希望这些海报能够激发人们对于和平生活的美好想象:如果战争结束了,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他们相信,当人们喜爱自己想象出的画面时,人们就会对其产生向往,并愿意为把想象变成现实而奋斗。在斯道雷看来,两位艺术家的这一反越战运动,是“激进乌托邦主义”的典型实践。

约翰·列侬、小野洋子和他们的反战海报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
是对“黄金时代”的乌托邦想象
当被问及是否也存在着一种与“激进乌托邦主义”相对应的“保守乌托邦主义”时,斯道雷表示了肯定。事实上,在他年初刚出版的《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一书中,斯道雷就以特朗普的2016年竞选活动为例,探讨了一种“怀旧”的存在。这种“怀旧乌托邦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保守乌托邦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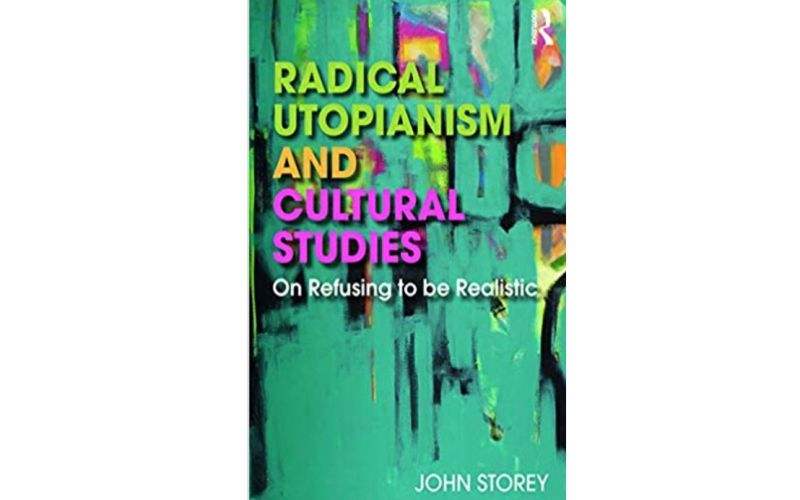
《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约翰·斯道雷著,劳特里奇出版社
“怀旧乌托邦主义”永远关注过去,期望通过某种神秘仪式,回到过去的某个完美世界。在斯道雷看来,不管是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中的“再次”,还是英国脱欧运动口号“夺回控制权”中的“夺回”,其实都强调着一种对于过去的回顾和向往。
这些口号向人们勾画了一幅有关过去的美好图景,即在过去的某个时期,英国是拥有控制权的;在过去的某个时代,美国是伟大的。在这一框架下,不管是孔子对于尧舜时代的向往,还是今天许多人对于汉唐时期的缅怀,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怀旧乌托邦主义”。
在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一书中,他驳斥了部分学者对于某个只存在于旧日乡村中的“黄金时代”的缅怀。在他看来,所谓的“黄金时代”永远只存在于某个更遥远的过去。当你真的回到某一个“黄金时代”,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代的人也在缅怀着之前的一个“黄金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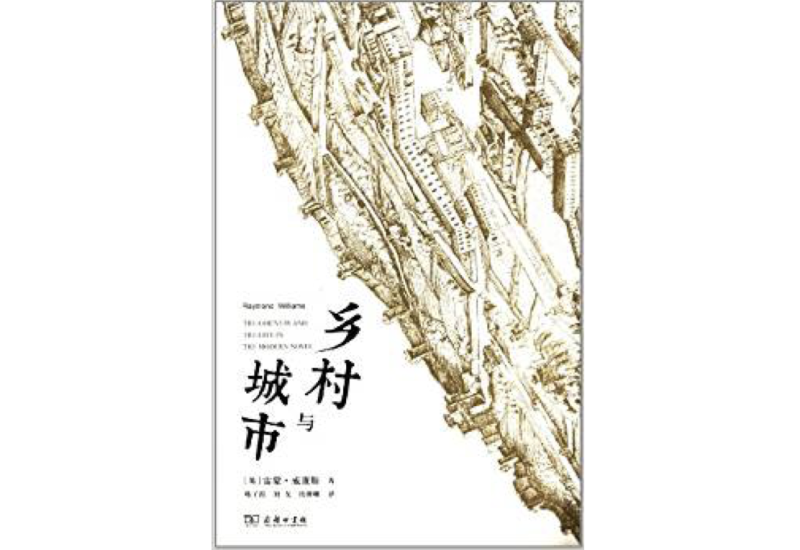
《乡村与城市》,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 / 刘戈 / 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版
从来没有“黄金时代”,
但人类的向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威廉斯认为,保守主义者对于过去的恋恋不舍,只是因为不愿改变现状。但是,这个永远美丽、永远神秘的“黄金时代”,真的存在吗?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
许多人认为,“欲望”反映了人性的恶,所以该被压制。但斯道雷强调,正是欲望的存在,让我们成为“人”,所以欲望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各种层出不穷的广告,都试图通过满足人们的欲望,来实现对人类的控制:“只要你购买足够多东西,你所有的梦想都会成真。”然而,人类的欲望永远无法被彻底满足。因为我们总在寻找着更好的东西,也渴望着“此时此地”之外一个更美丽的新世界。
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作品《乌托邦》一书中把这种对于美好世界的欲望起名为“乌托邦”,这也就是“乌托邦”的正式开端。莫尔发明的“乌托邦”(utopia)一词源于希腊语。Topos(topia)的含义为“地方”,而字母u既指代希腊语中的“eu”,意为“好、快乐”,也指代“ou”,意为“不存在的”。所以,“乌托邦”一词指代了“一个不存在的美好世界”。

《乌托邦》第一版中的插图
在斯道雷看来,欲望和乌托邦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管是威廉斯认为的“乌托邦主义是欲望的关键载体”,还是E.P.汤普森的“乌托邦解放了欲望”,其实都是在论证“乌托邦主义”和“欲望”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激进乌托邦主义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是“对欲望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desire)。只有首先引导人们对某样东西产生欲望时,才能在接下来号召人们去采取行动。“激进乌托邦主义”相信,通过对欲望的教育,白日梦也可以变成有意义的希望。当欲望变成人们对未来的某种期待,人们就会开始采取某种实际行动。
在激进乌托邦主义中,人类的欲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鼓励人们去畅想一个“向往的生活”,去渴望更美好的世界,并为之付诸行动。尽管人们对欲望多加批判,“激进乌托邦主义”却肯定“欲望”的积极作用。因为,欲望可以引发现实的变革,它是推动历史前行的一种强大生产力。
乌托邦式的欲望追求
源于我们无法摆脱“缺失感”的纠缠?
斯道雷说,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同欲望抗争的一生。我们羞于承认自己的欲望,却也不得不妥协于欲望的控制。欲望,成了人们无法摆脱的原罪。而雅克·拉康关于“缺失”的论述,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拉康相信,每个人自出生起就是不完整的,我们的欲望来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缺失感”。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上,雅克·拉康进行了重新解读。在他的分析汇总下,人类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不完整的个体,时刻处于一种“缺失”(lack)的状态中。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寻找能填补缺失的方法。大多数人对于浪漫关系的渴求,其实也源于这种与生俱来的“缺失感”。我们期望能通过对欲望的满足,使我们重新回到最初母体中那个“完整的自我”。

雅克·拉康
斯道雷表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适用于解释“乌托邦主义”。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在某个时刻对乌托邦产生过欲望,这可能也正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一“缺失感”。人类对于这个并不存在的“美好世界”的追寻和向往,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摆脱“缺失感”的纠缠。
正如在拉康学说中,人们一生都在不断追寻一个圆满的自我一样,“激进乌托邦主义”也认为,人们不应停止对更美好世界的追求。乌托邦也代表了一种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望,我们走在一段没有终点的旅途上,永恒地追寻着它。
“人性从根本上是有缺陷且不可改变的”,这是保守主义者们常用来反对激进变革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因为人类的“性本恶”,所有试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计划都将以失败告终。
与之相反的是,“激进乌托邦主义”认为:“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人的本性绝不是一成不变的,21世纪的人类与5000年或10000年前一定大不相同。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人性在不断改变并进步。

约翰·斯道雷在学术研讨会现场
斯道雷介绍道,在激进乌托邦主义者看来,人类希望改变世界的这一“乌托邦式欲望”,正是人性中最好的部分之一。因为它促使我们去想象新的可能性,也传达着希望。因为相信终有一天一个叫做乌托邦的美好世界会来到,所以我们才能有不断前进的动力。
激进乌托邦主义在今天的意义:
或许不能直接改变世界,
但可以引导人类去追求变革
在介绍历史上的“激进乌托邦主义”实践时,斯道雷提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一个名为“掘地派”(The Diggers)的嬉皮士群体。“掘地派”是在旧金山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激进的年轻人群体。他们向当地社区发放免费的食物,但想要获得食物,首先要跨越一个所谓的“自由参照框架”(Free Frame of Reference),即一个涂满鲜艳色彩的木架。“掘地派”们认为,当你跨越这一框架后,你就可以开始想象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自由的。

一名“掘地派”成员在发放食物
“掘地派”的一名前成员Peter Coyote表示:“(越过框架)就像一个邀请,你由此进入了一个没有领导的自由世界。你可以开始重塑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对自由的定义。我们的文化束缚了我们,而要改变这种束缚,就必须要想象并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当人们体验了新的生活方式并享受其中,人们可能就会开始为之奋斗。”
“激进乌托邦主义”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它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欲望,它让人们以全新的视角去想象“今天”。有关于生活的一切变革都是如此,它必须首先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然后才有可能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被实现。
在斯道雷看来,“激进乌托邦主义”或许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却可以引导人类去追求变革。对于乌托邦的追寻,可能会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人类旅程,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抵达那个美丽彼岸。但我们仍需保持对于乌托邦的欲望和希望,因为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它既推动着过去的种种变革,也会继续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
“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拥有‘希望’和‘欲望’。除非我们确信,我们已走到历史的尽头,并已耗尽人类的全部潜力,否则早早就放弃‘希望’和‘欲望’的力量,实在为时过早。今天,我们不应一味批判‘激进乌托邦主义’的不切实际,而应感激它赋予我们的全新思考、写作和行为方式:拒绝现实,追寻不可能。”斯道雷说。
撰文丨楚若冰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