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余雅琴
每一个在1990年代度过青春的人都会喜欢香港电影,那里面有江湖,有豪情,有都市,有市井生活,满足了物质和娱乐还相对匮乏的时代里我们想要的一切幻想。
在众多的香港导演里,陈果则始终是一个异数,他的电影告诉我们,香港除了中环白领和帮派斗争,有着那么多和我们一样的小人物,除了江湖义气,还有那么多无可奈何的颓然与妥协。他的作品不像我们熟悉的香港电影,却又似乎比那些更加“香港”,他准确捕捉到世纪末的情绪,让他的电影始终有种惘惘的危机感,他镜头下的人物常常飞扬起又跌落,唱着一曲挽歌。
《香港制造》里少年中秋成为很多人青春的代言人,而《榴莲飘飘》里的“港漂”阿燕更是与如今的“北漂”遥相呼应。二十几年过去,这些年轻人不论老去还是死亡,历史都已然成为过去。陈果的电影关注的是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而不自知的人,是那些时代飘摇中的畸零人。他说自己只是“偶然”拍了一部又一部“社会片”,而这些“偶然”中又有着一个创作者的必然坚守。

《香港制造》剧照
与许多香港导演不同,陈果没有选择在中国电影最热的时期“北上”拍片,他不多的几部商业片也备受非议。这一次,他作为第八届香港主题电影展开幕影片《沦落人》的监制来到北京,同时放映他的名作《细路祥》。或许是不谋而合,影展的主题是“师徒传承,前辈后生”,而陈果就是被师徒传承式的香港片场培养起来的,从事过几乎所有电影工种,才有机会成为导演。
抛开那些获得的奖项和提名,陈果到底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导演,他是被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教会的导演,成长在片场,却终于还是成为片场的“叛逆者”。他总说自己想拍商业片,却总是失败去拍艺术片;自己想要生存,却一定要表达自我。
或许,正是因为在商业和艺术的夹缝中,在现实和理想的鸿沟间求生存,陈果的电影追求电影的可看性,好看之余才夹带私货,用隐喻书写大时代。而这些将说未说的感受,到底是评论家的过度解读,还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呢?陈果只是留给我们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陈果的电影可以被看做研究香港这座城市文化心态的最佳影像文本,他描摹了一个世纪末的城市寓言,让彼时的内地观众看到未来的自己。

陈果,香港导演、编剧、制片人,1959年出生于广东,代表作有《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榴莲飘飘》《细路祥》等,曾获第3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我的电影都是偶然成就的”
新京报:我第一次看《香港制造》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当时在上中学,那会儿内地青少年的处境虽然和电影里面表现的香港很不一样,但是依然感觉特别有共鸣。
陈果:对。年轻人的确会有那种共鸣感,无论什么时代都会有青春的“勇者无敌”的感觉。
新京报:你当时拍这个片的时候,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
陈果:我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当时香港的社会氛围和现在很不一样。我是1996年拍的《香港制造》,那时候只有成年人在担心回归之后的各种制度的改变。年轻人是完全不管的,没有成年人的浮躁和忧虑。
我当时的直接感觉是香港社会和家庭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在主流电影工业里,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没人拍这种大时代之下的骚动?就算有人拍也只是想去借那个时代的一些气氛,最终还是主流电影的东西。
于是我就有了《香港制造》那个故事,当时我想做一个跟社会有关系的题材。但是,“回归”这个议题是很奇怪的现象。按道理来说,“回归”在我们中国人这边是很正能量的,但那个时候又不完全是。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太大野心,是完全把《香港制造》当成反映家庭的变化来拍。那时候,很多香港工厂已经开始转移到内地城市,像东莞这样的地方。也有很多跨地区的婚姻和男女关系,于是出现了很多家庭结构上的变化。当时香港的社会是挺复杂挺热闹的。

《香港制造》剧照。
新京报:我发现你的作品一直非常关注时代,关注香港这座城市在时代当中的变化,还有很多的隐喻。《香港制造》之后紧接着又拍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后来又拍了像《榴莲飘飘》这些作品。这些如果去分析的话,都有某些隐喻在,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自觉性,还是说被评论家解读出来的。
陈果:是偶然的。我在拍《香港制造》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东西引发这么一连串的效果。我那时候在主流电影界也开始做导演,但是,做了两部以后觉得挺不舒服。我决定要拍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电影。
当然现在重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么冷静。我们是在主流电影里成长的,我没有受过任何艺术电影的教育,甚至没有人去提醒你怎么拍,我们是真的乱拍。《香港制造》的成功启发了我,原来用这手法去拍社会问题还是有一些人看的,不是完全没有观众。
《香港制造》拿了很多奖,偶然的东西就变成了必然,本来真的只是我偶然想拍个关于回归的故事就算了。随着影片的成功,我就继续拍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这一系列电影。做出一些成绩之后,香港也没有别人拍这样的电影,我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还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开创了另外一片天空,这样我就慢慢把风格定型了。
《榴莲飘飘》之后我就在想,如果这样拍写实片,也很难找到故事。虽然社会每天很多事情可以拍,但是我找不到自己需要的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拍社会问题片,一边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还要找到一个娱乐观众的层面。其实我是一直希望拍所谓沉重的题材,但也要有可看性,有娱乐的一面。
我这种类型的电影是很难的,因为香港没有这种电影的市场。除了一拨文青喜欢,受众很窄。

《榴莲飘飘》剧照。
新京报:我知道你是在内地出生,然后在香港成长的,不知道这个经历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陈果:当然是有的,这种“根”的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说成长,《榴莲飘飘》中我成长的部分比较多一点。我去香港的时候还很小,很多东西记不清楚。香港其实是一个没有根的城市,是一个移民城市。我们当时想通过香港去南洋,但到香港后没有走,像我们这种家庭特别多。
当我在香港住下来,无缘无故又住了几十年之后,我发现在这里蛮适应的,而且它有一种洋气,跟我们小时候的环境完全不一样。香港人拍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内地拍的那么沉重。虽然我的电影还是有一些阴暗面,可我想在里面放一些幽默进去,这或许就是香港海派的地方。
很多人问我到底有没有受什么导演影响,我小时候看了很多“法国新浪潮”、“日本新浪潮”的电影。刚入行的时候,我又很幸运地就见证了“香港新浪潮”那个阶段,但是,那个阶段又和“台湾新电影”不一样。
因为“台湾新电影”关注比较人文的东西,“香港新浪潮”其实已经商业化。当年我们没觉得香港拍的是艺术片,这些电影里都有明星,还是挺主流的。但是如果你用现在角度去分析,“香港新浪潮”这些电影还是一个艺术品。我们那时候没人教的,都是慢慢跟着工业的发展或者社会的进程去学习。
新京报:你不认为你的这些作品是艺术电影?
陈果:现在谈“艺术电影”这个词比较言重了,以前没有这个说法,以前只能说自己拍的是“独立电影”。但是,“独立电影”在外国既可以是商业主流的“独立电影”,也可以是彰显个人艺术的“独立电影”。
我现在当然不能不说我做的是“艺术电影”了,但是我的“艺术电影”跟别的“艺术电影”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一直很在意我电影的可看性。可看性是什么?如果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娱乐性,就是没那么苦闷。就像刚才所说,一个很悲观或者严肃的题材,一样也可以拍得有观赏性。因为我知道其实做艺术电影是很残酷的。如果去电影节,片子又得不到奖,很可能就卖不出去。
我们在香港做电影生存很难,因此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果片子卖不出去,就很难继续下去,作为导演,只能在电影里面找它的观赏性。做得大众(universal)一点,谁看都懂,都说好看。我的电影跟很多艺术片完全不一样,不像有些艺术片比较自我一点。当然不是说我的电影就没有自我,只是大家走的路有点不一样。
新京报:但是,我还是感觉你的电影和主流电影很不一样。
陈果:那当然不一样。在香港,我的电影基本上都是独立做出来的,但是我又是反“独立”的,独立的东西会把题材限制得非常小,拍法也都差不多。这种拍法也慢慢也形成了一种主流。我是完全不理这些规则。其实,商业片有商业片的套路,艺术片也有艺术片的套路,看多了我就烦。
如果你问我是什么样的导演,我会告诉你,我真的就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导演)。我是非常坐不稳的人,比如说《三夫》,20年前拍完《香港有个好莱坞》之后,我就可以继续拍,但是我那时候找不到演员。隔了这么多年再去拍,电影会非常不一样。
其实,我拍《三夫》是因为《九龙不败》受到很大的挫败,于是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拍主流电影那么困难,遇到那么多问题?我想还是算了,继续拍“三部曲”吧。
拍《三夫》就花了一个月筹备,见过小美(演员曾美慧孜),回去就开始写剧本,写了两三个星期后就开始拍了。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计算,很简单就去拍了,我也没想过拍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品。
有时候记者也问我,觉得自己的电影如何?成绩怎么样?我说这样问是想我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吗?你怎么可能要求我的作品到(你希望的)那样一个水准。其实我没有目标,我真的随意就拍了。因为我知道限制在哪,困难在哪,极限在哪,资本在哪,预算在哪。所有东西都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
我们拍电影最难的部分是每次拍完一部你就要重新来过,这次“三部曲”拍完,我就开始想接下来是继续拍主流,还是拍所谓的“艺术片”,我挣扎得很厉害。大部分朋友都觉得我不应该再拍主流电影。但我自己拍主流片虽然还没成功,还是期盼可以拍到成功为止。如果有人继续投资,我还是一定拍,做导演应该每次都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陈果导演和编剧的新片《九龙不败》评分极低。
命运好像每次都在捉弄我,非要逼我去拍艺术片不可。其实《九龙不败》本来是不错的项目,可惜后来被老板剪得一塌糊涂,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是做主流出身的,为何拍主流电影这么难呢?也许真的有宿命论在里面,非得逼我继续做比较自我的电影,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怎么样走。
香港电影的衰落不必觉得遗憾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在最初进入电影工业的时候,实际上一开始不是做导演,而是做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这些经历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陈果:帮助很大。我一开始没有决定要做导演,不像现在年轻人一上来就要做导演。现在一百个人里九十个人都说想做导演,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做导演,我只是想说能进入电影工业就好,因为我喜欢电影,我进入这个体系就已经很有成就感,我做每一个部门都非常勤快,非常投入。
那时候太年轻,只有20岁,很热情,做什么都非常投入。当时也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候,往往上一部还没结束已经有人拉你去拍下一部了,当时真觉得拍电影太好了。这样过了两三年后,我开始慢慢地成长,当时看见一起入行的年轻人开始做导演,我就觉得原来做导演这么容易啊,奇奇怪怪的心态才出来。
当然,我也在很多不同岗位里熬过了十年,也不容易。做副导演是最久的。场记做了一年多,然后做制片也跟过摄影组,接着做第二副导,做了五六年,又做了一两年策划。头尾有十年了。这十年对我影响非常大,掌握了非常多的工业经验,当然,经验跟拍电影是两回事,当真正做起导演后,可能又有点不一样。
我那时候都是自由电影工作者(freelance),做完一部就失业,再接着找第二部。我跟过很多导演,每个导演都有很不一样的个性,我从中学习了不少。
我非常珍惜这十年,完全没有后悔。其实,年轻的时候十年不是什么问题,人往往过了三十岁,才发觉十年是那么珍贵的时间,当人的年纪上来后,才领会人生短暂这个道理。后来拍的时候我也会慢慢回想,以前学过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你问小美(曾美慧孜)就知道现场我怎么拍,因为她合作过的导演比我多,而且她都是拍艺术片。她说我拍太快了,他们都受不了,因为一般艺术片导演都是磨洋工,大家不知道磨什么,拍了一条又一条。我是完全没有,这就是工业经验,这不是一定好,对老板有利,对导演来说未必。只是起码我非常稳定,或者说我知道我要什么。
这是经验使然了,经验使我成熟。但我又会觉得有时候太成熟是一个毛病,就是很快就知道电影怎么做的时候,没有了中间摸索期那个感觉。这种感觉按道理不是现场来决定的,应该是前期已经想好,我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不是该放缓脚步慢慢地去拍。
我的经验跟现在年轻人完全不一样,当然现在的社会也很不同了,没人会听完我的话就熬十年,毕竟青春有限。我按照当时的社会节奏才熬,如果现在还要熬十年,没人愿意去拍电影,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新京报:你这次跟年轻导演合作,监制了《沦落人》这部电影,你觉得两代导演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陈果:《沦落人》的导演陈小娟,她也是慢慢才喜欢电影的,毕业进入社会后,她才去找机会学编剧什么的。她本来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然后自己找机会去认识电影是什么,再考进大学学电影。这种导演我们叫“社会派”,但她后来已经不是“社会派”了,变成“学院派”。
现在很多社会派没有受过正统电影教育,也没有进入过工业,到了二十六七岁才知道自己喜欢电影,花三四年进入工业,掌握了拍电影的技巧之后,其实已经三十出头,感觉上会比较急。
但如果一个人18岁,高中刚毕业,在考虑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电影,直接进入电影学院,早点进入工业,就会比较清楚想要什么。有些人一开始只是觉得电影很好玩,进入工业后发现自己不适应这种工作,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转行,但有些人就转不了。
最近就有很多进入社会后半路做电影的现象。但是电影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喜欢,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它非常残酷,残酷得一塌糊涂,做导演跟做演员有点像。特别是那些想做大导演的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成功。

电影《沦落人》剧照。
新京报:你怎么看现在香港电影的情况?因为你经历了最辉煌的时候。
陈果:老实说,其实全世界都在进步。现在如果没有韩国电影,没有新加坡电影,没有泰国电影,可能香港电影还好一点,但是这个世界不会给你独食(粤语里意指独自称霸,通吃)那么多年,人家还是会起飞的。衰落也是人之常情。香港主要是因为地方太小,在历史中创造的辉煌已经很厉害了,就算要退下去也不用有什么遗憾。意大利电影以前也很厉害,有很多大师,但现在完全没人提意大利电影了。香港电影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就可以退休了,真的无所谓。
我们很多主流导演都离开了香港,跑来内地拍电影。但是因为制度的关系,很多电影不能在内地拍,比如恐怖电影就不能拍。这类电影只能留在香港拍,在香港拍的话,就只能在香港上映。但是如果拍得不好,这样的电影也很难卖出去,香港电影萎缩是正常的。
当然,还可以依靠政府的支持,像《沦落人》这种电影,政府给了几百万港币的支持。香港这几年出现了像《一念无明》这样的电影,也是因为政府的辅导金。这种艺术片里,也就《桃姐》算是一个奇迹,可是如果没有刘德华的加入也拍不了。就算你拍成了,但没有刘德华这样的明星,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回响。你问许鞍华就知道,这种文艺片她拍了很多,但是很难成功。但是只要有人继续投资,她一定会做下去,我也一样。
好在香港有个“首部电影”项目,如果你是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想拍第一部电影,可以申请一个比赛,得到冠亚军,政府就完全资助你拍。另外还有一个公开组,就是给“社会派”的导演——那种出来工作很多年,突然想做导演的人。这样一些具有人文关怀的题材才有机会拍。
我们社会的架构本身就偏向商业制作的。一些内地导演到香港后,就发现在香港生存太难了,像贾樟柯那样每年慢慢拍一部电影的几乎不可能。我们真的很难,所谓的香港电影真的要衰亡的话,也不必后悔,它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能做成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
新京报:就你个人而言,你会考虑“北上”拍片吗?因为很多导演后来把重心都放在了内地,但你参与的合拍片好像还是不太多。
陈果:你知道在内地拍片真的不容易,一些题材不能碰,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大的干扰。内地不可能没有人才,如果环境更宽松,那时候才是百花齐放。
当然,社会的发展走到某个节点就会开始往回收,这个很自然。我不觉得香港电影会永远站在高地上。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看到过一个高峰,或者说看到过辉煌的一面,又再目睹香港电影慢慢地往末路走,那当然是有点可惜的,但没法改变。
新京报:今天再看《去年烟花特别多》,你会有特别的感受吗?
陈果:《去年烟花特别多》这部片子老实说当年我是用商业片的手法去拍,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那片子是刘德华的公司投的,虽然钱也不多,但是我希望它没有那么艺术。电影里环境氛围还是比较真实的,把握住了一点真实的东西吧。对我个人来讲,虽然也不是很讨厌它,但觉得还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很少再去看《去年烟花特别多》,基本上我都很少回看我的电影,因为放完就算了。
新京报:很多人喜欢那部电影,因为有一种很诗意的伤感在里面。
陈果:那时候是有的,我当时接触到这些被英国人辞退的士兵,就觉得应该拍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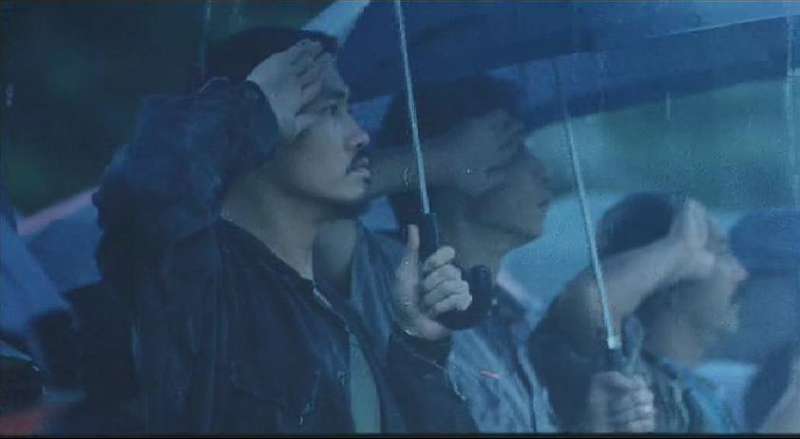
《去年烟花特别多》剧照。
新京报:这里面肯定也有你对于社会的态度吧?
陈果:社会态度当然也是有的,没有就拍不出。但是,我当时是想把它综合一点,拍得商业化一点。其实,现在看来,它真的是一个商业片的结构,我当时拍的时候用了比较主流的拍摄手法,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大舒服。
做电影,就会面临批判
新京报:《香港制造》获得那么大的反响,之后几年,你的创作是怎么样的?
陈果:《香港制造》成功后我去了很多电影节,我才感觉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做,因为香港以前都是封闭在一个非常传统的主流电影工业里面,完全没有这种空间给你认知另外一个世界,我才决定拍三部曲。因为“回归”那年我碰到很多事情,比如很多退伍华人英军投诉,我就决定拍退伍军人的故事。然后我就回想起“小人蛇”(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居民,将在内地出生的子女未经许可偷渡赴港)那个事件。“小人蛇”是发生在1996年,于是我就拍《细路祥》,就变成了“三部曲”。其实《细路祥》是我又回到非常写实的路子上,用很稳定很淡然的拍法,就没有那么商业性,但还是有可观看性的。其实,我也将我童年的一些部分放在《细路祥》,拍的时候就比较舒服。
每一部电影都有难度,你知道《三夫》怎么拍的吗?我都不知道怎么拍。去年突然想做这个项目,在一个月里,看演员,看完取景,然后决定拍,我就会问我自己怎么拍?如果我20年前刚拍完《香港有个荷里活》直接去拍可能就不会问太多,就直接拍。
我十年没有拍电影,我拍完《饺子》后,基本上就没拍电影了,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新京报:但是,这十年正好是香港导演北上来内地拍片的好机会。
陈果:我就在香港和内地两边做了一些监制,比如说《全球热恋》等电影。其实,拍了《饺子》这种商业片后,我可以继续拍类似的片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没有拍。
我拍《饺子》拍得非常愉快,包括和陈可辛的整个合作过程,他也叫我继续拍,但是,现在想不起来为什么我又没有那么做。然后,我去拍了很多广告,拍了几年觉得没意思。我小时候是喜欢广告的,谁知道后来我实现了这个理想,突然觉得不好玩就没有拍了,才继续拍电影。
这个过程可能是浪费了一点时间,但我也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原因。
新京报:当时刚好是内地电影腾飞的时候,一部电影票房从上亿元慢慢跳到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像是《英雄》这样的电影,还是需要香港这边的工作人员和经验的。
陈果:对啊,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来?其实,也有拍过像《成都,我爱你》这种艺术片。我个人觉得那个片子是我拍得最好的,成都人都觉得我拍得好。那个片子是汶川地震后第二年拍的,三个导演每人拍30到45分钟。但是电影拍完后也没上映,因为不够商业。
在这一点跟韩国电影没法比。因为韩国电影的进步是艺术片跟商业片一起来。之前是国内的艺术院线没有成长起来,它的配套来不了。现在艺术片的配套来了,可是有很多东西不能拍。这个局面下导演真的太难了。那么,我只能说每个人都是顺着走吧,也没有想那么多。
新京报:其实,你在香港的导演里面还是很特殊的一位。
陈果:我这种导演是特殊,现在最惨的就是我这种特殊的,让我很迷茫。很多人觉得我不要拍商业片了,但我真的无所谓,因为我们做导演是喜欢挑战自己。我们香港导演没有像内地导演那样强调艺术性,也可以说我们都是有“分裂症”的人。可能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要拍一些为生存而做的东西。但是我想尽量为自己做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每次拍完,我的想法是这个电影能带给你或者说带给观众什么。如果你让我老老实实拍一个电影,我其实很快就可以拍一部,但如果拍出来没有影响力,我宁愿不拍。 特别是小成本电影,已经没人讨论你的价值,你就更要做出这种价值。
新京报:但你不怕它被批评吗?因为有很多争议。
陈果:无所谓,你做导演,无论是怎样的大师,一出来就面临着批判。被骂了就骂了,现在这个网络世界这么离谱,我已经习惯了,经常被骂得半死。有些人给我看网上的留言,我说你不要给我看,那些骂我的人不了解我什么状态,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就行。
观众是很现实的。你只希望我拍艺术片,那我艺术片如果拍得不好,你会看吗?观众早晚会遗弃我们,那我为什么要看你脸色做人?我的想法是,能做多少是多少,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最初的想法是最美好的,什么都不要管。
记者:余雅琴 编辑:徐伟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