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周末 ,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这个夏天口碑最好的综艺,如果未来我们回望中国摇滚乐的历史,或许这个夏天会有属于它的一点色彩。
稍晚于西方摇滚,中国摇滚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吸引了许多年轻乐迷的注意,其内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规并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难上加难。曾经最躁的摇滚乐,也在迈入新千年后逐渐消沉下来。

新裤子乐队获得hot5第一名。
自然,《乐队的夏天》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将摇滚和乐队重新带回公众视野,一度显得沉寂落寞的乐队们焕发了生机。《乐队的夏天》刚刚开播时,舆论不乏质疑之声,就连节目组本身对于摇滚与综艺的碰撞,也充满忐忑。但随着节目逐渐展开,这种碰撞似乎渐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们从经典意义上的摇滚,尤其是中国摇滚入手,观察当下摇滚乐的新趋势,以及《乐队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们发现,当下的摇滚创作似乎正从宏大议题走向微观情绪,我们的理想和缺憾,都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破碎,越来越细微,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新的力量,正蕴含在这些碎片化的歌声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乐队的夏天》中,摇滚乐面临的矛盾反复出现
七月底,德国重金属摇滚名团“德国战车”(Rammstein)在莫斯科举行欧洲巡演的演唱会上,两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万粉丝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随后将照片贴在了乐队的脸书和IG上。对于此举,粉丝普遍认为是乐队对俄罗斯恐同立场和法律的反对,而就在不久前,俄罗斯知名的LGBT活动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残忍杀害。

重金属摇滚乐队“德国战车”两位吉他手在演唱会上公开接吻。
我们时常看到一些乐队表达他们对公共事件的看法。这个传统并非晚近才出现。当我们回溯摇滚乐的诞生以及其发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动、反叛、奔腾喷薄,也带着深深的乌托邦色彩”,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园之门》中对于当时兴起的青年文化运动精神(“垮掉派”与摇滚乐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尔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称作“破坏性的一代” 。
于是,摇滚乐注定和其他音乐,如流行乐,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当我们处在如今这样一个权力、资本与消费大潮所织成的无边网中时——人们对其的期望与想象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它带着出生时的喧哗与骚动,对现代秩序带来干扰与破坏;另一方面,音乐作为产业,它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导致其不得不面对被阉割,甚至禁声的命运。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滚乐所面临的纠结与矛盾在《乐队的夏天》中反复出现。
如果不是马东所做的这档《乐队的夏天》,多数观众对中国摇滚乐的前世今生大都了解有限。无论是高晓松、面孔乐队、张亚东还是新裤子,每每说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于言表的同时也伴随着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黄金时代”转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复的言说。

刺猬乐队在《乐夏》演出。
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关于摇滚乐十分典型的象征,即曾经经典意义上的摇滚乐辉煌不再,并且似乎再也难以复现。这种气氛如同一股强烈的潜流蔓延在《乐队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节目中颇有张力的一幕: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经典摇滚理解的专业乐迷评委们,始终无法抛弃传统标准,来接受节目中许多乐队的“出轨”。
香港著名音乐人陈少宝曾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北京发展,见证了当时北京地下摇滚乐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传《音乐狂人》中说:“1996年,当时在北京做音乐的环境还不太理想,但是每个音乐人都很有激情,”而且“当时北京的乐队气氛真的很热闹”,“当时我眼里的北京摇滚乐手真的个个都有一团火,非常有冲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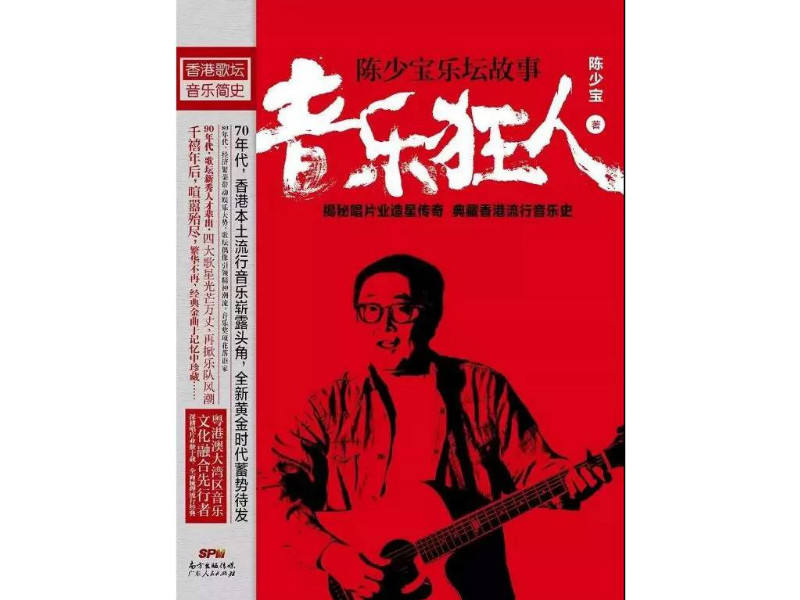
《音乐狂人》,陈少宝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
正是这些摇滚乐史与实践,塑造了《乐队的夏天》中专业评委们关于摇滚乐的理解和想象。这一“古典”,或说是“保守”的看法,使专业乐迷们遭到大张伟以及普通乐迷的反对。大张伟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听众们一个典型看法,即音乐不必为各种标签或圈子所束缚,否则难以进步。而在《乐队的夏天》中,100名普通乐迷们投票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你是否喜欢乐队的表演”。但就如张亚东曾指出的,这其实是听流行乐的方式,对于摇滚乐它存在很大局限性。

涅槃乐队。
在摇滚乐中,很多歌并“不好听”。各种重金属摇滚(Heavy metal)、华丽摇滚(Glam Rock)或是垃圾摇滚(Grunge Rock)中,组成一首歌的词、曲和唱有时难以平衡,甚至出现嘶吼、走音跑调和各种临场发挥的状况。这也是许多人在听摇滚乐时的感受:这些人到底会不会唱歌?涅槃乐队(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的唱法就十分特殊,其中掺杂着各种嘶吼。在《乐队的夏天》中,新裤子主唱彭磊也曾使用过这一唱法。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的混乱、嘈杂和嘶吼,也是摇滚乐的一部分。在《春歌丛台上:对话33位音乐人》中,就有音乐人指出,当下一些音乐综艺通过后期修音把一些乐队演唱中的“瑕疵”修掉,但许多朋克乐队有意通过这些跑调和瑕疵来表达某些观念。
摇滚精神碎片化?但这不一定是坏事
与古典或流行音乐不同,摇滚乐“混乱”的表演,从歌词曲到舞台表现(摔吉他等行为),本身就是组成摇滚乐的重要形式。而在《乐队的夏天》中,这些特质都只得到十分有限的展现,毕竟,这是一档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的娱乐节目,同时它也处在当下权力和市场的网中。
一个细节就反映出了这些问题,在《乐队的夏天》中,好几支乐队的歌词都被改过,如旅行团乐队的《Bye Bye》中,原本的“bye bye主义的世界”被改为“bye bye狭义的世界”;新裤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热》中“被社会伤害的人们”被改成“不能再见的朋友”……
这正说明摇滚乐在当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在《春歌丛台上》接受访问时也指出,音乐的商业表现同样是评价音乐好不好的标准,尤其在今天,在很多人眼中,音乐不再是艺术品而是日常品。就与曾经所有“经典”的艺术(摇滚乐或许甚至不愿称自己为“艺术”)一样,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消费与娱乐至上的时代中,所有音乐都在被以流行乐的方式制作、传播和再生产,而流行乐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其对于听众最大公约数的依赖。为了实现更广的传播,经常出现模仿、复制和各种套路,最后耗尽其内在的精神。

《春歌丛台上》,小鹿角APP 音乐财经 联合出品 / 董露茜 主编 ,东方出版社2019年4月版。
美国学者迪克·赫伯迪格在其《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指出,亚文化的风格与主流文化风格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刻意“罗织”(fabricate)出来的,带有被建构性,因而不同于主流风格的传统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摇滚乐就开始反对自身,诸如垃圾摇滚或迷幻摇滚的出现,如贝克(Beck)、垃圾(Garbage)、涅槃乐队和枪炮与玫瑰(Guns N' Roses),正是为了抗议摇滚乐在日渐华丽的外形背后越来越苍白空洞的灵魂而产生的。而正是这种自我反叛和破坏,才使得摇滚乐能够持续地产生动力而继续发展。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美] 迪克·赫伯迪格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但创新和破坏本身需要付出代价。《乐队的夏天》中,除了一些已经名声在外的乐队,Click#15、九连真人、帆帆与斯、盘尼西林等新乐队的演出机会和收入都有限。这或许正是摇滚乐在当下所面临的最大悖论,即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赫伯迪格在总结亚文化的流变特征时指出,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是其难以避免的周期。对于摇滚乐而言,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后现代的来临,它们曾经所需要对抗的种种有形有声的高大敌人,已经开始以另一种形式渗透在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中:权力不再打压它、主流商业和资本也对其伸出橄榄枝,甚至在这其中,一定的冒犯和反抗都能被接受,并且成为主流所欣赏的某种“景观”。当乐队选择参与这类综艺时,也便意味着他们需要遵守市场、娱乐、消费以及权力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甚至束缚摇滚精神。戴上“镣铐”是否还能跳出自由的舞蹈,始终是令专业乐迷以及那些对摇滚乐有着深深期望与想象的乐迷们的焦虑所在。
伴随着市场与娱乐发展起来的,是宏大理想与反抗的碎片化。彭磊也曾说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放弃摇滚乐,去上班和拍电影,在《生活因你而火热》中,描述的不正是理想失落之后的茫然和投身日常生活的状态?
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学界把渐渐出现的这个新时代称为“后现代”,而其最典型的一个特点便是宏大叙事的破碎、整全性和同一性理想逻辑的解构以及一切坚固的偶像随之烟消云散。似乎一切都变“小”了,变得无处不在,就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也开始变得如毛细血管般密密麻麻,肉眼难见。
即使在《乐队的夏天》中被赞不绝口的几支年轻乐队——如盘尼西林、九连真人和Click#15——他们的摇滚乐在多元且丰富的同时,却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虽然那些专业评委们对其爱之深,却不能遮蔽他们同样因为生活在当下这个琐碎、日常、平庸的消费世界中所无法切掉的尾巴:盘尼西林继承着英伦摇滚中的一部分精神、九连真人利用客家话唱着小人物的奋斗与失落、Click#15则继承了美国著名歌星Prince和迈克尔·杰克逊的魅力……我们曾经为摇滚乐所预设的许多概念、任务和形象在这里也随之消散,并且早已经不再是年轻乐队们所考虑的问题了。
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也正是在这一混杂的处境中,摇滚乐一边被解构着一边被呼唤着。
变动中的摇滚乐,重新赋予我们想象的能力
这也正是《乐队的夏天》所引起的讨论。它让人们在大行其道的流行乐之外看到了不同的音乐形式、乐手和乐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努力让乐队们展现自己的个性与魅力。在最后一期节目中,乐队们真心地感谢《乐队的夏天》的帮助,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被看见、被听到本身就是生存的最基本前提。而对于一个健康的音乐生态而言——就如在《圆桌派》中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所说的——只有当所有音乐形式都被关注了,观众们才真正有了选择的自由,也才能促进其多元发展。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曾把陷入拟像(Simulacra)的消费时代称为“玻璃屋”,人们能够看到外面,却又难以逃离。摇滚乐也身居其中,面对一地鸡毛,它似乎开始发现自身力量的有限,以及由于人们的冷淡所引起的努力的无效。“让我快乐一点吧”,更像是对当下摇滚乐无奈的一个写生。而面对着这样的“玻璃屋”,或是福柯所谓的“环形监狱”社会,改变和反抗从何而来?如何进行?

大张伟在《乐队的夏天》,让彭磊(新裤子乐队主唱)接着“躁”。
最终我们发现,只能从面对每一处不断(再)生产的破碎、无聊和日常开始。就如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在其《日常生活》中所指出的,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性思维以及其重复性实践往往会对创造力造成磨损与压抑,最终消灭个性,而形成某种平面化的单调世界;而无论是消费还是娱乐,它们同样都对创造性与个性造成威胁甚至破坏。对整合性的权力而言,这是治理术所能规训出的最好的统治状态。而摇滚乐与这一状态截然相悖,因此必然会遭到压制或阉割,但与此同时,也便发掘出了摇滚乐最迷人和最具力量的地方:它能够揭示庸俗和单调背后的死气沉沉,也能够发现谎言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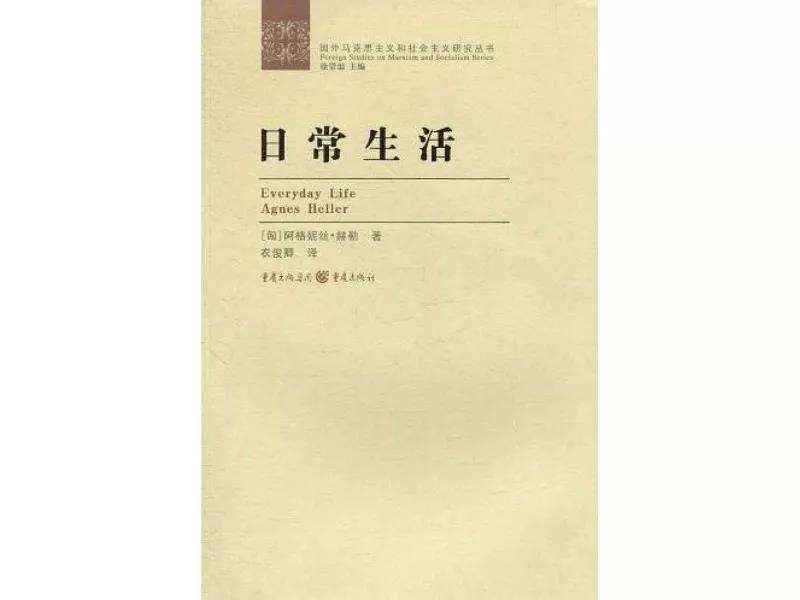
《日常生活》,阿格妮丝·赫勒 著,衣俊卿 译,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摇滚乐以或严肃、或愤怒、或轻松戏谑的态度告诉我们“皇帝没穿衣服”。赫伯迪格提醒道,“武器才是亚文化的本质”,一旦它失去了这一内核,也往往意味着死亡。而在当下,如何使用这一“武器”的方式已经改变。
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开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自己对于开放性的追求和努力。或许也就如福柯所说的,它最终将变成一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状态。《乐队的夏天》本身就是娱乐节目中的“异类”,而也正是它的这一不同才使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力量,这是它的抱负所在。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借助摇滚乐想象,借助它纾解心中的情感、苦闷与愤怒,也曾借助摇滚乐希望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无论如何,它始终都是单调与贫乏日常生活中的一根“刺”,提醒着另一种可能的存在,“不一样”的体验,关于个性、关于冒犯,关于对一个更好的世界和社会的想象的能力。而就如约翰·列侬在《Imagine》中所唱的:“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作者 | 重木
编辑 | 安也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