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柏琳
我们误会了彼得·汉德克。
但这不能怪我们。这个奥地利人很分裂,你很难找到理解他的通道。
他被视作“德语文学活着的经典”,世人把他当做一个充满后现代风格的作家,一个先锋派,一个和世界对着干的人。

知道汉德克的中国读者念念不忘他的戏剧《骂观众》,或者和大导演维姆·文德斯的合作,汉德克每听到这些话都一脸无奈。写出反传统戏剧规则的《骂观众》时,他才22 岁,那时候还没有“后现代”这个词,他不理解为什么读者喜欢往他身上贴一块“后现代主义”的标签。
他甚至拒绝“反叛”这个词,因为那是“年轻姑娘才干的事儿”,汉德克觉得自己是个传统作家,更愿意“成为托尔斯泰的后代”。
但往往事与愿违。这个留着一头“披头士”式中长发的男人,长年独来独往,他用叙事表达梦想,试图打破语言的条条框框,描述人们孤寂迷茫的生存状态。他爱这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并不爱他,并且让他成了所谓“另类”。
误会
一个勉为其难的剧作家
1966 年4 月,著名德国作家团体“四七社”成员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开会,与会者包括当时走向巅峰的君特·格拉斯。时年23 岁的彼得·汉德克飞越大西洋,不请自来出现在会场,破口大骂当时的德语文学墨守成规、语言软弱无能,在场的文学前辈目瞪口呆。
汉德克暴得大名,被喻为德国文坛上和“20、40 一代”完全不同的“68 一代”革命性文学新星。他这一反叛形象还因为同年出版的剧本《骂观众》而家喻户晓。
写《骂观众》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坐在床上用膝盖垫着打字机,在六天里一气呵成。《骂观众》只有四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这部戏在德语文坛上引起轰动。

《骂观众》,彼得·汉德克 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月
年轻的汉德克以一场“语言游戏”粉墨登场,《骂观众》这种“反戏剧”的做法,部分灵感来自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思想,更多的像是“游戏”——上世纪60 年代,欧洲剧院里大多上演梦幻性质的传统戏剧,汉德克觉得那是一种幻象,决定写一出戏来开开玩笑,告诉观众,“你们的时间空间就是演员的时间空间”。
一场玩笑却成就汉德克的成名作,今天他还在为这“盛名”所苦,“《骂观众》只是我早期的一个小小的作品,更多像是一部完整的话剧之前的引言”。在《骂观众》之前,汉德克的小说《大黄蜂》已获出版社认可,他想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却发现除了小说,还需要写点戏剧才能生活。
在汉德克开始写作的年代,艺术形式是互通的,剧本被当做文学作品来阅读。当大学教授在台上讲授法律课程,他在台下看尤奈斯库的剧本,读迪伦·马特的小说,听披头士的歌,跟着歌曲节奏,捕获创作灵感。
他对而今的艺术生态颇有微词,“文学和戏剧的距离越来越远,戏剧和写作成了两个圈子”,而他总被当成先锋剧作家。第一次来中国,读者的问题都围绕《骂观众》《卡斯帕》等他最初五年的作品,还迫切想知道他对于剧场实验和电影改编的看法。汉德克不喜欢这些问题,他说自己不过是个勉为其难的剧作家。先锋?其实并不像。

在写完改革传统形式的最初几部戏后,汉德克回归了经典话剧,陆续写下《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关于乡村的故事》等戏剧,后者更是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榜样。
如果写作是一棵大树,对汉德克来说,主干是史诗性的叙事,戏剧只是“美丽的枝杈”。史诗性的创作在处女作长篇小说《大黄蜂》里已见端倪。叙事的长河从童年心灵创伤中奔涌而出,支离破碎的叙述成为汉德克生存体验的表达形式。而创伤性结构是这个出生在奥地利底层家庭的不幸的年轻人的印记。
天性
在写作中他才能体验他人
汉德克有一个自杀的母亲。她自杀时,汉德克29 岁,母亲的死带来的是一种钳制他的魔咒——他终生都在苦思,被异化的生命如何找回生活的感觉?
1942 年彼得·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贫穷的家庭供不起汉德克上学,他被迫上了八年牧师学校,直到1961 年进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并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文学对于汉德克来说,是认识自我的通道。进入70 年代后他从戏剧创作中的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转变的契机在于因母亲自杀而写成的小说《无欲的悲歌》。
他用一种身临其境的叙述方式表现母亲的生与死。这个天性热情的女性,因为出生在天主教小农环境里,被迫终身忍受无欲望的道德教育和贫穷的小市民生活,文学无法拯救她于毁灭,自杀是抵抗异化的归宿。母亲被异化的人生成为汉德克写作的阴影,他发出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先后发表了《短信长别》《真实感受的时刻》《左撇子女人》,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如何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
从22 岁创作《大黄蜂》开始,汉德克就着迷于探索自我内心世界,自甘于一种危险境地——在自我世界里拔不出来。上世纪80年代后,他从巴黎回到了奥地利萨尔茨堡,过起了隐居生活。此时他阅读了大量的描述外部世界的法国新小说,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只表述外在世界不够,“如何处理你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平衡”成为他写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这段时间他先后写下《铅笔的故事》《痛苦的中国人》《试论疲倦》等,但最能体现汉德克此时精神状态的,是“归乡”四部曲(《缓慢的归乡》《圣山启示录》《孩子的故事》《关于乡村》)。

他喜欢大自然,隐居时经常面对无人的原野写作,也时常因为害怕而回家。“归乡”四部曲是他寻找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转型,在四部曲的尾声,主人公找到了自我在世界站立的方法——获得“写作的权利”来捕捉真实。
感受真实的时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非易事。汉德克生活中也和普通人一样,经常被生活的“固定路线”磨得存在感无足轻重,只有在写作中他才能体验他人,让自己愉悦。
回归
写作的时刻无限接近良知
“我是我自己的囚徒,写作把我解放出来”,汉德克每天都对自己这么说。虽然外界对他80年代的隐居封闭状态很担忧,但这是他的主动选择。他想让心灵进入一个叫做“永恒”的“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也许像一个乌托邦,但不知道入口。
那个空间里起码没有战争。挑剔的和平主义者汉德克,从童年开始,战争记忆就是影响未来情感世界的恐怖幽灵。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内战……不太平的欧洲,90 年代的社会现实把汉德克拉回“外部世界”。从《去往第九王国》开始,他的作品到处潜藏着战争的现实和人性的灾难。1996 年,他发表了游记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成为众矢之的。1999 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 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 年3 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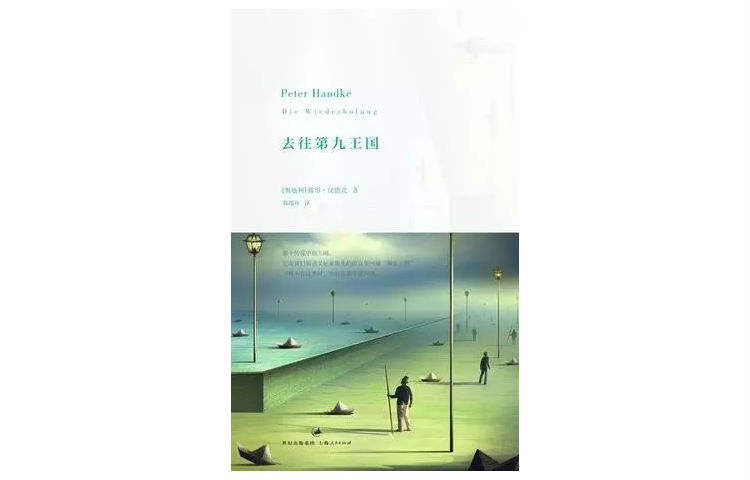
《去往第九王国》,彼得·汉德克 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南斯拉夫深藏在汉德克心中。《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挽歌式地描写了他与南斯拉夫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其解体在他心灵的震撼。尽管饱受非议,他却一直为这些关于南斯拉夫的作品而骄傲。
但他始终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作家,他的骄傲在于写作的时刻——独自一人,无限接近良知。他经常引用歌德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写作状态,“喜悦和痛苦交替着碾过我的心头”。
他也有恐惧——因为写作是一种未知的冒险,“你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写出来”,74 岁的彼得·汉德克,往后每天经历的所有时刻,都不是惯常的时刻。
本文刊载于2016年11月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版。
作者 | 柏琳
编辑 | 孔雪,户晓,小井、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