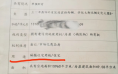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其独特的魅力。近年来,随着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公众的增多,有关于日本文化的图书也颇为热门。在作家萧耳看来,生命的绚烂与短促一直是日本人的执念,物哀之叹构建了日本人一生的情感格局,而日本的主流文化,则总是咏叹万物变移不定。
近日,萧耳携新作《樱花乱》,做客北京SKP RENDEZ-VOUS书店,通过“花”和“刀”两个关键词,与著名批评家、作家李敬泽等,一同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生发于日本文学典籍阅读,在奈良、京都的日常生活与行走,以及日本民族相关节日仪式中的思考。
在《樱花乱》一书的代序中,萧耳援引了木心的说法,“日本如浮萍,没根没底的。非常狡猾,头头是道,没有下文。日本人不可以谈恋爱,也不可做朋友。很怪,但终究是乏味的。”而在她看来,“我见过的说日本文化的,没有比木心说得更妙的了。”而在当日的活动现场,萧耳说:“《樱花乱》对我来说就是一本生长已久的书。对我来说,这本写日本文化的书关联着我的前世今生,这里有我个人对东方文化的探寻,对日本国民性的深究,有从几百万字的日本相关作家的著作中对藕断丝连的中日文化渊源的追溯,还有自己血液里与日本隐约的、难言的联系。”

“花落,刀落,跟清少纳言谈心——萧耳《樱花乱》新书分享会”于近日在北京SKP RENDEZ-VOUS书店举办。邢贺阳/摄。
十年前,李敬泽曾为萧耳的作品《小酒馆之歌》和《女艺术家镜像》写过序言。李敬泽注意到,今年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就是日本,满日本都是中国人,而这恰恰体现出大家对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兴趣。李敬泽说,中国和日本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中国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日本我都懂、日本我很熟悉”的错觉,“尽管我们有文化的亲缘关系,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有着非常深刻的非常不一样的差异。”在李敬泽看来,这些差异恰恰是最不应该忽视的,“那些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李敬泽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复杂,因此才有必要互相认识,“我们要承认,日本的文化有它灿烂、优美、极具特点、极具魅力的一面,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和我们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读、相互映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李敬泽说自己特别爱看中国文人写日本,他认为这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见识、水平和感受力,几乎是一块试金石。李敬泽认为,萧耳能够掌握日本文化中的独特之处,“用北京话叫‘很拧巴的劲儿’……这样的感受力用来写《樱花乱》,我觉得非常合适。”因此,李敬泽十年后再次为萧耳作序,在《樱花乱》的序言中,他称萧耳为“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闺蜜”。

《樱花乱》,萧耳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李敬泽在《樱花乱》序言中写道:“花事无成败,人事难免成败。”李敬泽说,紫式部、清少纳言的作品如果放在中国,可能会写成《甄嬛传》《如懿传》《延禧攻略》,因为我们和日本人对待同样问题的看法和角度很不一样。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笔下的宫廷,宫中之事,相比于《甄嬛传》,就显得很“没心没肺”,因为她们的心思不在心机或谋略上,而是她们对人生的看法,“什么叫成功?成功是花开了,什么叫失败?失败不过是花落了。”李敬泽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2007年,由蜷川实花导演,土屋安娜主演的电影《樱花乱》在日本上演。这部作品之中,有日本文学中常见的刀、花、寂、艳等元素,而这似乎是对日本文化比较普遍的定位,类似于《菊与刀》。而在创作《樱花乱》时,萧耳也将该书分为了两个部分:上卷名为《花落》,写花;下卷名为《刀霜》,写刀。

电影《樱花乱》剧照,该片由蜷川实花导演。
“是日本人不懂得节制感情吗?”萧耳非常推崇《平家物语》,在她看来,这本书里有着日本物哀文化的美和人性,“日本人悲痛起来,贵族也可以满地打滚、匍匐在地,中国(式)的节制、中庸这些东西,在日本不存在,比如妻子和丈夫离别,平氏和原氏两方打仗,平氏逃奔之后告别家人,全是贵族世家的哀。男女离别的时候体现了一种凄美,所有的悲痛、不堪,通通展现出来,痛哭流涕,不留任何余地,这些东西非常打动我,很真实,不做掩饰。”萧耳曾经读过李敬泽有关清少纳言的文字,她当时颇为震惊,觉得李敬泽是少有的能把清少纳言文体中的阴柔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的男作家。
在《樱花乱》一书中,萧耳数次提到谷崎润一郎,她表示自己很喜欢这种阴柔。谷崎润一郎有一本随笔集叫《阴翳礼赞》,萧耳认为,谷崎润一郎的恶趣味中有暧昧的东西,而这与日本的和式建筑有关,这种阴暗的室内空间,决定了明治维新前足不出户的贵族女子的情感方式,处理男女关系的方式。而这正好与萧耳喜欢的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形成了正反面,因此,《金阁寺》也是她热爱的日本文学作品之一。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