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也不会忘记陈独秀研究的先行者与铺路人任建树。
作为先行者,任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陈独秀研究(以下简称“陈研”)行列。彼时,这块园地还是禁区或半禁区,他所在的上海市社科院与社会上都有劝阻者,但他义无反顾力破坚冰,奋然前行,直到生命的终点。
作为铺路人,任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陈独秀著作的搜寻及其传记的打造,功不可没。他先后主编的《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成为中国陈研之基本文献;他先后撰写的《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陈独秀大传》,客观公正且不失生动地再现了陈独秀的形象,是国内最受欢迎的陈独秀传记。
仁者,寿也。任建树先生以九十六岁高寿,于2019年11月2日在沪上溘然长逝,也进入了历史星空。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24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1945年初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54年任上海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进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后隶属上海社科院,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任,著有《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记》《五卅运动简史》(合著)、《现代上海大事记》(合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主编)等。
“坚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精神的人”
我在陈研路上,沐浴着任老关爱之光。为写此小文,我将任老之签名本从书架搬到案头,垒起了一座书山。我凝视良久,也勾起一桩桩往事。

作者收藏的任建树先生的部分著作。
我与任老第一次相逢,是在1997年10月20—22日于合肥花园大酒店召开的陈独秀研究会期间。1989年3月,在北京市党校召开了全国首届“陈独秀思想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陈独秀研究学会,此后不定期地在全国各地召开陈研会,陈研同仁才有时而相见的机会。21日下午小组讨论,我以马克思主义原本原理与人类文明史常识为依据,论证某流行口号为僵化思维、禁锢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荒谬口号,被视为“大胆的发言”(传播常识竟要大胆!)。没想到在座的任老赞同我的观点,并与别的专家一起推荐我在次日的闭幕式大会发言。这次发言给任老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后来的交往中他多次提到此事。
会后,主办方又安排任老等专家在天柱山、安庆独秀园往返参观、座谈,直到10月27日。我始终作陪,零距离地感受到任老之平易近人与善解人意。10月26日,他为我在《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与《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分别题写“钟扬同志指正,建树1997.10.26”,极为谦虚,其实,彼时的任老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是史学“权威”。只是有人呼他“权威”,他立即纠正:什么权威不权威?!这才会与我等后学亲密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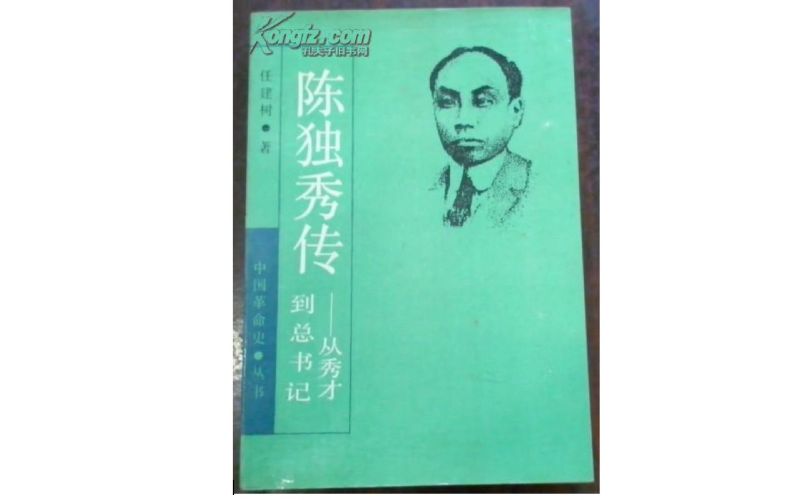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任建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这两套书都经过任老近十年的艰苦打造,方得问世(著作选1993年出齐,传记1989年出版)。其间的艰辛,任老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道及,他说:“我在陈传(上)所使用的资料,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从图书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里的书刊上摘抄下来,真是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了。那时复印的条件不如现在,而且费用也高,因此我都是摘要的。所谓‘要’也仅限于当时的所需。这是很费时间的,我的所谓研究工作,大约有一半以上是做文抄公——不是完整的,而是零星的抄录”。(1997年12月1日信)个中滋味,非经历者实难体会。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像此前他花两三年时间做的《陈独秀研究资料汇编(1921—1927.8)》二十万字,虽签了合同却被一纸通知废了),而这两部书确为陈研破冰期的硕果,也是陈研后学的入门书,提升了全国陈研学术的起点。不过,任老没就此止步,仍在文献与传记两翼作精益求精的挺进,尽管他1991年底就办了离休手续。又经过十来年的打拼,他主编的《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终于2009年出版,他独撰的《陈独秀大传》终于1999年出版,又过三年《陈独秀大传》修订本于2012年再版,再次推进了全国陈研学术水平。蒙先生错爱,每有新著与新版书,他都有签名本赠我。在《陈独秀大传》(修订本)上,他的题字竟升级为:“石钟扬先生教正,任建树敬赠,二O一二年三月”且加有名印。令不才惭愧不敢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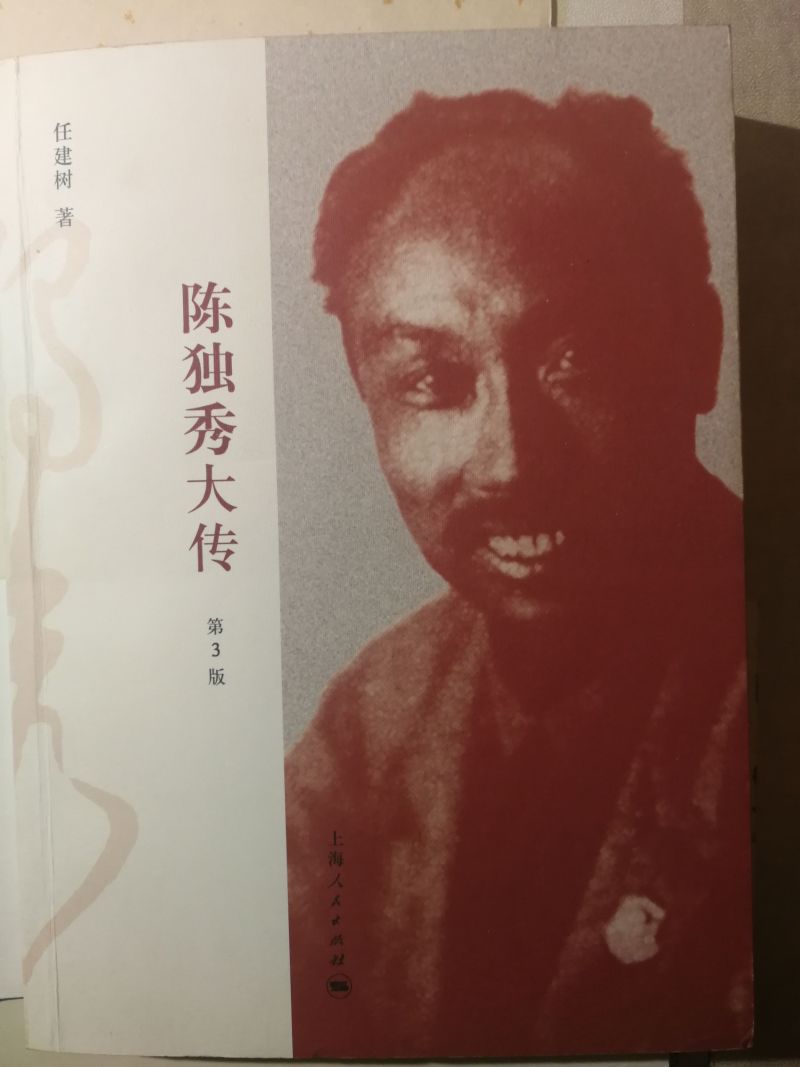
《陈独秀大传》任建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版
任老说:“说到陈独秀的风貌和生平事迹,最引人入胜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我常常觉着在中国,在有着长达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像陈独秀这样一生坚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精神的人太少了(中国历史,诚如鲁迅所云:一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为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我敬仰他的人格和精神。这就是我不肯罢手(书写陈独秀先生)的主要原因”。(任建树《我怎么会研究陈独秀的》,江苏《陈独秀研究》总第12期)任老之言深得我心,我从中获得了灵魂洗礼与精神动力。
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抑或政治领袖?
与任老通信,是那次合肥会议之后开始的。1997年10月30日,我随信寄了篇《从<惨世界>到<黑天国>:论陈独秀的小说创作》,请教任老。任老11月6日即给我回信。
钟扬同志:
10月29日的信收到。大作也已拜阅。
谢谢你为我提供查考邓仲纯的线索,同时也感到你在做学问上是一个细致的有心的人。
大作,我看了。我很欣赏这篇作品。《惨社会》,我浏览过一遍,《黑天国》只看了个题目,说不清当时为什么没有读一遍的原因,也许是未署名(记不清了)。你的评论我认为很好,文笔也很好,不愧是中文系毕业的。我希望你今后仍然可花些时间从文学的视角去研究陈。对陈的研究领域一要拓宽,一要深,只要改革开放不逆转(这是不可能的,小的曲折也许难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陈发生兴趣。这次在安庆认识你们几个年青(轻)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种高兴的心情,是年轻无法体会的,我希望你们能组织起来,寻找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最好找那些有几分傻气的“书呆子”(即勿找急功近利者),大家能真诚合作做些事情。需要我出力,只要我能做到的,自当效劳。
祝健康
建树11月6日

任建树先生信件手稿。
任老在这封信中表述了对陈研事业的自信,(陈研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通着命运)并将寻些有几分傻气的“书呆子”作为对陈研后继者殷切的期望,更有对我之厚爱。中国陈研队伍以近代史与党史学的朋友为主体,研究的热门话题为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命运,唯我是中文系出身只研究陈之文化/文学,被视为“异己”,有好心的朋友劝我皈依主流,唯任老及少数师友支持我“从文学的视角去研究陈”。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这一独特的陈研究路上渐行渐远。
200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陈研专著《文人陈独秀》。在此书中,我给陈独秀定位为: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政治领袖他是个悲剧人物,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吁的科学民主具有永恒的魅力。作为国内第一部从文化视角研究陈独秀的专著,《文人陈独秀》的问世,在学术界反响比较强烈。江苏省陈研会2005年10月9日为此在南京财经大学举办了高端学术论坛,任老欣然赴会发表了别具一格的讲话。他高度肯定拙著“为陈独秀研究开拓了一片新领域”,同时认为“把陈独秀定位为首先是政治领袖,其次才是文化领袖是比较妥帖的”。

《文人陈独秀》石钟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他指出:“当前关于陈独秀的作品约有三种:一是研究型的,先从资料入手,下功夫,这自然是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急功近利、为评职称而写作者所欲为的。二是看了他的著作,写出感想式的文章,其中也有好的论文,还有一些为陈打抱不平、情绪高昂的作品,这些都对‘陈研’有利,也许可以说是以第一种研究为基础的作品。三是戏说性的,其利害对比,一时说不清。石钟扬的《文人陈独秀》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著作,是我欢喜,感到高兴的作品。尽管我对之略有不同看法,却并不影响我认定这部书是我近几年来见到的最好的一部”。(任建树《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抑或政治领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月)
“学术研究多是离退休后抢回来的”
2010年我们策划的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自然希望得到任老的支持。这年除频繁的电话之外,任老分别于2月1日、4月5日、7月12日、11月14日给我写信,主要是推辞写字,却愿为我们推荐合适的书家。其中7月12日信用双16开竖格旧纸,他破例以毛笔书写,申述他不善书的原因,其实即一幅甚佳的小品。信曰:
钟扬兄:
谢谢你在电话里盛情约我为书画展写几个字,我亦想为画展出点力做件事,可我觉着写字之事,是你找错人了。我是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才进初中的,但不及一二月由于战事逼近,学校不得不南迁,此后又一迁再迁,进入伏牛山区。那时的穷,那时的难,且不说现在的孩子们,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部分的爷爷奶奶也是难以想象的,哪里还有像样的毛笔,写英文字用的笔是当地产的细竹自制而成的。
你现在正儿八经地向我索讨“墨宝”,这使我感到既为难又好笑。前年搬家时,清理杂物,发现了一叠五十年代末的信纸,与其弃之如废物,不如借此涂鸦,见笑了。
我答应你的事,已办妥,即陈独秀外孙吴孟明先生写好了一首诗,现一并挂号寄上,收到后望告诉我。 敬礼
书画展诸事顺利、在宁诸友健康
弟 建树七月十二日

任建树先生信件手稿。
任老毕竟年迈,不良于行,他没出席《迟到的纪念》书画展(陈独秀130周年诞辰本在2009年,推迟到2010年纪念,故用此名),他却寄来一千块钱资助我们《陈独秀研究》(简报)。年底任老特寄来贺年片慰劳我。而我在编辑《迟到的纪念》画册时又过于死心眼,一味强调画册的艺术水准,竟没将任老、郭德宏等资深陈学专家之手札与作品放进画册。于今思之,深以为憾!
自任老不良于行,我只要到上海,他知道了定会召我去他府上畅谈兼小酌。这种机会毕竟不多,更多的是电话交流。先生念念不忘的是《陈独秀全集》的编辑与出版,这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可惜此项工程迟迟难以启动,令人浩叹。每念及此,先生却自责他衰老无用,我则以他声音洪亮为由来“反驳”他,他总发笑说当年在中央大学唱过歌,落得一副好嗓子。与先生电聊是别样的享受。
2014年我也退休了。先生得信后多次打电话让我好好设计退休后的学术研究,说他们那一代多在运动中折腾掉好时光,学术研究多是离退休后抢回来的,让我退休后要把握好、多做点事。与社会上流行的一退万事休、好好玩玩之论调大相径庭。我铭记先生之嘱咐,退休后仍在有序地进行着学术研究,力争有个如先生充实的晚晴。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
任先生身材挺拔,初逢时节他就是一头银丝,纯洁到一丝不染。不管多大的会场,不管先生坐在哪里(主席台就更不用说),我都会一眼看到或望到先生,有时会用目光互致问候。先生儒雅的仪表中,书写着仁厚、稳健、坚毅的内涵。
与他同行的,往往有一位与之风格迥异的学者王观泉,他是黑龙江社科院的研究员,长期蜗居在上海亭子间苦熬,熬出了不少妙文,而双目也几乎熬得失明了。他不修边幅,墨镜下却渗出满满的艺术范。仅看书名《“天火”在中国燃烧》《人,在历史漩涡中》,就知道其充满着诗人气质。他没有任老好亲近,我也终与之结识,且从1997年11月起有不紧不慢的通信,我手里头也有他八九封信。除一二答疑信件,多为贺卡,很逗的是他的贺卡全是他手制的艺术品,弥足珍贵。
最感动我的是,观泉先生2005年5月13日将他的名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的校样寄赠给我。题字:“钟扬老弟存正,观泉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还慎重地钤上三颗印,并附有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他有眼疾,兼龙飞凤舞,其字形同甲骨文,我好不容易“破译”出来。
观泉先生这部陈传,本是1991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台北业强出版社之约,以只眼之微光在放大镜下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写成的。不敢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两年辛苦确实不平常。但此书在国内辗转不能问世,让观泉痛苦不已。他将其校样与有关部门的审读意见及他对其之解读,一同寄我,让我保留了一份中国陈研史上珍贵的学术档案。谢谢先生对我的信任。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是“五四”精神领袖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这年对“五四”和陈独秀的纪念与研究都相当平静。
倒是相继走掉几位陈学专家,年初是“世纪老人”李老(2月16日),接着是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5月12日),再则是几乎双目失明、人称“目中无人,心中有仁”的董健教授(10月22日),到年底是任建树先生(11月2日)。令人难以平静,于是有了这篇短文。
岁月无情,历史存根。任老等陈学先哲之学术业绩将永留人间,传播着独秀精神,滋润着来哲之灵魂。
作者:石钟扬
编辑:徐伟、余雅琴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