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月12日)下午,《长江日报》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 》的评论文章刷屏。毫无疑问,“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武汉加油”,无论来自哪,都是一种支持。然而,文章末尾的一句,却迅速在微博、微信等社交app引发热议。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并不是诗歌本身是残忍的,而是一个写诗的灵魂,要经历他们所曾经历的磨难,去感受那些磨难,让语言经历洗礼。
这是作者对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的误用。众所周知,奥斯维辛是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它见证了20世纪的一场巨大灾难。从诗歌到其他形式的创作、研究,在黑暗降临的时候要么苍白无力,要么“沉默”,甚至沦为“帮凶”,为纳粹罪行提供正当性辩护,使之可能。而等到二战结束,纳粹退出历史舞台,它们不沉默了,转而紧随大流控诉纳粹,而非首先忏悔。悖论的是,真正具备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创作者,在德国纳粹时期往往难以幸存。创作仿佛与正义、人性、良知已经决裂。阿多诺因此怀疑整个文明(但此后他重拾信心,认为“写诗”也许不是野蛮的,需要包括“写诗”在内的思考、创作与历史遗忘斗争,因为恰如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说的,“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那么,灾难之后,如何写诗,如何继续生活?问题的背后是德国到底要如何面对这段历史,如何进行反思。
我们今天推送的,是徐贲关于雅思贝尔斯《德国认罪问题》的文章。雅斯贝尔斯说:“政治意识越开明,人们越能感受良心的责任。”反思不是一部分个人的“认罪”。一个国家在政治灾难以后,集体反思成为一种为重新加入尊严人类的灵魂洗涤,“洗涤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它永不停止”,它使我们不断接近真实的人之为人的自我。
原文作者 丨徐贲
对民族国家中发生的政治和人性劫难进行反思,这就意味着要厘清不同成员应当担负的不同责任和罪感,接受责任和承担罪感,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这种历史性的集体自我重塑,在战后的德国是比较成功的。与德国经验相比较,世界上许多其他暴政统治(如拉丁美洲的军人独裁、南非的种族隔离等)就远远够不上1945年纽伦堡审判为世界设立的先例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对暴政统治的元凶们充分追究刑法责任和政治责任。
正如维拉威森修(Charles Villa Vicencio)在讨论南非种族隔离统治结束后的“真情与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问题时提醒的那样,出于国家内部和解的政治需要,许多国家都不能充分追究暴行元凶的刑责和政治责任,造成社会和文化日后长远的“道德和精神”弊病,维拉威森修还指出,由于德国经验的相对成功,“纽伦堡审判成为一种政治正确、道德正义和社会正派的象征”。必须看到的是,“道德的、形而上的和共同体的罪过同样重要,不清理这些罪过,严肃的国家和解或政治更新都不可能发生”。
刑责、政治、道德和形而上,这四种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对反思纳粹极权统治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由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

雅思贝尔斯《德国罪过问题》英文版
第二种是政治罪责,现代国家的所有公民都必须为国家之罪承担政治罪责,因为在现代国家中的每一个公民都不是非政治的。无论一个公民喜欢不喜欢他的政府,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必然涉及所有的公民。政治罪责对于那些反对国家罪行的公民看似不公正,但是每个公众却仍然必须为他的政府行为担负责任。正因为如此,每个公民有权利自由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对之施加影响,以避免承担他认为不公正的那种责任。在公共事务中不参与、不表态是一种变相合作的做法,政治责任更不容推卸。政治罪责面对的是国家历史的法庭。
第三种是道德罪责。道德罪责是个人在自己的良心法庭面前担负的责任。道德罪责的前提是绝对诚实,任何一个人的内心别人都无法知晓,所以每个人的道德罪责都必须由他自己来确定。然而每一个人却又必须不用任何借口逃避检查自己的道德。道德思过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估,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共同)认识”。

纽伦堡审判
第四是形上罪责,这是幸存者对死者或受害者所负的责任。尽管一个人并未加害另一个人,因而不能为那个人遭遇的恶负有刑法或道德责任,但出于人类共同体责任的本体联系,他仍然会因为不能阻止恶,在恶发生后仍苟活于世而有负罪之感。在别人受难时,谁淡漠旁观,无动于衷,谁在自己的良心前犯下的即是道德罪过。谁若睹之愤慨,但又无力阻止,谁仍会感觉到自己的形上罪过。人的形上罪责面临的不是自我良心的法庭,而是上帝的法庭。
雅斯贝尔斯指出,刑法和政治罪过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在历史性反思时所作的集体自我分析,而道德和形上罪过都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是个人的自我审视。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指出:“除非先有个人的自我审视,不可能有集体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个人能够首先做到,然后以交际的方式真正汇集到一起,那么就能扩大为许许多多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称作为民族意识。”
悔罪和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更新必须是集体的、公共的、持续的。具有公共意义的反思必须是集体反思,“集体的观念指导着人的判断和感觉”。在民族国家里,有一个总的民族群体,集体蒙羞后,亚群体同样因此蒙羞,“在今天的世界里,德国人……成为谁都不想是的那种人。在海外的德国犹太人也是蒙羞的德国人,因为他们总是不被看作为犹太人,而被看作是德国人”。在今天的世界上,就算是受尽痛苦的德国犹太人,从来没有恶行,也因是德国人而抬不起头来。这种感觉同时包含着政治罪过和道德罪过的因素。一国中的人道灾难是那里的人们为集体道德缺失所付出的政治代价,“以集体思维方式看,该担负的政治责任同时也是该惩罚的道德罪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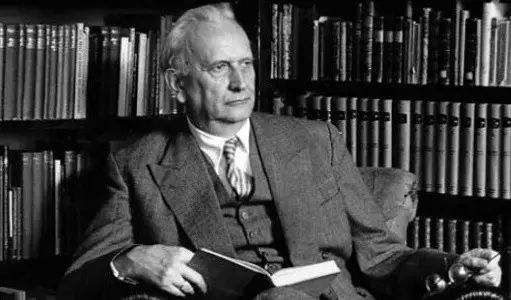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的集体责任思想带有韦伯式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苦难深重的犹太人会觉得对此不能接受。但是,雅斯贝尔斯并不只是就某个政治人道灾难发生的那一时刻来谈民族群体的集体性。他是把这个集体性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来考察的。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环境,因为个人的道德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个人并不能全然摆脱这些环境,因为无论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都是这些环境中的一环,无法逃避其影响,就算他反对这些环境也是一样。”
雅斯贝尔斯这里所说的是一种与政治形态相一致、并与之共生的国民道德素质或国民性。例如,专制政治与奴性人格(唯诺顺从、政治麻木、自扫门前雪、公共意识冷淡等)相一致并共生。这种一致和共生是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但在历史紧要关头表现得最为典型。阿伦特说,在纳粹德国,可以自称是反纳粹的只有那些被纳粹处以绞刑的人。任何存活下来的人,不管他心里多么不服从,多么反对,他必然没有可能将此公开展现出来,否则他就不会存活下来。雅斯贝尔斯说:“在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中有一种集体道德罪过,作为个人,我也有一份。政治现实就是从这种生活方式中浮现出来的……在道德罪过和政治罪过之间没有绝对的阻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意识越开明,人们越能感受良心的责任。”反之亦然,一个国家的政治越专制腐败,人民就越不在乎道德良心。

纳粹集中营的铁丝网
政治和道德之间存在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关键在于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有道德的作用”。政治专权扼杀政治自由所包含的人对自由的根本意识。人如果没有自由意识,就不可能有道德的自我约束。政治专横表现的不是权力统治者的自由,而是他们完全被权力和利益驱使的不自由。至于被统治者,他们的不自由造就了他们的无自尊。一个人没有自尊,道德也就不再可能。雅斯贝尔斯写道:“政治自由指的不只是一国实在法允许公民做什么,即人们普通所说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这种法定的政治自由固然重要,但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政治自由,那就是自行承担政治责任的自由意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是政治自由的初现。”而且,“越有知识,越有自尊……就越能觉察自己的政治责任”。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自由,一国所有的人民都得为他们政府的专制付出道德代价。
公共生活的政治不自由还会造成人的“内心不自由”。这两种不自由总是如影相随。内心的不自由有两种表现,“一方面是驯服顺从,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罪过感”。雅斯贝尔斯指出,政治不自由的驯服顺从本身就是一种双重罪过,“第一,它无条件地在政治上只服从领袖,第二,它服从的居然是这样一种(专制)领袖。驯服顺从的氛围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罪过”,“有罪过感才能接受责任,罪过感是人为实现政治自由而在心里奋起反抗”。政治不自由的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性的内心奴性。国民的政治自由启蒙必须以现实政治的开明、宽容和民主为条件。德国战后的民主政治为德国人民反思自己面对战争罪恶所负的责任创造了条件。反思是他们内心的政治自由的一种表现。
雅斯贝尔斯还进一步从民族文化的传统来看待集体罪过的问题,“我们不只是在现刻发生的事情中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不只对同代人的行为负有共同责任,我们还与传统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祖先的责任”。一味地在文化心理上妄自尊大,不愿承认“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包含着那些具有强大威胁力的东西,那些造成我们道德灾难的东西”,这本身是内心不自由的一种表现。对于纳粹造成的灾难,所有的德国人都负有一份罪责。这是因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德国文化和文化传统的一分子,每个德国人都是“德国的”或“德国性”的一部分,都“属于德国思想和精神生活……我和所有说同一语言的、有同一起源的和同一命运的其他德国人分担一种类似于共同罪过的责任”。这种罪过与公民个人责任不同,这是一种形而上的罪责。个人之所以负有形上罪责,不是因为他个人做错了什么事,而是因为他所属的那个群体已经做出了人之为人所不能允许的事情。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他无法撇清他的集体玷污。
当德国人在极权统治下集体堕落到人之为人的底线之下时,凡是德国人都会感到羞耻,都会觉得抬不起头来。这种羞耻感是一种在全人类的共同人性面前的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人之为人的骄傲和不能人之为人的羞辱,这二者都是先在民族群体中发生,然后才向更大的普遍人类群体扩展延伸。人首先必须在自己的民族群体中感觉自己是有尊严的一分子,然后才会意识到自己是普遍人类中有尊严的一分子。一个在自己国家当奴隶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形成关于人类的普遍尊严感的。所以,一个国家在政治灾难以后,集体反思成为一种为重新加入尊严人类的灵魂洗涤,“洗涤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它永不停止”,它使我们不断接近真实的人之为人的自我。
 2013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造访达豪纳粹集中营并敬献花圈
2013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造访达豪纳粹集中营并敬献花圈
民族集体反思的国民教育作用必须落实到社会体制中,其中最受雅斯贝尔斯重视的是大学教育。在关于战后德国大学教育的许多讨论中,雅斯贝尔斯特别强调的是大学去纳粹化和重振人文文化传统。雅斯贝尔斯是三四十年代经历了纳粹极权而且没有与之合作的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战后他在知识界发表的意见是很有分量的。战后初期,他协助创办了极具影响的文化刊物《转型》,为之撰稿的著名作家和学者包括托马斯·曼、阿伦特、马丁·布伯、布莱希特等。《转型》的宗旨,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是倡导“公共精神”,以此作为战后德国新人道秩序的基础,并且让人们“在讨论中知晓与我们生活有关的种种关系”。
雅斯贝尔斯讨论德国大学问题,是在《德国罪过问题》之后继续参与对战后德国政治重生和价值重建的反思。在他论及大学问题的文章中,他明确表示不赞成继续聘用那些曾经与纳粹沆瀣一气的教授,明确要求以民主的原则重组大学。他坚持大学对新德国的重生担负着重建人道价值基础的重任。这也是大学自我更生的任务。大学自己应该看到,它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道价值场所,极权统治总是把大学用作统治工具,大学非常容易成为极权权力统治的帮凶。
雅斯贝尔斯指出,自然科学研究早就以“科学不管政治”为借口脱离了普遍人道关怀的原则。科学家为纳粹杀人机器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成为间接的刽子手。因此,科学研究一定不能没有普世人道主义的关怀。科学必须了解,“人都是不可限定的,科学的任何一个分科都不可能充分认识人(的无限性)”。不仅如此,大学教育促进的普世人道还应当成为新德国民主秩序的普世法治的基础,“大学的理念增强的是法律地位上的人的自由”。每个人都在人类群体中有独特价值,都是不可代替的一员。每个人都应当体现人的存在目的,而不是他人利用的手段。这个康德意义上的普世人道主义在战后雅斯贝尔斯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民族国家群体意义,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中由法定权利保障的自由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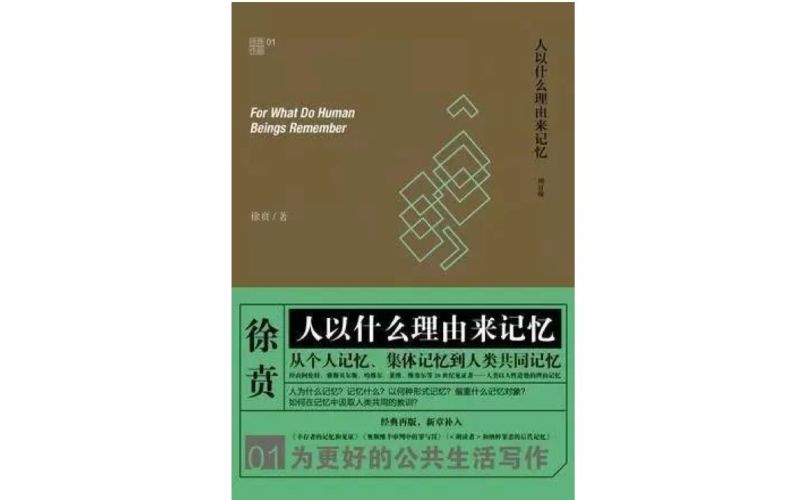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作者: 徐贲 ,版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三辉图书 2016年1月
本文经三辉图书授权节选自《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
作者 | 徐贲
编辑 | 余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