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徐学勤

叶匡政:著名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著有诗集《城市书》《小说馆》、文化评论集《格外谈》《可以论》等。主编有“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等多种丛书。摄影 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北漂”十九年,这是祖籍安徽的诗人叶匡政第二次在北京过年,上一次是因为遭遇2008年的暴雪,路途受阻,未能成行。去年年底暴发的疫情,让他临时退了票,决定再次留守京城。一个多月来,他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都被疫情所占据,他在微博上持续关注和转发相关动态,让众多求医无门的病患得到救治。
多年来,他一手写诗歌,一手写时评——用时而温柔、时而悲愤的诗句,倾诉内心的情感与哲思;又用严谨、冷峻、理性的时评针砭时弊,为诸多社会公共议题建言献策。他深刻反思了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诸种问题,这篇采访正是他对这些问题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包括对时代的审视、对人性和心灵的拷问,以及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求解。
没想到“黑天鹅”来得如此之快
新京报:这个特殊的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与往年有何变化?心态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叶匡政:这个春节让人永生难忘。我窝在北京家中,完全被新冠疫情的信息和舆论风暴所吞没,连挣扎一下的企图都没有,就沉入到海底。往年,我都会和家人回老家合肥,与父母兄弟一起过春节。除了2008年暴雪,在北京这19年一直如此。年前一周时,我已知疫情暴发得有些严重,只能退票取消行程。
我对疫情关注得比较早,去年12月底就看到自媒体上的一些传闻。因去年11月北京有过鼠疫报道,女儿学前班春节前出现了几例手足口病,已停课近3周,加上职业习惯,我较早就关注了这次疫情。今年1月初,想给武汉的好朋友打电话,但看到“未见明显人传人”的说法,觉得可能杞人忧天。到14日,各种来自民间的消息已比较明确了,可能会暴发一场很大的疫情。当天我给住在武汉的诗人刘洁岷打电话,告知他要注意防护。他取消了15日去医院看牙预约,后他被“人不传人”说法所惑,17日又接受了医生的回访预约,去了趟医院。好在他一直戴着口罩,自我隔离了14天后,才确定是虚惊一场。
我从1月15日后,开始重点关注疫情资讯,几乎浏览了中文世界所有重要的报道和传闻。过去我很少在朋友圈转发各种资讯,玩了多年微博,不想再把微信变成微博。但1月18日后,感觉事态严峻,我又不可能给每个朋友打电话,于是开始密集转发各种与疫情相关的资讯,多时一天要转30多条。这些消息或文章我都甄别过,须专业真实,或是最新的疫情进展,或是关于疫情真相的最新线索。我的朋友圈有5000人,各类型的人都有,有诗人、作家、学者,也有不少做媒体或自媒体的朋友,大家对新闻的关注度差别很大,我一是想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护,另外也期待有媒体人能跟进挖掘一些真相。对控制疫情来说,真相也是良药。
在近30天的时间里,心态经历了难以言说的起伏,从最初的担忧、焦虑到恐慌,其中夹杂着不解、震惊、悲愤、哀伤、无力、绝望、抑郁,五味杂陈,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扑面而来。我2003年在北京经历过非典,当时因网络还不普及,灾难现场的感受没有今天这么真切。如今社交媒体的发达,加上我参与了一些人的救助,看了很多发自救助者的一手信息,这些信息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把人凌空席卷到武汉现场,就像经历了患者同样的苦难。我想一直关注朋友圈的人,都有这样的切肤之痛。
新京报:疫情期间,对你冲击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对你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主要是什么?
叶匡政: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件事对我冲击比较大。一是武汉封城后,周先旺市长说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按概率,等于有三分之一感染者散播到各地,武汉疫情已演变为中国疫情。前几年就有人说“大洪水”,去年因各种局势复杂,很多人也料到今年会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只是无人料到,这只“黑天鹅”来得如此之快,如此迅猛,它带来的“蝴蝶效应”,将影响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全国一千多人死亡,数万人被病痛折磨,数亿人被禁足家中,湖北10多个城市宣布封城,大量城市停摆,无数行业受疫情影响无法复工,疫病蔓延的速度、规模与影响均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二是一位医生的去世,他在用生命警示我们,有一些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否则被剥夺的就可能是每个人的生存权。
目前,我还无法估量对我个人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但肯定更深刻地改变了我对未来生活的看法,甚至可能改变我原来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它会改变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你在武汉疫区,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一次创伤太严重了,随时间流逝,这种改变会慢慢显示出来。
苦难会模糊人们的记忆,
消除诉说的欲望
新京报:疫情期间你在读什么书?为什么选择这些书?阅读过程中有哪些感想?
叶匡政:疫情期间,我基本没心情读书,也没有选书的动力,有时为了让自己从信息漩涡中挣脱出来,读的也是去年12月初看的书。一本是布朗肖的《灾异的书写》,一本是刘小枫主编的《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后一本年轻时读过,现在重读感觉已忘得差不多了。近几年我读的书,多是与灾异、政治或民族灾难相关的,大概是想对自身处境有更深的认知。其实数年前,从事观念生产的人已感受到一场浩大的疫情,只不过它是在头脑间发生的,没有新冠疫情这么直观,砸到了每个人的头上。

《灾异的书写》,[法] 莫里斯·布朗肖著,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
《灾异的书写》是一本格言体的小书,是布朗肖晚年对奥斯维辛、灾异、书写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文辞有些晦涩,但很有嚼头,有些片断值得反复阅读。比如,它认为灾异总在我们掌控之外,当我们试图理解灾异,灾异却剥夺了我们思考的权利。灾异甚至会使我们失去对一切意志与内在活动的兴趣,它是站在遗忘一边的,不留一丝记忆,正是为了这种灾异造成的沉默,作家开始了艰难的书写。这和我们身处灾异现场的感受很像。
在武汉疫情现场,我们也看到大量死去的匿名的脸,这是灾异带来的藏匿。这些被灾异摧毁的人,不仅失去了外在形象,也失去了发出某种声音的可能。所以,布朗肖强调自己“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时,写作成为让沉默发声的唯一途径。作者让我们听到灾异中的沉默,你即使努力忘记灾异,那曾经发生过的灾异,也会从深处控制一个社会和它的每个人。就像当年的SARS,我们试图忘记它,但当它化身成另一种病毒卷土重来时,你才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控制着我们。当然这本书有非常丰富的面相,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建议大家在疫情期间读读,会有更深的感受。
之所以重读《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是因为当人觉得自我的可能性与现实的限制构成强烈冲突时,向宗教哲学求援几乎成为一种本能。自我的可能性与所处的现实密切相关,当这现实提供的自由范围越来越小时,就像我们不得不因疫情而禁足在家,放弃一切公共活动时,我们会渐渐感知到,生存将不再向理性和知性开放。我们遭遇了最深刻的悖论,人人都知道问题出在何处,却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
大量的媒体人离开专业场域,或不想写,或不能写,步入了米沃什所说的乌尔罗地,在那片灵魂饱受煎熬之地,残损的人类也必将承受心灵的困苦。当写或不写变得不再重要时,我们内心已发生了变化,被恐惧俘虏,或被厌倦征服,新闻的灾难已经发生。如某位作家所言:整个悲剧开始于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重读此书的目的:想把秩序重新带入自我,让生存摆脱紊乱和灾难,或许你只能向人类自身之外寻找支持。
在宗教中,有一个献身的理念,这种献身是指向未来的,它意味着扩展自我的可能性,它意味着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把自我引向一种重大的可能性。人生其他的可能性,都将从属于这种可能性。信仰可以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相信,它还是一种生存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包含了献身。当我们身处灾难现场,或许更需要这种思辨。
新京报:疫情期间,是否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
叶匡政:很后悔,因两个月前,已看过了这届奥斯卡的获奖片,疫情期间几乎没有好电影来分散我的注意力。与病毒相关的电影,也大多看过,只有一部《传染病》没看过。勉强看完,发现拍得太差,远没有今天的疫情现场这么惊心动魄。
倒是不久前,一部中国拍的电视剧《心灵法医》,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部凝视死亡的法医剧,其中透着对时代的审视、对人性和心灵的反思。剧中的逝者,都没留下遗言,但他们身上的痕迹、他们逝去的环境,就像他们的遗言。现在看,剧中那些死者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法医为他们寻找裂痕,让光照进逝者陷入黑暗的生命,也照亮生者的未来。但是,那些在疫病中死去的人,则悲惨痛多,匆匆被火化,亲人都无法守护在侧,甚至见不到最后一面。他们的生命,或许就这样永远沉浸在黑暗中。

2019年上映的电视剧《心灵法医》海报。
每个逝者都与我们相关,这或许就是人类的含义。这次疫情,为何让每个人都倍感痛苦,就是因为那死去的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法医是向逝者偿还债务的人,替逝者的亲人,替谋害他们的凶手,也替所有的人。然而,对于这次疫病中死去的人,可能无人来清还这最后一笔债务,亲人也永难放下心中的负疚。胡适说过“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而辩冤白谤的第一步,就是要发现死亡的真相。有真相,辩冤白谤才有可能,对于疫病我们同样需发现这样的真相,才能还清所有逝者的那一份债务。
人就像一粒粒稻谷,迟早要脱去肉体的外衣。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尸体、死亡这类故事,与崇高的情感无关。但看西方戏剧史会发现,崇高情感的根源往往与死亡和恐怖有关。因为我们面对的死亡,是一个庞大的不可知之物,它让我们焦虑与战栗,也让我们充满认知的期待。每个人都将面对死亡这一巨大的虚空,只有真诚地面对每一个死亡故事,才能唤醒对生命与爱的崇高意识。
新京报:近期是否有在写作什么作品?此时做这项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叶匡政:除了写了一篇《凤凰周刊》的社论,没写任何作品。当疫情仍在发生时,如果你设身处地感受着它的苦难,你真的无法写作,你是完全失语的。这就像你的亲人在生病,死亡的困扰仍压覆在你身上,你除了关注对方的信息,除了默默帮助对方,你确实很难思考。即使只有你一个人时,你也只能诅咒或哭泣。写作需要一定距离,如今因社会媒体和视频带来的惨烈的现场感,极易让人沉陷其中。
苦难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会消除诉说的欲望,会让意识麻木,即使是幸存者,开口说话也变成艰难。苦难让人感到的只有非意义。如布朗肖所言,悲观主义不书写。那些受难者不读不写不说,但并非缄口不言,沉默是表达,号哭是表达,缺席也是表达。在这场疫情中,没有牢狱,却处处都是牢狱,家也成了牢狱。
但不写并不意味着没有作品,我去年春节写的一些诗,似乎写的就是当下。我从两首诗中各摘录一节:
一
……
坟墓中,母亲起身
为泥地里劳作的孩子,洗净衣衫
那衫上有他们的泪
有他们的汗,他们的血
这地方,太阳来得
那么慢,升起时,月亮就出来了
受难者的尸灰
在地里凝为尘土
活人用它砌墙,造屋
闻着死亡的焦味入睡
这地方婴儿尚未降生
已成为新的受难者
二
……
每一句谎言,都压着老人
或婴儿的白骨
每一句谎言
都含有对邪恶的沉默
每一句谎言,都是末日
“在荒谬的时代没有正确的生活”
在荒谬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除了诅咒
也没有真正的诗人
要减缓民众的恐慌和焦虑,
信息真实尤其重要
新京报:疫情暴发以来,你一直在微博和朋友圈帮人转发各种求助信息,以及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就你的观察,目前的患者收治诊疗和疫情防控是否已经做到高效有序?对患者更快获得医疗救助有何政策建议?目前,社会的恐慌情绪是否有得到一些平复?
叶匡政:最早转发和求助信息,是好朋友黎学文在武汉的大学同学求助,我在朋友圈和微博都转了。《国家人文历史》总编王翔宇在微信主动留言,说他可以找湖北朋友提供帮助。然后,他联系了《人民日报》湖北分社社长贺广华,请他帮忙。第二天求助者住进了医院。有这个线索后,我开始注意收集求助信息,只要看到求助者,就转给王翔宇,这些求助者通过他们的帮助,陆续住进了医院。此后,中央督导组到湖北,与他们有了沟通,
请他们广泛收集求助信息安排住院。他们开始公开征集,一下出现了大量的求助者,也出现了很多志愿者,主动帮病人整理和核实求助信息。诗人巫昂和她的志愿者团队是其中一支,第一天通过我转的信息,就有40多人。这时安排患者住院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因为确实医疗资源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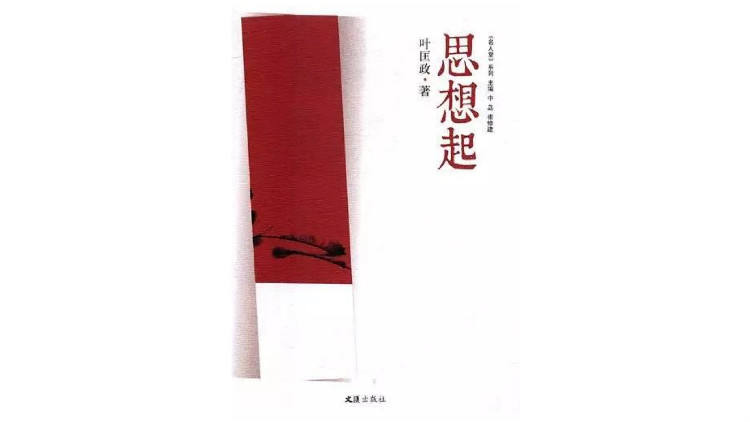
《思想起》,叶匡政著,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版
应当说,随着时间推移,患者收治诊疗的工作有所好转。但对有着5万多病患的武汉来说,即使医疗资源在全国算得上一流,即使有全国医疗队伍的援助,仍难以应对如此多的患者。这是导致武汉病死率较高的主因。出现这种被动局面,完全是因为武汉错过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期,一句“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误导了大量市民。
时间长了,人们的情绪会变得麻木一点。从这点上说,对病毒的恐慌情绪有所平复,但下一步可能对中国经济的恐慌情绪会进一步蔓延。这是一次重大的公共危机,要减缓民众的恐慌和焦虑情绪,保证信息的真实、客观尤其重要。湖北媒体在这次疫情报道中的完全缺位,地方政府和媒体管理者责任极大。现代社会有迅捷的电子传播网络,危机的传递和扩张也会变得异常迅速。如果官方媒体,作为民众最依赖的信息源,不去报道真实、客观的信息,只会引发民众压抑、惊恐、茫然的情绪,甚至导致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引发新危机。这种重大疫情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影响一个社会中民众的基本价值和行为理念。如果信息得不到完全开放的交流和沟通,只会加速各类流言和谣言的滋生。
只有对媒体完全开放各种信息,才能实现与社会民众的沟通。媒体常年在冲突事件的一线,特有的敏感使他们往往能立刻发现复杂现象背后的问题和症结,这种前瞻能力发挥得当,对于政府来说有预警功能。对民众来说,情绪也能得到合理的宣泄,有明显地缓压作用。怨气的隐藏和积聚,会使民众迷失在自己的情绪中,丧失理性的判断力,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给媒体以更大的自由度,其实也是在实现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这样只会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减缓恐慌情绪的发生,也能有效制止各类小道消息的传播。虽然治理危机的主导是政府,但在今天公民个人、公益组织和企业的作用也变得日益重要。这种突发疫情的紧迫性,要求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来完成治理。诸多治理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危机信息的真实与公开,这一切都有赖于对媒体的开放。只有如此,才能了解民众对政府现行方案的态度,才能真正动员民众参与到疫情的治理中,提高疫情治理的效率。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有哪些不够健全之处?类似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救助和民间自救该如何配合?
叶匡政:这次疫情的大暴发,确实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大量短板。去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还对外宣称,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实现了对39种法定传染病病例个案信息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在线监测。但从武汉疫情看,这个监测网络基本是无效的。高福称“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是没有出现SARS,但出现了超过SARS数倍的公共卫生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疫情已暴发一个多月了,问题的症结仍没有真正弄清。按已经公开的时间线可看出,在疫情早期,一线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已用最快时间,完成了测序、试剂等科研任务,并提出预警。这原本是一场可以躲得过的灾难,至少不会变得像今天这样人人自危。但为什么卫生管理部门与当地政府,对全社会的疫情预警竟一拖再拖,甚至远落后于不是疫源地的香港。这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真正隐患所在。是立法上的?是程序上的?还是有其他原因?
疫情暴发后,武汉在短时期内呈现了各种乱象,本应严肃、科学的疫情防控,竟荒腔走板成一场让人不堪回首的巨大悲剧。要应对这类公共卫生危机,需打破对传统管理模式的依赖,主动推动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弥补政府治理能力的缺陷,把政府本位变为社会本位,把控制变为服务,让多元的管理主体和民间组织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才能提高民众对未来的预期。
当社会一盘散沙时,一旦出现公共危机,必然把矛头都指向了政府,也只有政府可以依赖,而政府的能力又无力改变乱象,必然导致更大的危机。地方政府要想实现这类对公共事件的顺利治理,客观上需要在政府和民众间有一种中介机制,民间组织就是这样的中介机制。通过民间组织对公共管理参与,不仅更易获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与意见,也更易沟通与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和关系,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形成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公众三方共同受益的公共治理格局。

《格外谈》,叶匡政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版
让疫病之灾成为一个社会课堂
新京报:你撰写时评多年,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反思的?有哪些政策建议?
叶匡政: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这次疫情,几乎是一种社会机制整体溃败,才可能导致的结果:地方治理和应急系统的失灵,公共卫生防控系统的滞后,媒体监督功能的完全退化、慈善和社会组织能力的丧失、医护救治力量的紧缺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武汉的今天。我会陆续给《凤凰周刊》写至少五篇社论,反思这次疫情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目前只是简单重复一点第一篇文章中的观点:
疫情恐怖,但疫情如果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就更恐怖,痛定思痛,只有重新科学地预判与治理这一场浩大的公共危机,才能让中国社会的元气不至于过度损伤。
首先,政府要确保各地疫情数据的真实、完整、准确,因为全球的科学家需通过研究这些数据和案例,才能建立有效的科学模型,并弄清疫情流行中的一些关键事实,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对疫情造成的社会与经济伤害,政府也需有科学而充分的研判,不能再犯武汉市政府那种信马由缰的错误。今年正逢中国经济下行期,又有美国贸易战的复杂背景,这次疫情带来的经济伤害,显然要超过SARS时期。只有科学而充分的研判,中央政府才能做好有远见的规划,让宏观指导变得更体系化,对各行业的政策引导也能更细致到位,避免给国民经济与民生带来更大的次生灾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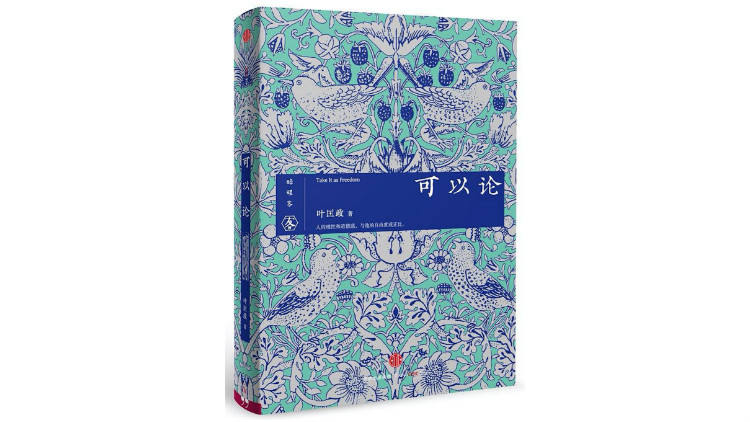
《可以论》,作者: 叶匡政,版本: 中信出版社,2015年10月
其次,要科学地引导社会预期。这是一场与危机的赛跑,越是这种公共危机时期,政府对社会预期的科学引导就越是重要。因为社会预期形成民众的社会心态,是民众对未来的估计与评价,这种评估会影响民众下一步的选择与行动。科学地引导社会预期,不是指碰到问题就一禁了之,只堵不疏,或以维稳为理由强压公众合理的权利诉求,这样只会进一步导致民众的社会预期过低,诱发一些抗争性事件,甚至引来社会震荡。
科学地引导社会预期,首先要制约权力的不可预期性。权力的滥用,往往是民众社会预期不稳定的根源。因为权力如果让民众感到捉摸不定,就会产生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另外,法治的保障也很重要。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在不确定中给人以确定感。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可预期性,当法律能充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时,就为公众的社会预期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让权力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能让身处疫情重压下的民众,体会到安全感。
当疫情变得无法避免时,我们如何面对疫情却能够选择。只有当全社会对疫情及各种灾难,有一种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民众对灾难的认知才会趋于理性,在了解疫情真相的同时,维护和尊重受难者的遭遇与命运。只有这样,疫病之灾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课堂,那些同胞的生命、苦难和悲伤,才不会白白付出。
采写丨徐学勤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