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庄沐杨
2010年,67岁的T. J. 克拉克(Timothy James“T. J.” Clark)结束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与同样到了退休年龄的妻子、艺术史家安妮·瓦格纳(AnneWagner)一起回到了伦敦。这位颇具影响力的英国艺术史家,如今在伦敦继续思考、写作,同时也开始写诗。
克拉克的学术经历堪称炫目且丰富,他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博士则是在著名的艺术院校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攻读艺术史。基于博士论文他又出版了两部著作,《人民的形象:库尔贝与1848年革命》(Image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848–1851)与《绝对的资产阶级:1848至1851年间的法国艺术家与政治》(The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自此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英国“新艺术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经历了在埃塞克斯大学的教职之后,克拉克来到了洛杉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艺术史,此后又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并在1988年回到美国西海岸,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自己的研究。
与他对库尔贝或马奈等画家的研究不同,《告别观念:现代主义历史中的若干片段》(Farewellto an Idea: Episodes from a History of Modernism)是一部更加“松散”的著作。构成本书的七个章节,其中有四篇是克拉克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论文,另有三篇新作,涵盖了现实主义、(后)印象派、立体主义、苏俄先锋派、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或风格,分别讨论了大卫、毕沙罗、塞尚、毕加索、马列维奇和利西茨基、波洛克等艺术大师。作为一名有着浓厚左翼色彩和左翼活动经历的艺术史学者,克拉克并不满足于在他之前艺术史家们对于形式和风格的沉迷,尽管他接受了良好的学术训练,但试图找到作品“背景”的文本性,并让背景成为“前景”(张茜语)。
与“现代主义”的观念道别
笼统来讲,克拉克的研究方法非常依赖对作品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与分析,一些学者也试图把克拉克归入到所谓“艺术社会史”这一脉络之中。当然,对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史背景的梳理,也往往会使得慕名而来的读者对于克拉克的研究,尤其是《告别观念》涉及的内容望而却步,因为哪怕是再人尽皆知的一幅名作,都有可能在克拉克的笔下,与宏大的历史事件与不起眼的历史细节串联在一起,使得对作品的解读多了一层绵密厚实的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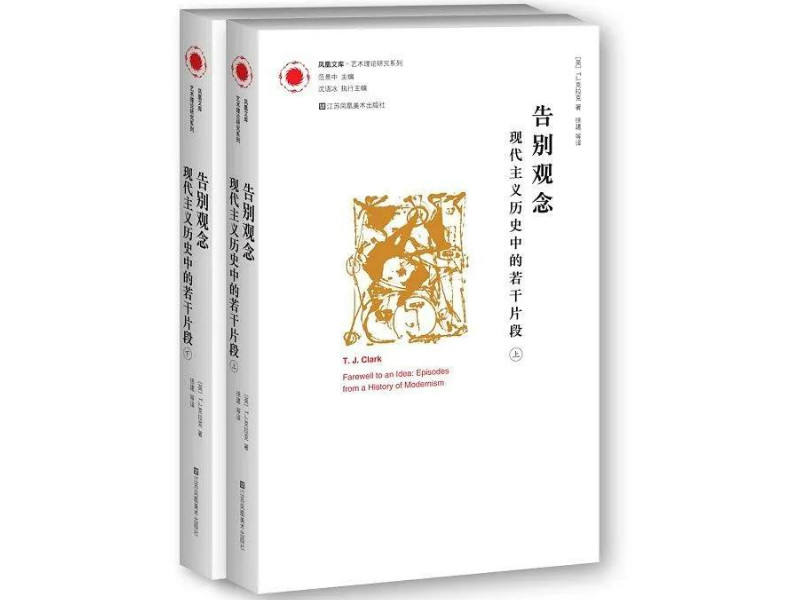
《告别观念》,T.J. 克拉克著,徐建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9年3月版。
不过,克拉克的研究并非是单纯地借助艺术作品来阐发对既定社会历史的见解,沈语冰就认为,克拉克的艺术史观和研究路径的独到之处在于,只有当“阶级”或“意识形态”等范畴“影响到绘画的视觉结构,从而改变有关绘画的既定概念(传统和惯例)时,对阶级与意识形态等范畴的阐发才是有可能且有必要的。
无论读者在进入本书之前是否对克拉克有所了解,或许你在读导论的时候,就已经能嗅出克拉克行文间浓郁的左翼气息。这位自诩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史家,在书中挖掘现代主义的“废墟”与探究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时,总不免将左翼意识形态代入其中,或作为反思对象,或作为参考坐标,并试图通过拼接这些断片,来对“现代主义”这个观念道别。
在第一章对《马拉之死》的研究中,“人民”的阶级立场在法国大革命的浮现被克拉克反复锤凿,以让其在画布上被“物质化”地显现,并经由艺术作品加以铭记,为此画家大卫本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立场也在克拉克的笔下逐渐被明晰;而毕沙罗的《两位年轻的农妇》在他看来,则可以从画家的表现技法,以及作品的社会属性出发,窥探到无政府主义在现代画作中的萌芽;至于马列维奇和利西茨基这对师徒的先锋派创作,则响应了苏俄革命时期对乌托邦的极端性的描摹与折射。
“立场先行”的艺术家?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层左翼色彩过于浓厚,一些评论在肯定克拉克的部分分析之余,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质疑,即克拉克在解读这些作品时,是不是“立场先行”了?从克拉克的导论来看,这七篇文章之所以被串在一起,是因为作者试图在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摘取出一些“断片”,通过这些看似松散无关的作品,克拉克希望挖掘出现代主义是何以被发明和延续的。
多伦多大学的MarkA. Cheetham认为克拉克的书中免不了一套提前预设的说辞,目的在于用这些文章的私有性来自我解套,从而可以有更宽裕的余地来排布他对画作的政治性理解,而克拉克对历史时间坐标的认定,也显示出了他反后现代话语的坚决心态;而另一位艺术评论家DavidFraser Jenkins则认为本书更多是克拉克作为左翼人士的自我书写,他的立场先行甚至使得在他解读作品时,将画面呈现的因果颠倒,例如在谈论毕沙罗的第二章里,克拉克甚至是在以“政治伪装”(Political camouflage)呈现毕沙罗的技巧,为这位画家安上无政府主义的立场。

T. J. 克拉克 (Timothy James Clark,1943- )
对克拉克政治立场的警觉,使得评论界的目光更加挑剔。同时,也有另一部分读者和评论家察觉到了这本书的忧郁气息。考虑到本书的一半篇章都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再加上克拉克在论及社会主义时的乡愁笔调,这种忧郁气息似乎由来有自。或许,苏东剧变与冷战终结让这位老左翼也倍感唏嘘。在此基础上,在翻阅克拉克的文字之余,笔者也试图用克拉克式的方法,摸索其学术经历之外的另一层“背景”,并简单地把这些背景前置到对克拉克著作的理解中,使它们成为另一层文本。
他从不是象牙塔里的“星巴克左翼”?
身为左翼的克拉克从来都不是一个安身在象牙塔里的“星巴克左翼”,他的经历表明了这位艺术史大师终其一生都花了不少时间在左翼政治活动和结社之上。在求学阶段,克拉克曾经是“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一员。这个左翼国际组织成立于1952年,曾受到先锋派艺术、字母主义运动和包豪斯运动的影响,成员大多是以变革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理论家、艺术家等,《景观社会》的作者居伊·德波就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该组织对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克拉克本人只在1966-67年间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此后他就由于观念不合,被组织开除。1997年,克拉克曾经和唐纳德·尼克尔森-史密斯(Donald Nicholson-Smith)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何艺术杀不死情境主义国际》(WhyArt Can't Kill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文章,梳理了组织内部的分歧,以及对于左翼和斯大林主义的争论。
除去情境主义国际,克拉克还曾卷入到一个极端组织KingMob之中,这个组织是情境主义国际等左翼运动在英国的变体。该组织追求并强调文化上的无政府主义,并试图通过暴力活动促成无产阶级革命。而即便离开欧洲到美国任教多年,克拉克也没有停下参与左翼运动和结社活动的脚步。在来到伯克利这个美国左翼思潮大本营之后,克拉克和其他一些学者,包括妻子瓦格纳一起加入了一个名为Retort的社团。社团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既有克拉克夫妇这样的人文学者,也有科学家、律师、编辑等。该社团定期集会,所有成员都对资本帝国持反对态度,他们共同完成的著作也由Verso出版社出版。
这些经历比起克拉克的学术简历,更像是一条“暗线”,藏匿在他更为人熟知的艺术史家这一层身份之后,像他拾起的现代主义断片一样,看似只是注脚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或者至少有彼此关联的可能。基于这一条暗线,或许读者也可以更清楚克拉克对于《马拉之死》里人民何以呈现的执念,对于毕沙罗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坚持,以及对苏维埃乌托邦本质的体认。克拉克就像一个裁缝,试图将七块断片裁剪成一件成衣,在向既往的现实主义告别之余,直面左翼在后冷战时代的挑战。
作者丨庄沐扬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