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黄兆慧
罗素的访华历程
1920年6月30日,罗素访问苏俄结束后返回英国,在他的巴特西公寓,从一大堆信件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讲座协会(主要发起人是梁启超和蔡元培)的讲学邀请信,希望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为期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罗素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而历经一个多月的苏俄之行,也使他对新兴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正是在这样心境下,罗素希望到中国去寻找新的希望。1920年10月12日,罗素应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机构邀请,偕他的情人勃拉克(Dora Black)乘“波多”号轮船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中国之行。
在罗素抵沪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并无人来接船,致使罗素怀疑邀请他来华讲学是不是一个玩笑,后来证实原来是接待员把轮船到达的时间弄错了。次日,江苏教育总会等七个团体在上海举行了欢迎罗素的晚宴,罗素在宴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英文演讲。演讲的内容被翻译刊登在《申报》上,这篇被翻译的演讲内容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不过罗素本人似乎没有为争论而分心,几天后他应邀到杭州游玩。在游览西湖过程中,轿夫们抬着罗素在崎岖的山路中穿行,虽然辛苦,但轿夫们却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忧愁。罗素对中国人的这种性格和人生态度大为赞赏,他在《中国问题》和《自传》中都提及了这件事情。但鲁迅对此不以为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有别的意思罢。”在鲁迅看来,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是要不得的,它造成了中国自古以来无数的人吃人的“人肉盛宴”,这种性格和人生态度必须由青年们去打破。
罗素从杭州回到上海,再从上海经南京逆流而上到达长沙。他在长沙连续作了四次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在访华前,罗素曾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做过调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借鉴苏联模式,他们满怀期待罗素为他们指点迷津。然而罗素在演讲中却批评了布尔什维克,这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如毛泽东、陈独秀、陈望道等等)大失所望。湖南省长谭延闿亲自出面宴请罗素、杜威和蔡元培等人,再三挽留罗素,希望他在长沙停留一周,但被罗素拒绝,他希望早点赶赴访华的终点——北京。
罗素抵京后,于11月7日在北京大学作了第一次“哲学问题”的讲座。此后,罗素陆续发表了系列演讲,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等,通常称之为罗素在华“五大演讲”。可能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罗素的“五大演讲”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以致许多学者认为,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罗素感受到了中国学生的冷淡,他到中国的热情也逐渐消退了,一切就像例行公事那样按部就班。这种热情在罗素一次生病后被彻底浇灭了。罗素赴河北保定的育德中学进行演讲。在这次演讲会上,罗素为了保持一贯的绅士风度,拒绝穿外套,他因此受了风寒,之后感染急性肺炎,病情危重。这个病折磨了罗素三个月,他深感疲惫,归心似箭。养病期间又得知勃拉克已有身孕,罗素毅然决定返回英国。
1921年7月6日,罗素在教育部会场作了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的临别赠言。罗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为中国未来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有两件事实必须提出:第一,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第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应当进行彻底改造。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
五天之后,罗素正式与中国告别,结束了他这段颇为曲折的中国之行。

1920年,罗素偕第二任妻子多拉·布莱克来华讲学。图为罗素(前排右一)与中国学者的合影。
罗素演讲的两次风波
关于“保存国粹”的辩论
罗素在中国的第一次演讲,就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辩论。1920年10月13日,罗素在欢迎晚宴上作了简短的演讲,次日《申报》便刊登了罗素演讲内容,新闻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报道后不久,此文便遭至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
在同一期《晨报》上,还刊登了F.L支持罗素观点的文章《改造社会与保存国粹》,与周作人针锋相对。该文认为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对罗素的质疑传播开来后,张申府立即致信给《时事新报》,认为《申报》断章取义,报道的内容与罗素原意相去甚远。罗素的意思是要国人有创造的精神,应警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像中国传统艺术一类的好东西应当保留,而以“保存国粹”归纳罗素的演讲,极容易误导大众。张申府的辩解,暂时平息了罗素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所引起的争论,但罗素对中国问题态度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尤其是主张激烈革新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罗素在上海的第一次演讲,已经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而他在长沙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传播开来后,直接引发了那场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此次论战的导火索是张东荪发表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张东荪陪罗素在湖南演讲后返回上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此文,他认为发现“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根本“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张东荪援引罗素的观点,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实业、增加“富力”才是解决落后局面的根本之道。
对张东荪所说的“教训”,陈望道、江春、邵力子等在《觉悟》上发文给予回击。陈望道发表《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直接驳斥张东荪的观点。江春发表《张东荪现原形》,他先贬损了张东荪一番,然后抓住张东荪提出的“人的生活”观点进行批判。邵力子批评张东荪,质问他谈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是否不可兼容、“人的生活”究竟如何解释。
张东荪不甘示弱,他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对陈望道、江春等进行回击。经过几番论战后,陈独秀终于忍不住了,分别致信罗素和张东荪,让他们直陈在中国施行社会主义的态度。在给罗素的信中,陈独秀想让罗素声明在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是否是罗素本人的观点。从现存文献中,未找到罗素的答复。
陈独秀与张东荪对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辩论,然而陈独秀对张东荪的回答始终不满意。经过这次论战,张东荪渐渐远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他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仍然援引罗素的观点,认为当时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然不会有好结果,应当首先“发展实业”和创办教育。虽然支持社会主义者的矛头直指张东荪,但他们实质上是对罗素不满。袁振英连续发表《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与《罗素——一个失望的游客》,表达对罗素的失望之感。

勃拉克在中国的院子里为罗素拍照。
在此次论战后,许多中国社会主义者与罗素分道扬镳,他们不再相信罗素,反而更加坚定了走“以俄为师”的道路。
罗素与中国思想家
在访华前后,罗素与当时中国的许多思想家产生了交集。
在中国宣传推广罗素思想的学者,当首推张申府。张申府最初了解罗素,是在北大藏书楼阅读了那本《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这本书让张申府爱不释手,并由此对罗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罗素”这个中译名,便是由张申府翻译而来。在罗素来华之前,张申府就各处搜集罗素的文章和著作,并译成中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此外,他依靠自己掌握的材料编了一个“罗素著作目录”,收罗了当时所知的罗素的全部著作。连罗素都感慨:“他对我的所有著作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得多。”在哲学上,张申府企图把孔子、列宁和罗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哲学体系,但他终究没有实现。
张东荪对罗素的态度,经历了从“十二分”崇拜到比较失望的转变。张东荪服膺于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思想,为此他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罗素从上海到长沙的演讲活动,张东荪基本都参与其中,他对罗素也都是赞成的。但在罗素发表了那篇离华演说《中国的到自由之路》后,张东荪对罗素的态度开始转变了。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在《时事新报》评论栏写了一篇《后言》,称罗素的“临别赠言”与其以往的主张多有矛盾之处,并毫不客气地说:“罗素自己之思想尚未确定,何能指导吾人?”

1920年,罗素(左二)与张申府等人在北京的合影。
胡适对罗素访华的态度,较为消极,甚至还有点抵触。在梁启超邀赵元任担任罗素的随行翻译时,胡适就曾劝阻赵元任,让其不要被人利用。胡适在日记中只提到过几次见罗素的情形,并且他从未参加过罗素的演讲。他说:“罗素的演讲,我因病中不曾去听,后来我病愈时,他又病了,故至今不曾听过。今日最后的一次,乃竟无缘,可惜。”与其说是无缘,不如说是他有意为之。胡适当时主要接待他的美国导师杜威访华,当得知梁启超等人邀请罗素来华时,他很可能心存芥蒂,因为这会极大影响杜威的关注度。此外,胡适熟知西方哲学,但他提倡的是实用主义,他对罗素抽象的逻辑分析方法持批判态度,这个逻辑分析方法无法像科学方法那样应用到人生问题上。
毛泽东与罗素有过直接接触,罗素在长沙连续作了四次“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毛泽东受长沙《大公报》的委托担任演讲的记录员之一。毛泽东对罗素的政治思想是比较了解的,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说他赞成罗素的共产主义主张,但对罗素所采用的渐进的、改良的、教育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
在所有追捧罗素的人中,徐志摩恐怕是最疯狂的那个。徐志摩原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他读了罗素的著作并被罗素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毅然放弃读博深造的机会,决心到英国去从师罗素。可等他到达英国,罗素却踏上了访华旅程。没有追上罗素的脚步,徐志摩便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但他此时的兴趣转向了文学,迷恋上新诗。徐志摩虽然没有成为罗素的入室弟子,在思想上深受罗素的影响。他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后,人们在缅怀他时,还对徐志摩没能师从罗素感到遗憾——要不然他肯定会成为罗素在中国的得意门生。
在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那里,罗素就是他所接受的“西方资源”之一。王小波多次引用罗素的“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来表达他的“崇智”立场。他吸收了罗素的哲学、数学、逻辑、社会评论等观点,以自由思想贯彻文学创作,抨击非理性和思想束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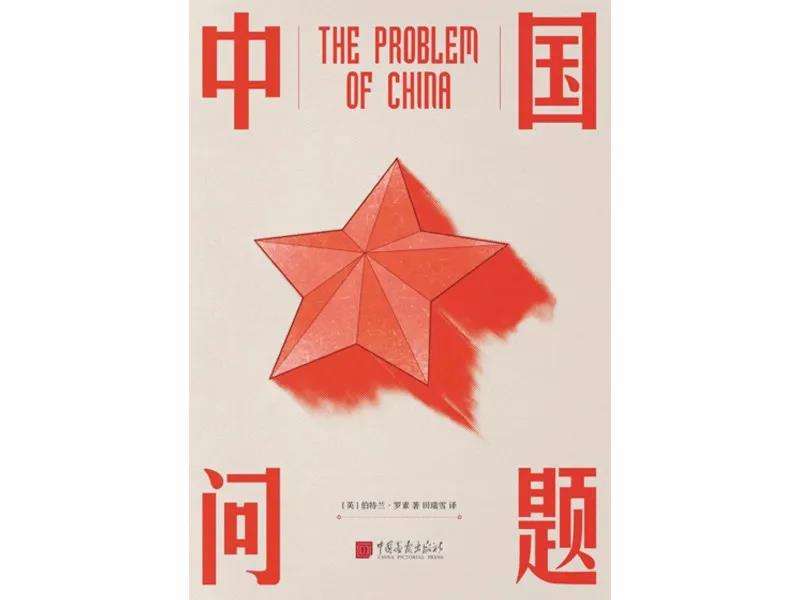
《中国问题》,[英]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9月版。
罗素访华回国一年之后,出版了《中国问题》(1922年)一书。在《中国问题》的开篇,罗素指出了当时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将这些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如果文化问题能够解决,那么经济或政治上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在罗素看来,要理解中国问题,首先就应当了解中国的历史。罗素对19世纪以前中国的主要朝代以及主流文化进行了梳理。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按照以往的历史延续下去可能并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打开市场以获取大量金钱时,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因此,分析中国问题时也要考察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
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特殊,一方面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又极端贫穷、实力孱弱。因此,分析中国的内部问题也相当重要。罗素认为,虽然中国在政治上无能、经济上落后,但是它的文化却值得重视。罗素对中国文化不吝溢美之词,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如果它能被全世界所采纳,那世界肯定会比当时更加和平幸福。
罗素对于中国的未来保持着充足的信心,主要是因为“少年中国”(Young China)的崛起——这些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未来。除了中国本身之外,与中国关系最重要的国家不是西方列强,而是日本。因此,罗素在书中用了较多篇幅介绍日本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罗素看来,当时中国最需要警惕的是野心勃勃的日本,而历史也如罗素所料。
分析完中国与诸列强的关系,罗素回到了文化问题上,他详细对比了中西文明:“我们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解释。”罗素认为应将二者融合起来,以此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对中西文化比较后,罗素进一步从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及中国的工业等三个内部条件分析了中国问题。最后,罗素为中国的未来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立有序的政府;二、独立发展工业;三、发展教育。罗素看到了当时古老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但他也相信中国人能够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同时融合西方的长处,以实现独立和富强。
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重新阅读罗素这本著作,并将其与中国这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我们会惊叹于这位西方大哲对中国问题的把握之准、分析之精与专研之深。虽然罗素在书中论述的种种问题已成历史,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中国未来道路的建议,仍然值得我们一读。
罗素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写《中国问题》的,他一再强调当时中国只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文化却有它的长处。他说:“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民族”。由此可见,罗素不仅指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优势。
罗素思想的余波
有学者认为,虽然当时罗素访华举世瞩目,但他终究没有成为现代中国思想舞台上的主角,没有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关键思想家。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主要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哲学,当时的中国确实鲜有人能理解。然而,他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流行的“清华学派”身上,其代表人物有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荫麟、张岱年、沈有鼎等。“清华学派”以提倡新实在论著称,而新实在论正是摩尔、罗素在西方引领的一种哲学思潮。在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哲学家的著作中,都明确提到了他们同罗素哲学之间的理论渊源。由此而言,中国现代哲学的兴起,与罗素哲学密切相关。
不只是哲学上,罗素有关教育、婚姻道德的论述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陆续被翻译到中国,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引起过不少讨论,这为中国的新式教育、新式婚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罗素思想在近现代中国,留下了独特的历史印记。
作者 | 黄兆慧
编辑 | 李阳 董牧孜 徐伟 安也
校对 |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