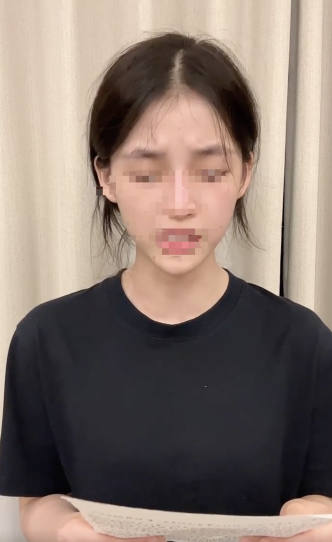每晚十点,刘丽萍要吃红白蓝三颗药片,混上小拇指指甲盖一样大的钙片——47岁了,骨密度偏低,得补钙;而红白蓝是保命的药,用来抵抗艾滋病病毒。刘丽萍性子急,药摞在手心,和着一口水就全吞了下去。

学生们的药盒,内装有一周的剂量。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抗艾药的种类、剂量各有不同,根据服药人的身高体重等变量做调整。和刘丽萍一起生活的孩子们,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不按时吃药,艾滋病患者会产生耐药性,影响治疗效果,长期会威胁生命。
有些孩子年纪小,不爱吃药,刘丽萍就把药藏在馍里,半哄半骗地喂下去。为了督促孩子吃药,刘丽萍曾把每一种药都尝了一遍,“看看到底是什么难吃的味道。”
刘丽萍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也是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生活老师。红丝带学校是中国唯一一所专门接收艾滋病学生的义务教育制学校。2006年,红丝带学校成立,本是病房志愿者的刘丽萍留下做了生活老师。
红丝带学校里的学生,全部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半数以上是孤儿。
十多年来,刘丽萍照料近50个艾滋病患儿的生活起居、治疗服药,更重要的是,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教会他们认同自我。

刘丽萍与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母老虎”
每天早上8点,刘丽萍坐进办公室,能听见背后一排教室中的朗诵、问答、嬉笑——声响持续一整天。
刘丽萍将近一米七高,短发、五官精致,爱抹亮一些的口红。她说自己两年前动了场大手术,鬼门关边走了一回,术后就学会了化妆,因为“想漂漂亮亮地生活。”
因为长期服用抗艾药物,脂肪代谢障碍的副作用体现在她身上——双腿如晾衣杆般过分消瘦,脂肪堆积在颈背部,按病友们的说法,这叫“水牛背”。她爱穿裙子,从网上“团”来的黑色长裙,一条几十块钱,宽大的裙摆盖着纤细的脚踝。
上课时间段里,她与学生的交流相对少,一下课,学生就撞进她的世界:也是受药物影响,孩子们多数比同龄人矮小,十岁左右的孩子看着只有五六岁。
到了晚上,刘丽萍趿着拖鞋在宿舍走廊来回地走,催学生洗澡、洗衣服,问他们有没有完成作业,有没有复习。有学生跑回宿舍,她跟着过去瞧一眼,门一开,就好气:“你看你的房间,像猪窝。”她对内务要求很高,如果房间脏得过分,学生在上课时都会被叫回来收拾。
睡前发零食,也是朝走廊里喊一嗓子,一人一包辣条,28个学生,谁拿了、谁没拿,刘丽萍记得很清楚,发得只剩一两包了,还能准确地喊出被落下者的名字。
9月4日下午,18岁的甄遇乐回学校看望老师,前两天,甄遇乐被天津一所专科学校录取。
甄遇乐微胖、白,面颊上常有两块红晕,一米六的个子,看上去与普通孩子无异。

学生们蹲着看书,刘丽萍悄悄拍照。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两三岁起,甄遇乐开始频繁发烧,身上溃烂,捱到三年级,一次高烧连烧了两个多月,到运城的大医院做检查,才知道是因母婴传播得了艾滋病。
等病情稳定,再回老家的小学,班主任劝她“回家去吧”。
甄遇乐想继续读书,但是离异的父母都不管她,奶奶和姑姑将她送到红丝带学校,她在红丝带学校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考上大学,她很高兴,但她父亲的态度模糊不清,母亲更是闪烁其词,“我一提钱,她要么说没钱,要么就不说话。”
她这次来,带来了录取通知书,刘丽萍当即向她拍板,不用征求家里的意见,“上学必须上。”若实在凑不出钱,母校给她想办法。
除去学习、健康,二十多个学生的吃穿用度,刘丽萍也全部要管:学生的衣服是她挑的,零食由她发,连零花钱都可向她要。
刘丽萍自认是严厉型的师长,常常和校长郭小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郭小平说,自己哄孩子,刘丽萍就负责批评,气急了会吓唬学生,有学生在手机通讯录里将刘丽萍备注为“母老虎”。
她和另外两位生活老师将学生看管得很紧,周一到周五要上交手机,一旦发现私藏者,则半年不得再用手机。
刘丽萍的严厉来源于担心,作为艾滋病患者,她明白艾滋病群体的前路艰辛。
人生转折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临汾市郊,许多出租车司机摸不着路子——从城市的主干道转出后,走一公里的田间小路,再拐两个弯才能到达。
2005年,时任临汾第三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发现在院的几位艾滋病小病人无处上学、渴望上学,就召集几名医护成立了“爱心小课堂”。
刘丽萍的人生转折也发生在2005年。
这一年她的舌头上长出一层白疮,吃饭、喝水都疼,辛辣的东西一点儿不能碰。她家所在新绛县的医生看了她的症状,委婉地让她去市里做个血液检查。
在运城的医院做了检测,两小时后,接到通知艾滋病病毒阳性结果的电话,“顿时觉得昏天黑地。”
其实疾病早已初现端倪。那几年刘丽萍经常扁桃体发炎,“跟白喉一样,嗓子里边全是白的。”她推断,病毒感染的源头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她做宫外孕手术需要输血,“医院那时候是混乱的,从献血者身上抽了血就给你输上,也不做检测,血型一样就直接给输。”
刘丽萍回忆,她随即赶去临汾三院治疗。站在院艾滋病区的门口,眼看标注着“病一区”的走廊长且阴森,无底洞一样的绝望,“我想着我不要进去,我一进去就真成了艾滋病人了。”她忍不住在门口痛哭流涕。
这时,有护士领着一个女孩儿走在走廊里,“胖嘟嘟的,大概只有七八岁。”那是后来就读红丝带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女孩儿跑到刘丽萍跟前,盯着她看,“觉得你一个大人在那儿哭什么闹什么?”
护士告诉刘丽萍,孩子是因母婴传播的。刘丽萍形容自己“忽然就平静了。”
“我想这病孩子也会有?我至少已经有过几十年的健康人生,而他们从出生起就完全没有选择。”
郭小平说,刘丽萍2005年5月开始在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就来到“爱心小课堂”做志愿者老师。
最初的“爱心小课堂”里有4个孩子,2006年9月1日,小课堂升级为学校,孩子从4个增加至8个,刘丽萍留下做了生活老师。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刚开始,授课老师特别难招,没有编制,只能请村小的民办教师。第一个外聘的老师待了不到一年,与孩子们相处时戴着口罩、穿着白色医护装。第二个老师只待了一学期。孩子们想和老师亲近,抱一下、拉个手,都会被有意避开,“完全不发生身体接触,不会直接碰孩子碰过的东西。”
2011年,红丝带学校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有了编制,可以正式招聘老师。现学校有编制内老师十名,编外老师及工作人员数十名。
红丝带校内现有的28个孩子,多在艾滋病确诊后受到当地教育系统歧视,无法继续上学,有的因为发病早,到了八九岁还从未上过学。

刘丽萍给学生发零食。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数学老师贺延庆介绍,许多孩子送来了,得从认识阿拉伯数字教起,更遑论简单的加减乘除。学习习惯也不到位,“乱拿别人的东西,听到上课铃不知道进教室,不愿意写作业。”普通学校的一年级语文课,两三个月就能教完拼音,但在红丝带学校,得反复教一年。要让孩子们跟上普通学校的学习节奏,短则一年,长则两三年。
学生卢昆来自四川西充县,戴副厚厚的近视眼镜,15岁的年纪,个头还不到一米四,火柴人一样瘦小。他的父母不知所终,一直由爷爷带着。
2014年,他被老家村民写联名信“驱逐”,后经好心人联系,2015年时被送至红丝带学校。
刚来学校时,卢昆的认知、语言能力都只有三四岁,讲不出十字以上的句子,经常偷跑出学校。刘丽萍就漫山遍野地找他,吃饭、上课、说话,一点一点来。
毕业生王子晨是红丝带学校的第一届学生。他的母亲因艾滋病去世,此前与父亲、奶奶生活在一起。在老家,他与家人的碗筷分开,不在一个锅里夹菜。偶尔回家,他打电话给刘丽萍哭,说自己在家无所适从,只想马上回学校。
郭小平说,孩子在老家分餐、分居很平常。“那群孩子就需要刘老师这样一个像母亲的角色,她是病人也是长辈,懂感同身受。不用说什么大道理,给煮碗面条,买个苹果,陪他们玩,给他们陪伴。”对艾滋病患者,尤其是年幼的病童,除去治疗,“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在红丝带学校,没有寒暑假、双休日的概念,孩子们基本不回老家,老师们也经常要住校值班。
刘丽萍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她的丈夫、女儿对她放下家庭、侧重学校的行为,“不支持也不反对。”这在她看来就是一种支持。
红丝带学校成了她的另一个家。她不爱光亮,选了一间没窗的宿舍。房间格局向阴,会泛潮,屋内的被褥常不干爽。但日子久了,她很习惯:“在学校总睡不醒,回家反而睡不安稳。”
刘丽萍形容自己和学生是“抱团取暖,互相治愈”——艾滋病患者的世界,完全健康的人很难深刻体会。她在“圈内”充当了半个媒婆的角色,为艾滋病人们“在内部找对象”。她觉得人生漫长,比起“双阳”,“一阴一阳”的伴侣组合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2017年,红丝带学校第一批16名学生参加高考,共14名学生考上专科及本科;今年,有两名学生即将考研。对这些开蒙晚的孩子来说,“是质的飞跃。”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刚办校时,学生们去村里理发,理发师一见他们就说有事,要关门走人。学生们回来全哭了,刘丽萍只好带他们去更远的、陌生的理发店。“那时候觉得科普没用,你也不能骂人家、逼人家。”
2010年,刘丽萍带着王子晨进电影《最爱》的剧组做群众演员。剧组中有六位艾滋病群演,片方要同时拍摄一部艾滋病群演的纪录片,挨个问群演们是否愿意在镜头前“露脸”。

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红丝带学校是中国唯一一所专门接收艾滋病学生的义务教育制学校。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起先,刘丽萍见到摄像机就下意识地回避。挣扎了几天,她决心坦诚:“如果你自己都在歧视自己,怎么再去反歧视?”最终,她和王子晨,以及另一位来自上海的男性艾滋病患者“露脸”参加了纪录片的拍摄。
2012年5月26日,刘丽萍和郭小平一起发起“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邀请各界志愿者和艾滋病患儿共同进餐。甄遇乐记得,她第一次参加“午餐日”,大家搬了桌椅到学校的后院里。小小一片院子挤了上百人,“有明星、企业家、大学生、公益人士,还有外国人。”就吃些普通的家常菜,每张桌子坐几个孩子、几个志愿者,互相夹菜。“我觉得很有意义,让更多的人不惧怕艾滋病人,不歧视。”
今年,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已办至第九届,成为我国仅次于世界艾滋病日的艾滋病主题宣传活动。
常年参加公益活动,频频被媒体曝光,刘丽萍不再避讳向公众告知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渐渐地,她对自我的态度,从躲避变成认同:“(得病)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不是我的错。”
甄遇乐说,刘丽萍是学生们的主心骨、教导员,“她会和我们说,不要因为自己是HIV感染者就感到自卑,只要我们把药吃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来红丝带学校任职之前,刘丽萍开过服装店、加油站,做过保险推销员。她出生在农村,但不喜欢农村生活,觉得节奏慢、没意思。现在她过上最慢的生活,每天一成不变地徘徊在宿舍和教学楼之间。
从前学校没有围墙,但院子里种的果树从来不会遭窃。摘了果子主动往附近的村庄送,也没人敢要。现在,学校收获了果实、蔬菜,村民们也想来弄些吃。“以前宣传工作不到位,大家害怕,可以理解。后来我们每年都做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有歧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9月5日傍晚,刘丽萍走出校门散步。田间开阔,横向里吹来凉风,刘丽萍说多自在。
正在地头干活的老农和她攀谈,给了她一把花生。小路上,成群的学生觅食而回,在双休日去附近购物、闲逛已成常事。这天他们问村里人买了一袋油炸鸡锁骨,“买两斤,送一斤。”
(文中甄遇乐、王子晨、卢昆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