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徐悦东
近日,美国西海岸所遭遇的山火仍在持续,已造成36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巨大的山火所造成的烟尘使得波特兰、旧金山、西雅图等地一度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美国加州山火
随着气候变暖的持续,我们似乎越来越常在媒体中听到山火的新闻。除此之外,北极冰盖消融、海平面上升、夏季的异常高温、各种“百年一遇”的灾害天气频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这些词汇在新闻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地球似乎面临着危急存亡之时刻,瑞典的“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振臂一呼,成了欧美青年所追随的明星偶像。在欧洲,各国政坛掀起“绿党旋风”。由于人类的活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生态环境,科学家们更是将新的地质时代命名为“人类世”。这都说明环保问题的紧迫性。
不过,环保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简单的议题。环保之所以那么难,是因为它还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旦拉扯到具体利益,事情就变得复杂了。由此,当我们要讨论环保以及人类未来的时候,我们脱离不了对环保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即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我们需要一种建构世界的全新知识,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来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刺激着许多思想家在理论上进行深入探索。对日常生活感受细腻的人类学家,则善于从具体事物中寻找零光片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指被资本主义用作生产活动而被改造后的空间和景观)上,人类还有何种生活的可能?在《末日松茸》中,人类学家罗安清从松茸身上得到了许多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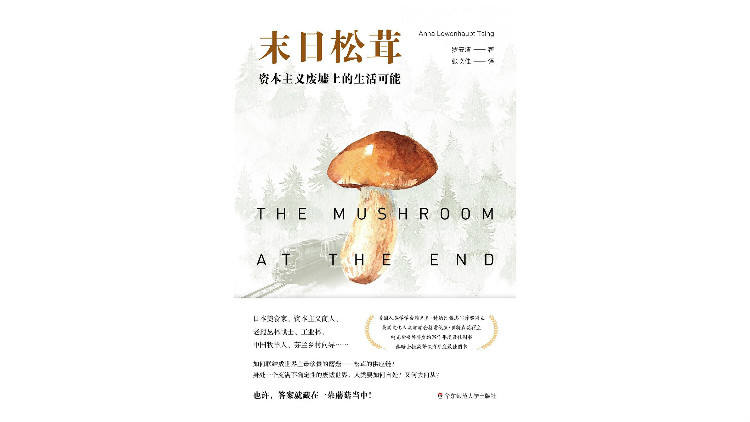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美]罗安清著,张晓佳译,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生态:交染的艺术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一个进步的思维框架下长大的。我们会理所当然对明天抱有期待,明天越来越好才是“正常的”——科技越来越先进、经济持续增长……进步似乎成为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只有人类会对未来有具体的期望,并且在当下为此进行准备。通过统一的进步时间观,人类实施着自己改造世界的计划。
但人类并非唯一拥有改造世界的计划的物种。许多物种都有着自己的时间观,它们按照季节性的生长律动、生命繁殖模式和地域扩张来重塑这个世界。只不过,现代人的自负使得人类无视其他物种的计划。其实,这些世界改造计划彼此重叠。人类也常常卷入进多元物种所参与创造的世界当中。人类的驯化农作物、牲畜和宠物,使得人类的维生方式为其他生物腾出空间,一起塑造出这个多元物种共存的世界。
松树和它们的真菌伴侣就是这样的案例。当人类学会用火后,人类通过焚烧林地,让土里长出野草吸引动物前来,然后加以捕猎以维生。松树和它们的真菌伴侣就经常在人类烧毁的环境里茁壮成长,一起利用明亮的开阔空间和裸露的矿质土壤。这些生长的真菌里就包括我们所喜爱的美味佳肴——松茸。

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生于1952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曾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所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可以说,松茸是包括人类在内多元物种共存互动所产生的意外馈赠。松茸是无法人工培育的,但没有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和影响,松茸就无法产生。比如,美国俄勒冈州的国家森林深受百年来人类的伐木计划和救火计划的干扰。当地的林务局致力于找出能获得木材巨鳄们支持的保育措施,又要抑制森林火灾的发生。于是,伐木工们大量砍伐西黄松。但假如林务局成功阻止了周期性火灾,西黄松就无法繁殖,伐木活动将不可持续。而且,由于没有火灾,冷杉和扭叶松就快速繁殖起来,它们的枝叶更易燃。因此,林务局试图恢复西黄松植被,并通过砍伐措施控制冷杉和扭叶松的生长。
这片国家森林充满着人类干扰的痕迹,西黄松、冷杉和扭叶松都是通过人类干扰才得以生长的。在这片被“毁掉”的工业森林景观中,新的价值——松茸却意外丰收了。松茸并不在林务局和伐木工干扰森林的计划中,但它恰恰是人类无心插柳的干扰所带来的。对于罗安清来说,这就叫交染(contamination)——不同物种改变世界的计划互相交染,共同世界和新的方向就可能会出现。西黄松、冷杉和扭叶松成了具有交染多样性的物种,正是交染多样性创造了松茸。
我们似乎能从松茸的诞生中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环境深受人类干扰的地球上,存不存在一种万物众生共存的可能?多元物种的交染会不会给世界带来新的馈赠?这是《末日松茸》里思考环境问题的起点。人类创造新世界的计划纵然已经改变了全世界,但实际上,人类的计划与其他物种的计划仍然交染在一起。每个物种都是靠着互相交染,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生存的。在这个多元物种共存的世界里,交染就是一种让“1+1>2”的合作,即便这并不是一种和谐的方式。这是松茸能教给我们的道理。
新京报:你尝试要寻找一种以变动为本的生态学,认为多元物种能既不和谐又无需争夺地一起生活。为何这些多元物种无需争夺却不和谐?这又给人类社会怎么样的启示?
罗安清:这里面有几种所谓的“不和谐”。其中一种就是,多个物种在一起生活,他们不会彼此伤害。他们也不会互相对对方彼此有益。但是,在历史上,有些偶然性的因素突然出现,使得这些物种突然开始互相利用。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这些物种都应该为他们能在一起生活而感到幸运。
这是一则体现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结盟”后潜力的寓言。假如我们停止对非人类世界进行征服或扩张,我们有机会挖掘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合作的潜力。
新京报:你之所以提出“交染”,是为了根植抗衡现代知识体系里的“进步等于扩张”的潜在假设,比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人口遗传学“自私的基因”等都有相似的框架(即每个学科的核心都是自足的个体行动者,目的是最大化个体利益。“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成为许多现代学科的潜在假设)。你认为,这些学科实际上忽视了交染(contamination)的可能性。但是,以“经济人”为基础的学科知识,大家可以通过公式和数字较好理解。但受交染的多样性是拒绝被简单总结的,“总结”是现代知识的特点。你觉得该如何建构这种重新认识世界的知识和方式呢?在认知论上,大家该如何认识这些交染的多样性呢?
罗安清:我建议用“互相关联的故事”来作为理解交染的历史和多样性的方法。这也就是说,生活中的很多知识是很难被简单总结为一些公式来进行认识的,而需要大家像听各种互相关联的故事一样,通过耐心阅读和仔细倾听来理解体会。与功利主义哲学相反,我不希望非人类世界是人类要去认识和研究的客体。倾听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里的“互相关联的故事”,是人类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在世界上生存、实践和创造历史的方式。

松茸
新京报:由于人类将自身和自然对立起来这种认知视角,反过来也使得许多环保主义者希望人类别去干扰自然。他们觉得,人类干扰是万恶之源,若没有人类存在,大自然就可以“恢复健康”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许多自然保护区和相应的森林保育方法就在美国建立了起来。你在书里说道,美国人就认为保育森林最好的方式是自我恢复。但日本里山(satoyama)的保育工作者却认为,人类刻意干扰森林对森林保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里山的保育实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理念提倡人类活动应该与非人类活动一样都是森林的一部分。因此,里山打算复兴“农耕森林”,他们会像以前的农民那样去打理山坡,挖出灌木丛的根——恰恰因为城市化,农民们进城当了市民,森林就被放任自流自生自灭了,这使得山坡愈发脆弱。日本的松茸文化(即日本文艺中对松茸的礼赞),恰恰就是农民们无心插柳干扰自然的成果。
那么,希望人类别去干扰自然是否也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何种人为干扰对于大自然来说是合适的?这是否意味着,在现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理想的?
罗安清:在这个大灭绝时代里,为其他物种提供避难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许多人说,人类可以在其他物种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靠自己生存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我不是在主张人类能通过干扰自然以获得更多好处。确实,从日本里山实验里面,我认识到我要尊重“荒野”(wilderness)——“荒野”在文化上代表着一种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尽全力和非人类世界保持着最好的关系。我希望“荒野”能成为美国人的里山。我现在会比以前更推崇“荒野”——不是那个要铲平、推倒的“荒野”。
城市的生活经验总让我们产生一种盲目的二元论:我们总想象着有一个未受人类玷污的大自然。实际上,世界上的森林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物种一起创造的。对于在环保上的保守主义者来说,里山就是一个需要他们牢记的重要例子。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正当化人类干扰。停车场和森林还是很不一样的。许多停车场虽然种满了树,但是停车场的生态系统相当贫瘠。里山则是一座森林,因为它不仅有树,还有动物、真菌和草本植物。在鼓吹人类干扰对生态系统有益之前,我们必须评估,这个生态系统有多复杂,允许接受人类哪种程度的干扰。
里山实验的意义在于,它允许我们质问西方的二元论——文明与荒野的对立。里山有着人类干扰,但其生态环境所依赖的干扰并不仅仅只有人类,还包括其他许多其他物种的“干扰”。中国也有许多跟日本里山相类似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物产大多富饶。这也是因为人类对自然有所干扰,但并没有完全控制生态环境的原因。
现代化来自于人类想要完全掌控自然的需求。人类世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所造成的工业景观成为了这个行星的环境灾难。我没有浪漫化我们的过去。在现代化之前,地球的生态系统很明显比如今健康得多。为了回应今天的环境问题,我们要比那些支持现代性事业的人,更关注他们在改造地球景观的时候,无心插柳所造成的影响。

日本里山保育的志愿者在打理山坡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在现代人类的认知中,物种间的世界观中最重要的似乎是“捕食者-猎物关系”,这意味着物种之间是一种互相消灭的关系。共生关系却成为了反常现象。这是结合遗传学和演化论的现代综合论(modern synthesis)现代性叙事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以松茸为代表的真菌似乎反对自我复制铁笼的理想代表和隐喻。早在蘑菇生成之前,真菌的身体就在森林地下以网状结构和束状结构伸展开来,与植物根部和矿物土壤结合在一起,与许多植物形成共生关系。这让我联想到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茎块”(rhizomes)。你有受德勒兹影响吗?你觉得你的菌根(mycorrhiza)的隐喻和德勒兹的“茎块”有什么不同?
罗安清:的确,德勒兹也深深影响了我。德勒兹将“茎块”的隐喻锁定他的“战争机器”(war machine)的概念里,这是一种能无法停止反抗至上而下权力体制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在植物各种各样的根部里,“茎块”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许多茎块有毒,能抵御生物的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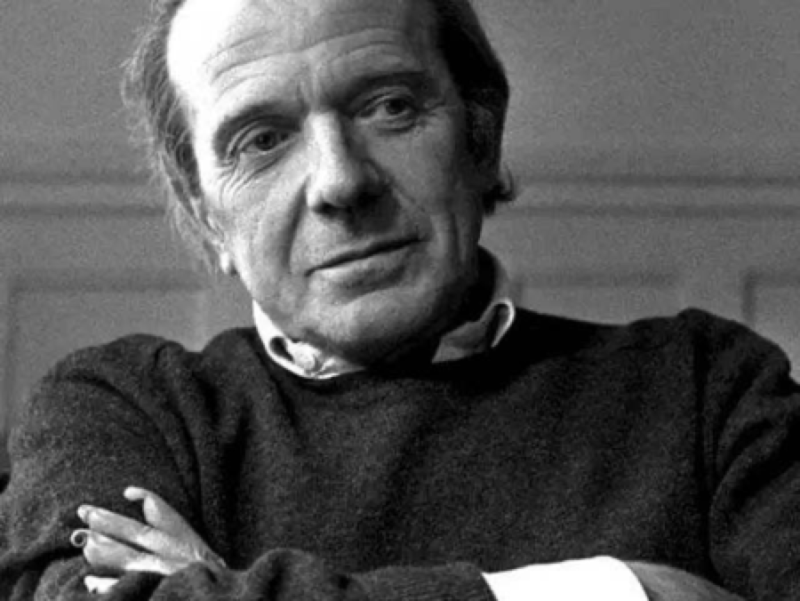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
我当然不是要用攻击性来作为我论述菌根的基础。菌根是真菌和植物根部的共生产品,它们互相传递各自所需的营养。菌根互惠共生的特性为森林带来益处,它们建构了多种生物的共同体。因此,菌根激发出一种新的生态学——每个生物的发展都需要物种间的互相依赖。这种物种间的关系比“捕食者-猎物关系”更重要。每一个物种,包括人类,都需要其他物种的协作,才成为它们自己。对此,女性主义哲学家唐纳·哈拉维将其概括为“共同生成”(becoming with)。这个概念受德勒兹的启发,并试图超越德勒兹。
资本主义: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
罗安清的松茸研究源自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在罗安清学术生涯的早期,她关注在全球化中的边缘族群。她的第一本书《在钻石女王的统治下》(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就是关于印尼加里曼丹岛梅拉图斯山脉下的达雅族(Meratus Dayak)的研究。她研究达雅族的萨满教、政治制度、神话传说与他们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罗安清第二本书《摩擦:全球联系的民族志》(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依然与加里曼丹岛的梅拉图斯山脉有关,她通过对梅拉图斯山脉附近的田野调查,研究跨国企业对环境破坏和当地社区所造成的影响。
罗安清对全球化研究的兴趣,使她想研究一条没有被国际贸易规则完全标准化的供应链——像小麦、煤就是典型的被供应链标准化的商品。有一个熟人给罗安清介绍,松茸就是这样一种未被标准化的产品——松茸无法人工栽培,罗安清可以去俄勒冈州的松茸采集地看看。等罗安清到了俄勒冈州后,她发现,这个研究选题对她来说堪称完美——采集者大多从老挝和柬埔寨来避难的瑶族和苗族人,他们过着没有社会安全网的生活,却能在采摘中找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他们未受保护的劳动加入了这个全球贸易体系里,满足着大家对松茸的需求。而这片森林的采伐史和防火史恰恰意外地产生了松茸。松茸成为了反思全球化资本主义供应链、生态哲学、族群政治等议题的切入点和和连接点。
罗安清从松茸的供应链中洞察出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人类财富集中的历史是通过使人类和非人类成为可投资的资源而实现的。这段历史让人类和万物都逐渐被异化,成为流动的资产。这种异化促成了景观的改造,成为资产生产的废墟。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不一样,罗安清认为经典思想家并没有发现在新时代所出现的“攫取资本主义”(salvage capitalism)。规模化(scalability)是经典资本主义的特点,其来源于欧洲殖民者的种植园——种植园里生产的作物是独立的、劳动力也是封闭性的、可互换的单位。复制定植苗、强迫劳动、开疆辟土,这里面蕴含了现代工厂的基因。这个现代化和进步的梦想,最终使得资本要将地球上的一切都进行规模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批判这种经典形式的资本积累模式。

日本的松茸市场。
但是,松茸养殖是不可规模化的,没有人雇佣这些作为难民的采集者,他们都是自愿过来采集的,过着非常不稳定且没有保障的生活。但这一切却振兴了本遭伐木业衰落而衰退的森林经济。罗安清从中看出了新时代的症候:在新自由主义下,规模化只是技术问题,规模化的计算方法和不可规模化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管理之间的衔接,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典范。精英们只需要将账本规模化,生产也许不需要规模化。
其中,供应链就起到了从不可规模化的劳动(非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到规模化计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转译”(teanslation)的过程,使财富积累成为可能。供应链的下游企业,为了从中间商中支付最少的成本,可以完全不关心原产品是怎么制作的——即使这个产品中的某些零件是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或是家庭作坊的童工制作的、某些零件所需的矿物在开采过程中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等——这些问题都在整个供应链中都不受监管,因为下游企业将上游产品层层外包出去了。罗安清认为,这就是一种攫取。
新京报:你能讲讲攫取资本主义中的“攫取”与经典资本主义中的“剥削”的不同吗?
罗安清:“剥削”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被雇主剥夺掉的。“攫取积累”的概念则有所延展,攫取的范围包括非人类产品的价值和那些资本家并没有直接控制的劳动力。这些非人类产品的价值和不受直接控制的劳动力所制造的价值分流到精英阶层手里,这就是攫取。“攫取积累”允许资本家和投资者从非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里获得利益——不管那是动物、植物或是其他种类的人类劳动。
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的概念来看,通过暴力和占有来进行攫取积累,跟经典的阶级剥削理论是很相似的。其实,攫取积累是持续不断地进行原始积累的其中一个元素。尽管资本主义持续制造“废墟”,但攫取积累依然可以在废墟里发生。(编者注:比如在伐木业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松茸。)
新京报:攫取的地点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和外部,所以你也称这种模式为“边缘资本主义”。你在书里说,像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等批评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席卷天下,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单一团结来攻克一切,但这个希望是何等盲目。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承认经济的多样性。你所提到的与经典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边缘资本主义”将如何让我们反思资本主义?这又给了我们思考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
罗安清:请别误解我,我对哈特和奈格里有着极大的尊重。我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比较单一。我理解他们的意思,若资本主义是一整块的,它就能被一个联合起来的力量打倒。

迈克尔·哈特(右)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左)
相反地,让我们想象一下,联合起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力量是由各种各样的群体组成的,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从男人到女人,从原住民到有色人种。这种政治联盟能让我们看清权力体制中的许多裂缝。这些裂缝就是这群人需要去做出改变的地方。“边缘资本主义”对这个政治联盟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也是他们对抗体制时要有所作为的地方。
有些群体联合起来反对警察暴力,有些群体联合起来反对对某些宗教的不宽容,有些群体联合起来反对污染环境。要让这些群体结合起来,我们就需要把他们所反对的议题,跟更大的资本主义系统结合起来。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日本战后发明的供应链和外包模式使得日本经济大为成功,这种方法并被美国学去。如今,供应链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在世界各地。你认为此次疫情会让供应链资本主义受到重创吗?反全球化的声浪越来越严重,未来供应链资本主义是否会受到影响?
罗安清:历史学家安德鲁·刘(Andrew Liu)有效地分析了新冠病毒肺炎为何是一个“及时的流行病”。他对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链进行了分析和跟踪,发现供应链在这次病毒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希望我能对此比较自信,大家对健康的关心能改变供应链的状况。大部分国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到疫苗研发上,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疾病的政治生态学。这一波大流行病过去了,下一波大流行病还会来。人类的供应链资本主义将自然界的病菌带给了人类世界。假如我们不想在多重流行病浪潮中生存,这种组织世界的方式就应该被质疑。
新京报:对于在松茸供应链中扮演着采集者的劳工来说,松茸展现出全球政治经济的裂缝。美国森林里的许多松茸采摘者是少数群体——来自老挝和柬埔寨的难民。他们所干的活不是有着稳定工资和福利的“标准就业”。他们过着生计不稳、安全感匮乏的生活。这样我联想到当下西方左翼中流行的“Precariat”——这个结合了“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词,用来形容全球化时代处于不稳定雇佣中的劳工们的新处境。“Precariat”们有着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对工作缺乏认同感。你认为这些采摘者属于“Precariat”吗?在你的书里,我看到许多采摘者在采摘中找到了自己的认同,比如对自由的文化实践、森林让他们延续着旧日的习惯和梦想等。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罗安清:据我的理解,有关“precariat”的争辩,主要是“无产阶级”这个词已经无法代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了。与其进入这场争辩,我试图对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进行有效地分析。

松茸
对于松茸采集者来说,这些“precariat”有着属于他们的快乐,但他们没有社会安全网的保护。他们的快乐是“自由”。但是,一旦他们生病或受伤了,没有人有医保。在美国,国家没有负担起居民的福利,特别是医保、养老保险和育儿保险等。因此,这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劳工,需要通过他们的交际网络,让他们的许多亲属好友一起互帮互助才能生存下来。对于资本家来说,不支付工人医保的钱当然是好事。对于工人来说,这事就十分复杂了。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国家福利制度的变化影响了美国对移民的同化政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美国国家福利制度的被侵蚀,使得美国的“大熔炉”成为历史,并形成了当代亚裔独特的美国公民身份认同。当代的亚裔所投奔的“自由”仅是市场的自由,当然,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具世界主义的文化建构。有人曾将美国对待移民的这段历史形容为从“大熔炉”到“色拉碗”的变化。你是如何看待美国的这种转变?如今,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另类右翼的崛起和美国社会的撕裂,是否意味着“色拉碗”为代表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
罗安清:我对美国正在崛起的白人民族主义感到沮丧和恐惧。他们对暴力的自信使得“特朗普现象”甚嚣尘上。我只能希望这个社会能有所改变。我知道这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现如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刻。这使得我这本在2015年出版的书都过时了。我害怕美国政府在压力之下会利用大众流行的最糟糕的偏见,来加强自己的权力。
撰文 | 徐悦东
编辑 | 李永博;王青
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