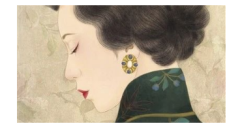撰文丨一把青
耗时8年整理,跨越近半世纪,累计700余封,共达70万字的张爱玲与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书信集,终于在这个“爱玲爱玲年”的九月揭开神秘面纱,这枚震撼学界与张迷的重量级炸弹,衬得两岸三地数不胜数的纪念活动与文章都成了自顾自的热闹,熙熙攘攘,失了颜色。

张爱玲的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
在梳理家族旧事的《对照记》和回忆良师益友的《忆胡适之》二文中,张爱玲都使用了“偶像有粘土脚”的比喻——发现偶像其实是土偶,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倒给了神坛之上祖师奶奶自揭粘土脚的契机。不同于作品中苦心经营的张腔,书信特有的即时性,让情绪更为松弛,双方几十年情谊,亦使表达无所顾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Deleuze)认为,书信除了本身的价值,往来运动形成的“流量”,使流量路径具有穿透力,换言之,世人皆知她一双冷眼,移居美国后大隐隐于世,殊不知,在无数长信与短笺中,她仍旧散发后场观察的触角,在更私密的一隅,长袖善舞,笔耕不辍。
人情篇
单论与张爱玲的书信,虽有夏志清、苏伟贞、庄信正等人先后公开发表,但论及亲疏,始终是业务往来居多,难免应酬话语,止于客气,与对宋氏夫妇“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的相知相惜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上文对胡适,在《忆胡适之》(收入《张看》,1976),她写与炎樱去拜访他,攀谈如对神明,最后一次见面,“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在1956年的信中,她却回忆“《传奇》与《赤地之恋》他(胡适)看了很不满,上一代人确实不像我们一样的沉浸在西方近代文学里……我和Fatima(炎樱)到胡家去过一次后也没有再去找过他们,你知道我是too self-centered to be anyone’s fan,别人对我一冷淡,我马上漠然。”
文才如胡适者,张爱玲也把他划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范畴之外,对宋淇妻子、任职美国新闻处的邝文美,却是从旗袍料子、流行发型,到明星八卦、阳台花草无所不谈,工作经验欠奉的张,要她务必把办公室动荡局面详细讲给自己听,更陪她骂同事,“成天和那些讨厌的人周旋,实在使人觉得气闷(后来在美国伯克利做研究员当上班族,张爱玲也开始在信中抱怨起来)”,心情郁结时,她不愿给邝写信,因为“不能代表这一向的愉快心境,不免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结婚时,她想起邝文美爱吃汉堡,想让她尝尝赖雅的厨艺,赖雅中风后,看医生须坐轮椅,焦头烂额中,她仍不忘分享丈夫叫住一个路人“嘿,给你一块钱,把我推到那里去”,对方恕难从命,因为也是病人的笑话博卿一笑。

张爱玲。
不同于20岁时赞叹好友炎樱的古灵精怪,张与邝文美,三十余岁相识,如此为对方着想,带着些女学生气,抛弃笔下世故,暴露全部天真,事无巨细,连带着她的儿女子孙,照单全收一律牵挂,下笔动辄“担心到了极点”、“高兴到了极点”的闺蜜情,让人想起胡兰成《今生今世》中著名的感慨,“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皆成为好”,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主角易帜,胡兰成亦已成信中“无赖人”。
《小团圆》初出土,读者尚感叹,就算写得种种不客气,胡兰成(邵之雍)虽未获得桑弧(燕山)般“那时幸亏有他”的盛誉,但也始终未出恶声。原来在1976年信中,作者早有自知之明地定义,“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笑也没像后来那样”——后来是哪样呢?是读到旧作中收录炎樱致胡兰成的信,“光是她替他起的名字已经译得肉麻得毛发皆竖(炎樱称胡为兰你(Lanny)”;收到《山河岁月》,她说“实在是写得太蹩脚”,书中引用自己的话满目错漏,但“他所说的话我全忘记了”,反驳又须参考书,不由失笑;《今生今世》虽只看了女学生代写的跋,也痛批“学的一口怪腔,末句‘先生的事,是大人的事’,看得哈哈大笑”,再版时翻了翻想看有没有添写关于自己的,“添了一些,我也没看,不然《小团圆》更写不出了”;文坛后辈朱天文赠书亦不领情,悻悻然写“朱西宁的大女儿寄她的小说集来,自序通篇是悼胡兰成”。
张胡的恩怨,固然不似盛九莉与邵之雍那样一别两欢,在《小团圆》一书的宣传上,宋淇却构想,可向皇冠出版负责人平鑫涛透露一二,新作写及与胡兰成情事,以平鑫涛的商业考量和江湖气,消息自会不胫而走,引发坊间好奇,有助销路,不同于平时背对读者、隐世独立的印象,张爱玲竟同意此提议,由是观之,如果说邝文美贤妻良母式的斯文,是张氏脑中长篇大论静默的聆听者,宋淇的形象,则如军师与顾问,为她经营文字、版权与财产,敢言又有谋划,数十年如一日,深藏功与名。
写作篇
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小说《色戒》的从无到有。
宋淇不仅是故事题材的提供者,更反复与张爱玲商讨情节,例如易先生为王佳芝买钻戒的场所,他指汪伪时代百货公司没有首饰部,不妨改作钟表店,整点钟声大作,添紧张气氛,店内装修、店员、布置逐一告知,附上亲绘地图,设计逃跑路线,那边厢,张爱玲亦问他意见,“她带着戒指走,心理暧昧,仿佛不过是得钱买放,主题模糊了,不带走,就不用预付金条,比较即兴”,宋淇认可,“这戒指是拿不得,一拿女主角的人品、故事的力量完全削弱了”,如此细节,鱼雁往返钻研近两年,可见布局之缜密,创作之纯粹,“不吃辣怎么胡得出辣子”,神来一笔的结局,也是由宋提出,被张采纳。

电影《色·戒》
就连《谈吃与画饼充饥》此类看似轻松,全篇写吃的短篇小品,二人都要就措辞和典故,探索将近半个80年代,历经无数誊抄改写、页码抽换,有时工作量大,张更颇不好意思地道歉一句,“我又要来了!”,遑论译《海上花》这种学术性十足的大工程,宋淇不厌其烦为她查询中英词源、对照翻译版本、邮寄参考书籍,有趣的是,在1983年信中我们看到,《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经典的两句“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初为“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中国人三弃海上花”,是宋淇指出“以张爱玲对中国人口气太大,不像你平日为人为文,而且很容易为别人捉牢‘小辫子’”,两个月几易其稿,方改为“看官们”——张氏从早期锋芒毕露,到平淡而近自然的晚期风格之蜕变,宋淇自然功不可没,但在作品背后的幽微角落,像此处的“张爱玲对中国人”,读者仍可一瞥她不期然流露的、18岁时《天才梦》中所言的“瓦格涅的疏狂”。
因是诤友,有的话也只有宋淇敢说。皆知张爱玲晚年受跳蚤和皮肤病所困,在美国各旅馆间频频搬家,信中写得触目惊心,时而是蟑螂爬过眼球,时而是小虫包围伤口,宋淇点出,“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作茧自缚”,叫她要舍得钱,搬高级公寓,比张爱玲还长一岁的他,周身病痛仍兢兢业业为她的稿费买外币、办存款,隔个一年半载总要汇报一份结合世界格局与理财利率的财务分析,劝她“盗墓式”地出版《惘然记》、《余韵》等陈年作品总不是办法,“你好久没有写了”,要趁仍有笔力,借港台张爱玲热的东风再推新作,中文版《少帅》搁置多年,张学良90年代结束台湾软禁生涯,张爱玲信中以作谈资,宋淇则回复“你信中讲了不少关于他的话,我想我们应该write him off(把他一笔勾销),做正事要紧”,恳切之余不可谓不严厉,一片冰心,焦急得紧。
除了《少帅》,书中我们也得以管窥张爱玲数个提上议程而终未付梓的写作计划。像是以曹禺为原型的《谢幕》,男主角早年投身话剧大出风头,因时代封笔,“长江后浪推前浪,浪头都冻结成了冰河,保全了盛名”,最终如演员在台上突然病发,“幕急下,替他遮盖了”;还有《美男子》,讲移民美国的高学历华人夫妇,开超市为生,美男子离了婚,被许多来LA做明星梦的少女看中;以及长篇散文《最后的老电影》,分析为什么有人爱看老电影,甚至《天安门外地球村》,徒有一个天马行空的题目……
有的是初步构思,有的是资料收集,何以未能成文,我们无从知晓,反观其22岁时的《论写作》,“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人生恐怕就是这样吧?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晚了”,年轻专属的骄纵言犹在耳,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迈入最后十年,信中占大篇幅的不再是《红楼梦》考据、文章校注,而是房东纠纷、丢身份证、手稿被偷、牙病胃痛、眼底流血,“麻烦层出不穷”,一语成谶,精于自嘲如张爱玲,恐怕也要“骇笑两声”了。
际遇篇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1990年信中,70岁的张爱玲提起姑父李开第来信,建议她可回上海养老,雇佣人方便,她婉拒,“喜欢这里,虽然不得志,从来没懊悔过”。
寥寥数语,思之怃然,心生几分到底是张爱玲的敬畏。由1955年赴美算起,她后半生际遇绝非顺风顺水,取舍与坚持也泾渭分明。1957年,母亲黄逸梵亡于伦敦,她只字未提,1967年,简短的一句“Fred(第二任丈夫赖雅)廿四突然去世,详情下次再讲”,便没了下文,1981年,她说“同时收到7千美元(版税)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1991年姑姑张茂渊病故,也是淡淡的“我前一向一直无缘无故低气压,也是一种预感”点到即止,甚至被宋淇不客气地提醒,姑父对姑姑真心真意,“虽然可能另有other motive,即你的著作版权费”。

张爱玲的作品《传奇》。
知交零落,已道是寻常,倒是信中许多陌生的熟面孔的出现,让读者大跌眼镜之余,更有恍若隔世之感。首先是琼瑶三毛,70年代在台湾大火,张爱玲自嘲,“我居然跻身于琼瑶三毛高阳之间,真‘悬’得汗毛凛凛,随时给刷下来”、“三毛写的是她自己,琼瑶总像是改编”,80年代言情风吹到大陆,她分析销量惊人在意料之中,因为欲望压抑太久,更透露桑弧曾以苏联小说为例,认为大陆会有天文数字的市场潜力,劝她留下发展,“结果实现的倒是台湾作品”;其次是几部小说的影视版权,卢燕最早有意拍《第一炉香》,自饰姑妈,李翰祥曾考虑拍《金锁记》,被邵氏否决,许鞍华导演《倾城之恋》,竟是宋淇女儿的同班同学,张艾嘉想监制《赤地之恋》电视剧自导自演,王家卫想买下《半生缘》版权,《红玫瑰与白玫瑰》有意找林青霞分饰两角,最终出演者之一陈冲,也因《末代皇帝》中的表现,获邝文美在张爱玲面前一番盛赞……
都是现在文坛影坛中,或已登上神龛,或成中流砥柱的人名,今昔交叠,用她自己1994年信中的话形容,就是“蔡楚生(《渔光曲》导演)喜欢《太太万岁》,跟从前周作人看《十八春》连载一样,使我一阵头晕,有时空混乱感”,像光影的幻术,一连串蒙太奇,万花筒般,对准张爱玲的长镜头,愈发显得似近还远,倏然急转,1995年8月9日,邝文美最后一封信,末尾一如既往的是“赶着付邮,别的话下次再讲,匆祝安康”,就此戛然而止,同年9月初,张爱玲逝世。
书不尽言吗?更多弦外之音,似乎已更竟在不言中。于是想起,最后一本书《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出版时,张爱玲曾打算取名《张爱玲面面观》,本是双关,“兼指各种facets与不同的面相”,又因“太自我膨胀,使人起反感”否决,读毕上下两卷,时光倒流又回溯,从盛年到垂暮,各种现实与虚构的人物对照,隔着迢迢时空,一个喃喃自语的张爱玲前所未有地跃然纸上,倒真真印证所谓“面面观”三个字——百年之际,虽迟未晚。
撰文丨一把青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