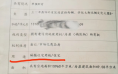撰文|孙嘉言
按照传统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史传统是“常事不书”,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日常”往往是不被史书所记录的。这就导致留存至今的历史资料大都是帝王将相的传略和重大的历史事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则往往隐匿不见。研究“日常史”的意义是什么?哪些“日常”值得被历史记录和书写?“日常史”研究是碎片化的吗?成为焦点的“日常”还是日常吗?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举办的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第三中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共同探讨了“日常史”的相关问题。
1
“日常”中的社会经济史
包伟民以其著作《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介绍了了日常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陆游生活在江南的山会平原,即今绍兴一带。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中“稻麦连作”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在学界一直颇有争议。梁庚尧、李根蟠等学者认为,稻麦复种制在当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即春季播种水稻,秋收之后再种下抗寒的冬大麦或冬小麦越冬,如此循环交替种植。曾雄生等则认为,稻麦复种制在当时并不普遍,更多是空间上的“异地而植”,高田种麦,低田种稻。
包伟民认为,陆游的诗作或者可以为这个争论提供一个案例。“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这些诗句或许可以说明,稻麦异地而植是当时较为普遍的耕作方式,麦子常种于山垄之间。而“纤纤麦被野,郁郁桑连村”、“麦苗极目无闲土,塘水平堤失旧痕”几句诗则提示我们,平原低地也并非全无麦子种植。这可以说明同一块地里的循环交替的稻麦复种制在山会平原的确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陆游的乡村世界》书封
庄绰《鸡肋编》中记载了南宋时期北民南迁、麦价飞涨的境况:“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有人以此为据,认为麦作在江南的普及是因为北方移民,当地人则不喜面食。而陆游却在诗中写道:“旋压麦糕邀父老,时分菜把饷比邻。”“村店卖荞面,人家烧豆秸。”当地还有着在新年佳节吃“年馎饦”(即面片汤)的习俗。由此可见,面食在当地民众的饮食结构中已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并且是跨越阶层的大众化的食物。
包伟民认为,江南地区人口密度的增长,对作物产量和丰富度的更高需求,才是麦作推广的核心内因。然而,“北民流寓”这样的非常态历史事件,常常比潜移默化的社会演进更能引人注目,从而使后者失载于历史文献、难以为人所知。“日常史”研究便是通过复原历史中的生活场景,如显微镜一般探寻种种历史细节,并以此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样貌。
2
复归叙事史传统
自法国年鉴学派以来,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历史“整体性”的“社会科学史学”成了史学研究的主要潮流。而1979年劳伦斯·斯通所作的《叙事史的复兴:反思一种新的传统史学》一书,则体现着“叙事史”传统作为写作样式与史学理论的逐渐复兴。
叙事史关注历史叙述过程中的个体体验,强调以普通人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向下”的历史写作。鲁西奇举例说,当我们聚焦于一个农民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其中的多重结构:在房间、院落、田地、村落、集市里的活动,构成了一组空间结构;出生、成人、结婚、生子、服役、诉讼、衰老、死亡,则是个体生命的时间结构。从展开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观测到个体与所处的制度和环境不断地发生交互作用,复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乡村社会的结构形态。鲁西奇认为,身处历史发生过程中的人往往是无意识的,历史学家则要将这种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对个体的“日常”进行结构化、群体化的梳理与阐释,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
侯旭东认为,“日常”并不等同于“普通人”,帝王将相等历史人物的日常同样值得关注。历史学家应该将他们由历史角色重新还原为“人”、从模式化和脸谱化的历史书写中解救出来。

电视剧《苍穹之昴》剧照
同为叙事导向的研究方式,“日常史”与微观史学在理念与路径上又有哪些区别?侯旭东解释说,二者都是对追求“宏大叙事”、淡化和数字化个体生命的社会科学史学的反叛,“把人重新召回历史的叙述中”。不同的是,微观史学在从个体层面切入历史后往往依然会导向宏大的主题:卡洛·金斯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叙述的是十六世纪意大利宗教统治与异端思想的冲突;沈艾娣的《梦醒子》则展现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时代,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危机。日常史则无须依附任何宏大的历史话题,可以纯粹地聚焦于“微小”个体的生命及历史侧面的细节性问题。
3
“碎片化”的历史与“焦点化”的日常?
“碎片化”是史学界常见的对日常史研究的批评。赵世瑜回应说,我们面对的历史本身就是碎片,数量有限、真真假假,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碎片按照尽可能客观的逻辑连缀起来。正如台湾历史学者陈其南教授所言:“历史学的主流做法,是从甲地找到一个翅膀,从乙地找到另一个翅膀,从丙地找到触须,从丁地找到身体,最后将它们拼揍在一起说,这就是蝴蝶。”对“碎片”的定义本身就是一种话语霸权:“宏大”的历史就是完整的而非碎片拼凑的吗?谁又有权力说探究个体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呢?
侯旭东认为,“非碎无以立通”,日常史的研究的问题在于,是孤立地看待某个历史材料,还是将其置于特定时空中具体事物相互关联的背景之下。这种关联绝不意味着攀附宏大理论,而是寻找事物的现实的联系。包伟民补充说,日常史聚焦的个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时代、特定阶层的人,其行动本身就具有历史的特征,对个人的研究也随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成为焦点的“日常”还是日常吗?赵世瑜认为,“日常”就躺在历史深处,是千百万人共享的也是个体独有的生存记忆,关注日常即是关注历史,日常绝不会因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不复成为日常。
侯旭东则认为,“日常”在目前还远远称不上是焦点,更多学者关注的还是传统问题,它代表的只是研究对象与思路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历史的更多断面、意识到历史的复杂之处,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某些宏大规律,将波澜曲折、时有断线的历史绘成一条平滑连续的直线。
撰文|孙嘉言
编辑|吕婉婷 张进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