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丨特里斯特拉姆·斯图尔特
摘编丨安也
当威斯奈尔搬到乡下,必须亲手烧烤活生生的鸡时,他的腿软了。“我劝你现在就把它勒死,”朋友彼得焦虑地说,“免得你和它变成朋友。”“我做不到啦!”威斯奈尔说道,“你看它楚楚可怜的眼睛。”这场对话是布鲁斯·罗宾逊的电影《我与长指甲》(1987)之中的一幕。
1714年,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也有此困惑。“我怀疑是否有人能第一次杀鸡就上手,而且一点也不感到歉意,”他有几分挖苦地说道,“但是人们却心安理得地享用着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牛肉、羊肉和鸡肉。”西方文明孕育出爱护动物的文化,但同时又认同人类具有宰杀、吃食动物的权利。今天,人们似乎在同情心与食欲间找到了平衡点,而寻找符合自身味蕾的生活方式也相当简单。
“素食者”(vegetarian)一词创造于19世纪40年代;1847年,“素食协会”出现了。虽然不时遭到消解或忽视,素食主义一直风起云涌。而在此之前,吃肉,作为一个公众议题,不仅关乎人类饮食选择,更关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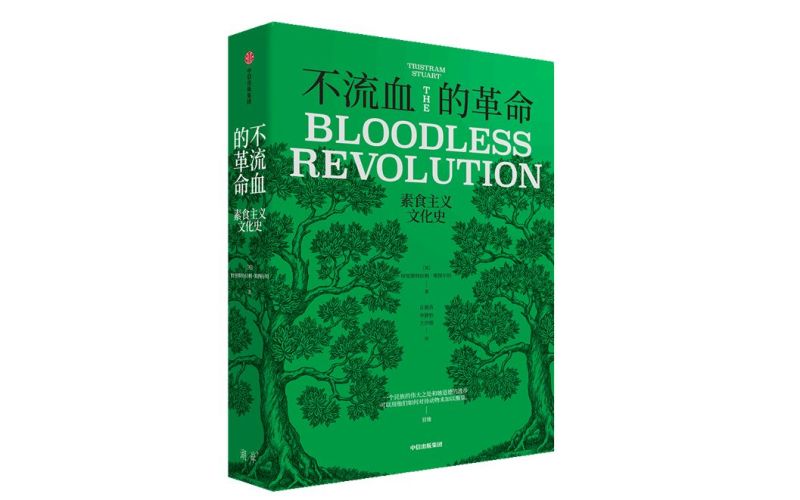 本文出处《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义文化史》,[英]特里斯特拉姆·斯图尔特著,丘德真、李静怡、王汐朋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版。
本文出处《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义文化史》,[英]特里斯特拉姆·斯图尔特著,丘德真、李静怡、王汐朋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版。
“人类该吃动物吗?”
工业革命之前,应否吃肉是最激烈的一个辩论话题,人们希望以此定位人类与自然界应有的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该吃动物吗?”这对西方文明而言是一大挑战,因为他们原以为世间的万事万物皆为人类而生。而素食者则希望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算人是造物主,”素食者问道,“有哪种上帝会吞食自己的子民呢?”
一切要从《圣经》的首章《创世记》说起。上帝创造世界后,对亚当与夏娃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创世记》1: 28)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城里,与《圣经》同样受到西方文明敬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有相同的看法:“植物为动物而生,而动物为人类而生。”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为人类狩猎本能提供了宗教与哲学上的支持。由于“一百万年前原始人即如此”,一切与当时人类不符的行为,也就得不到重新审视的机会。但是任何神殿都有罅隙,素食者们在其中埋下了撼动神殿的撬棍。
 纪录片《肉类真相》海报。
纪录片《肉类真相》海报。
人若是大地之主,那么他的统治之下究竟包括了什么?根据《圣经》记载,一开始,人类统治的,包括动物,但不包括可以宰杀它们。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的第二句话是:“看哪,我把全地一切含种子的五谷菜蔬和一切会结果子、果子里有种子的树,都赐给你们;这些都可作食物。”(《创世记》1: 29)17和18世纪的神学家由此断定亚当与夏娃只吃蔬菜和水果,而所有生物世界也都因食素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很久以后(以标准历法而言是1600年后),当大洪水摧毁大地并再次重生时,上帝改变了说法。
当挪亚从方舟上走下来时,上帝告诉他:“地上一切的走兽、天空一切的飞鸟、所有爬行在土地上的和海里一切的鱼都必怕你们,畏惧你们,它们都要交在你们手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绿色的菜蔬一样。”(《创世记》9: 2-3)1699年,学者约翰·爱德华兹对此做出乐观诠释:“自大洪水之后,你已拥有一切的自由,包括吃肉,如同你之前以植物和水果为食一般。现在,你可以吃肉。但这也说明,在大洪水之前,人们是不吃肉的。”
上帝应允人类吃肉和要求人类与动物和平共处,两者存在矛盾,素食主义者把矛盾放大表现出来。虽然《圣经》对当下社会的制约渐渐式微,但是相似价值观仍旧盛行,其深厚的脉络也贯穿于现代社会之中,不管是关于自然的辩论的正反双方哪一方,都如影随形。

纪录片《奶牛阴谋:永远不能说的秘密》海报。
17至18世纪,各个阵营持不同观点纷纷对肉食习惯展开抨击。革命家们炮轰主流文化的骄奢嗜血;人口统计学者抨击肉食浪费了贫苦人民得以生存的资源;解剖学者认为人类肠道系统无法消化吸收肉类;游历过东方的旅行者,更把印度的人与自然和平相处模式,送给惯于掠夺自然的西方世界作为借鉴。新锐人士和特立独行者也在强烈地动摇当时社会饮食的主流价值观。即便当时最进步的思想家也为此争论,这使人们重新理解了人类天性。当时,虽然极少数的欧洲人能够做到不吃肉,但是他们从底层社会了解到,即便过着大量劳作的生活,也实在无须消耗过量肉品。文化贵族们反过来影响了农业、医学与经济政策,并决定了多数人的饮食习惯。
17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间沸沸扬扬的论战,塑造了当代社会的价值观。重新审视观念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明晰现代文化的肌理,并抛弃错误的假设。早期素食主义的历史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禁欲道德观、初期医疗科学与印度哲学是如何深远而巧妙地影响了西方文明。
17世纪的人们幻想着重返和平岁月,远离血腥暴行;虽然明知不可行,无数的人仍旧抱着田园般的幻梦,亦称之为亚当与夏娃堕落前的伊甸园时代。伊甸园信仰者希望和动物们保持着原始的和睦关系。他们愿以仁慈与互助的方式管理动物,并拒绝做“野蛮暴君”。17世纪的先锋人士以此为论点,批判人类社会的剥削与暴力。
1642年,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爆发武装斗争,让全国陷入数年的殊死战中。不同政治光谱里的人士都希望从无政府状态里脱离,并寻求宛若天堂般和平的社会。保皇派分子托马斯·布谢尔遵从前辈弗朗西斯·培根的建议,设法证明原始饮食法可以带来身体长寿与精神澄明。而议会派的开明党员,力求民主改革的清教徒运动者们,则以吃素表达对主流社会奢华作风的不齿,他们更宣扬不流血的革命,建立无杀戮的平等社会。一些宗教人士也坚定地跟进,他们宣称上帝自得于万物之间,而人类亦须以爱和仁慈善待动物。

纪录片《食品公司》剧照。
另一股边缘潮流意外地带给了西方文明超凡影响。旅印欧洲人“发现”了印度古代宗教及其感人的“不杀生”原则,后者代表以非暴力的方式对待所有生命。他们勤奋研读印度与耆那教的哲学要义;他们见到前所未见的动物医院、普世素食主义,以及以博爱的方式对待低阶层生命。印度的素食主义观念冲击了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造成欧洲道德良知的危机。对很多人而言,理想主义者的幻梦已灿灿然于眼前。素食主义者跪屈双膝,呼唤古代印度哲学家引领众生脱离腐败而血腥的道德苦海。
与印度素食主义的邂逅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欧洲的先锋思想圈。日益蓬勃的旅行文学市场促成了哲学家之间的严肃论辩,并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虽然游记作者们往往取笑印度素食主义者,并认为他们的心肠过分柔弱,但许多读者认为印度文明体系包含了强健而美好的道德规范。哲学家如约翰·伊夫林、托马斯·布朗爵士与威廉·坦普尔爵士,皆认为印度素食者证明了人类能够以原始的蔬谷为食,并得到快乐富足的生活。艾萨克·牛顿阅读东方圣哲思想,并因此深信“善待野兽”正是上帝嘱咐人类的最根本的道德律则,而西方世界却早将之抛诸脑后。17世纪末期的怀疑论者以印度素食主义大举炮轰欧洲宗教与社会的正统性,认为印度人才是在奉行原始的自然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动物)。
印度素食主义动摇了《圣经》中人类是永恒统治者的思想,鼓励人们扩大道德责任的范围,并认为人类与自然都将因此受益。印度哲学特别是“不杀生”律法激起了大规模论战,并演变成现代生态学的认识危机。
笛卡儿、伽桑狄都认为素食正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的饮食
17至18世纪,是科学飞跃发展的时期。新发现和系统化的理论席卷西欧,并为受过教育的群体广泛接受。显微镜让肉眼得以观察到不为人知的世界;外科探索剖开了深藏不露的人体器官;不断发展的宇宙监测基站,其大尺度且精密的观测使人类知识抵达外太空。人类探索未知的技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使得许多新的人类种别与物种成了科学启蒙时代的研究对象,并被包含在旧称“自然哲学”的范畴内。而素食主义者也必须与时俱进,以符合当代思考系统的逻辑。素食者刻画出科学路径以描绘自身的哲学愿景,并汇入启蒙时代的大江大海之中。
伴随着解剖实验的发现,人体近似于猿类,并与许多动物无异,这使得解剖学与医学跃然成为哲学辩论的主战场。人类和动物很像,但是科学家还想知道人类更像哪种动物:草食的还是肉食的?知识界绝大多数意见认为,从人体生理构造来看,人类应为草食动物,并以此对应《圣经》中人类原本以蔬谷为食的说法。
 纪录片《食品公司》剧照。
纪录片《食品公司》剧照。
科学热延续了整个18世纪,而其启蒙思潮源自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派别,勒内·笛卡儿以及同样强劲的对手皮埃尔·伽桑狄。笛卡儿与伽桑狄以不同架构的理论追问最关键的问题:人类与自然、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灵魂本质。出人意料的是,不管是笛卡儿还是伽桑狄,都认为素食正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的饮食。
17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包括笛卡儿、伽桑狄与弗朗西斯·培根都提倡素食主义。当时素食主义受到的关注度,至今尚未能超越,那时素食主义得到知识界的积极支持。到了18世纪初,他们的进步思想已然形成新一波的科学素食主义运动。
解剖学家发现人类牙齿与肠胃结构更近似于草食性动物,而非肉食性动物。营养师认为人类的消化系统无法分解肉类,且肉类容易造成血管堵塞;反观蔬菜,则可以轻易地被人类的消化系统分解成极富营养价值的流体物质。神经学家发现动物神经系统具有感受痛楚的能力,这一点和人类一样,这个发现使得信奉同情心道德原则的人们感到坐立难安。同时,对印度人的研究发现,素食者拥有更健康而长寿的生活。上述科学发现使素食主义不再只是进步的政治宣言,而转型成为有可靠依据的医学观念。当时,欧洲的医学院普遍认定素食乃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这种风潮差不多成了医学正统典范。
欧洲各地出现了素食医生的身影,他们将医疗辩论转变成一张张的处方笺,嘱咐病人吃素,期望以此消除肉食过度所造成的病痛。素食医生成了社会名流,和今天的营养师一样风光,但同时他们也是早期医疗研究的重要推动者。曾经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认为,肉类乃是最营养的食物来源,特别是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对英国人而言,牛肉甚至成了他们的国族形象标志。而且很多人仍旧相信蔬菜会带来不必要的胀气,并会让消化系统产生不适感。然而素食者推翻了这样的刻板印象,证明了蔬菜富含营养成分,而肉类不但不必要,甚至很有可能危害健康。素食者推动形成了今日均衡饮食的观念,并强调了肉类的害处,特别是暴食肉类的可怕后果。
 《餐叉胜于手术刀》剧照。
《餐叉胜于手术刀》剧照。
人们开始相信素食比肉食更健康,并以此反推认为人类本该是草食动物,而非嗜血生物,杀戮动物根本违反自然法则。重新审视自然法则更让欧洲人思索《圣经》的内涵以及上帝造物的原理。新的科学观察呼应旧时代神学家的说法,认为人类饮食原本不包含肉类,而残忍地对待动物更是摧毁自然秩序的人类社会暴行之一。
上述结论起因于17 世纪晚期欧洲社会视同情心为基本的道德哲学标准,并由此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推力之一。现代的“同情心”等同于昔日的“悲悯心”,并为旧有的“共情”概念提供了科学解释。素食主义者托马斯· 特赖恩对此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认为人类身体如同磁铁一样,能够对所有相似的生命产生神秘的“对应”。
笛卡儿派解释,如果你目睹他人手臂折伤,“动物灵气”将自然传送到你的手臂,让你产生痛楚的感觉。虽然笛卡儿派认为不该为动物感到哀伤,但不难推论,如果人类具有同情动物的本能,那么杀害动物即是违反天性。素食者整合了“科学”、“道德”与“宗教”之间的逻辑,并努力让大家承认吃肉会有损道德高度。虽然很多人从来不去想这些事,但是素食者坚持,如果欧洲可怕的农业系统是建立在宰杀动物的基础上,那么全世界人民都将遭到剥削与残害。
反素食主义阵营迅速集结动员,否认上述指控,并为食肉展开辩护大反攻。辩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这也显示出素食主义已成为普及的概念,而人类确实深受挑战。素食主义威胁到人类长期以来的宇宙主导地位,更糟的是,它还剥夺了人们在礼拜天畅快吃烤牛肉和大餐的权利。

《餐叉胜于手术刀》剧照。
许多医学界名家肯定素食主义的革新观念,认为应该少吃肉类、多吃蔬谷,但是,他们又急切地宣称人类的身体构造更与肉食动物或杂食动物相似,绝非草食性,只吃蔬菜恐怕会造成营养不良。他们还指出,许多哲学家、小说家与诗人坚持同情动物是一件好事,但若变成素食者就太夸张了。
然而,许多声名显赫的文化精英坚持素食主义的理念,以饮食革命作为核心观点,发动了重返自然的运动。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认同切恩医生的理想,将素食概念写进小说《帕梅拉》与《克拉丽莎》中。卢梭认同解剖学概念,将人类本能的同情心转化成动物权利的哲学基础,并孕育出整个世纪的卢梭素食主义学派。经济学者亚当·斯密认识到肉食的奢靡之过,此后也在自己的自由市场理论的税收篇里添加了相关想法。18世纪末期,医学院教授、道德哲学家、抒情作家与政治行动者们齐力推动素食主义。素食主义成了反对旧文化的批判武器,同时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素食主义史似乎预示了近年来学者的质疑:非理性的宗教狂热信徒与启蒙自然科学家是否有对立的必要。17、18世纪,政治与宗教人士围坐在公社的餐桌周边生食蔬菜,而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则端坐圆桌前,用银晃晃的餐具切食蔬谷。
当人口膨胀数目超过食物生产极限,饥荒就会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全欧洲弥漫着一种追求革新的气氛,浪漫主义运动云涌风起。新一批的欧洲东方主义者游历印度,并将印度教奉为崇拜对象,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印度文,并将梵文翻译给欣喜若狂的欧洲读者们。许多东印度公司雇员受到印度慈悲文化的感召而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全力拥戴印度教,并视之为更人道的选择。进步的基督教批评者如伏尔泰持如此想法,并以历史悠久的印度典籍作为严厉抨击《圣经》的依据,认为印度对待动物的良善之心,使欧洲殖民者的贪婪更显龌龊。就连恪守自身基督教徒身份的知名学者威廉·琼斯爵士都深深为“不杀生”原则所倾心,并视之为18世纪医生与哲学家的理想缩影。
18世纪80年代,当政治思想逐渐酝酿成大革命风暴时,素食主义再一次进入启蒙版图。追求普世同情心与平等概念的印度教,与民主政治和动物权概念不谋而合。从印度返国的革命党人约翰·奥斯瓦尔德心中燃着熊熊怒火,他指责人类社会的不正义的暴力,却发起法国大革命中最为血腥的武装行动。而其他人则将卢梭的重返自然运动进一步发扬光大,甚至为了坚持信念而被推上了断头台。诗人雪莱加入积极推动社会改革的裸体主义者团体,他们将自己的理念融入素食诗文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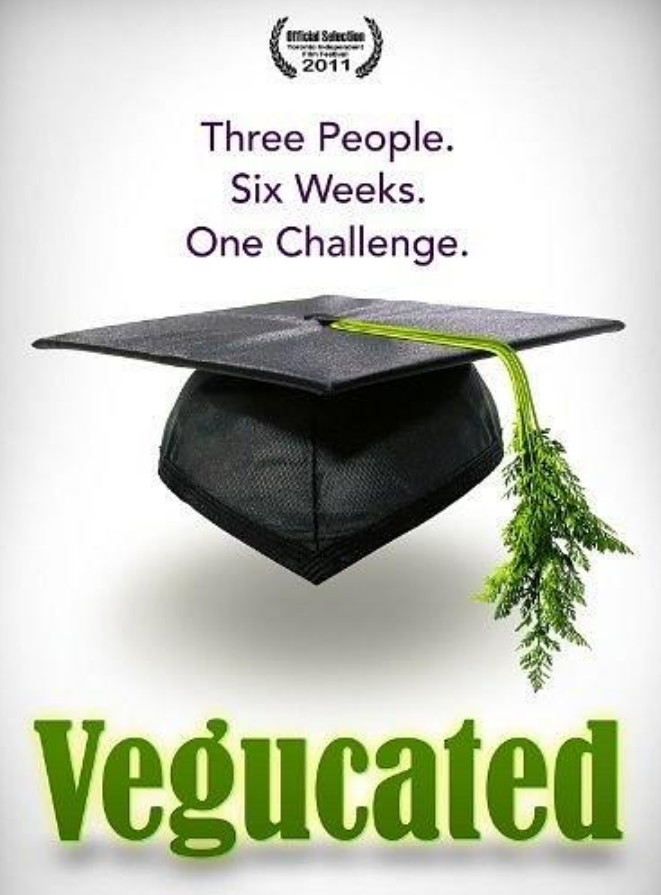
纪录片《接受蔬食教育》剧照。
当无神论者的势力越发庞大时,欧洲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随之萧条,人们不得不承认人与动物之间的有机关联,而此前的想法是错误的。遥想乌托邦的改革人士仍旧幻想一个和谐共处的世界,虽然他们明白伊甸园不过是个迷思传说,但是他们仍将犹太–基督教体系当成人类学的底色,并往前迈进,追求更为精进的人道主义与环境保护思想。
当欧洲社会面临环境衰竭与人口过度饱和的危机时,经济学者们开始着手解决自然资源有限的问题。许多人了解到制造肉食产品是多么缺乏效率:喂给动物的粮食,90%都转化成了动物的粪便。
功利主义者认为,土地若种植蔬菜,将比作为畜牧肉场更能满足膨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而拥有广大人口偏好素食的国家如印度与中国,再一次成为经济农业形态的典范。而此说法最终使托马斯·马尔萨斯做出结论:当人口膨胀数目超过食物生产的极限时,饥荒就会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时至19世纪,素食主义的哲学、医疗与经济论述已日臻成熟,并时时刻刻让欧洲社会主流文化感到芒刺在背。虽然19至20世纪时期的素食主义有所转变,但其脉络深远,以至于对今日产生了深远影响。阿道夫·希特勒、圣雄甘地、列夫·托尔斯泰等个性迥异的人物纷纷将素食主义转化成新的政治概念,并与印度道德观遥相呼应。
当我们研究数百年来人们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当时的情境,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判断对错,唯有这样,才能反思我们当今社会的观念。而本质上,人类社会是健忘的。早期素食主义者精彩而被忽略的人生,总是被随意地散落在历史篇章间。他们塑造了今日的你,塑造了你思考自然的方式,以及你为什么老是被提醒要多吃蔬菜、少吃肉。
本文选自《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义文化史》引言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特里斯特拉姆·斯图尔特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宫照华
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