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毫无意外地将成为今年年末最火的流行词之一,虽然当下的语言更迭过快,新词语的出现未见得反映着一种新的情绪,但这个词多少还是真实表达了一些职场人心中的苦衷。那么,既然给老板打工如此悲催,给自己打工,总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答案可能依然是:未必。
在许多企业话语的包装下,“给自己打工”这句话,不仅可以指向创业者,还可以指向另一群人:“零工经济”劳动者。
前些时日,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也曾引发公众对快递员群体处境的热烈讨论,其中一个被重点讨论的议题正是有关“零工经济”高度发展的利弊。快递员群体的构成中,除了与美团等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自营骑手外,还存在大量代理商骑手、众包骑手等,他们从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平台旗下公司的员工,劳动权益常常无法得到保障——而这正是“零工经济”的特征之一。
不仅仅在外卖行业,从网约车到家政工,从电话客服到网络写手,“零工经济”的劳动形式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在全球范围内,“零工经济”的崛起和扩张也已成为重要的现象。这类工作看上去往往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弹性特征,劳动者名义上能够自由地选择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并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量和收入情况,多劳多得。但同时,他们往往因为并未与企业签订带有完整劳动保障的合约,因而时刻面临着各类劳动风险。
2016年,英国专栏作家、记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开着一辆破老爷车离开了大都市伦敦,前往体验一种他平日里“看不见”的生活。他开始了一项为期180天的针对“零工经济”的参与式调查。在调查期间,他去到英国的一些偏僻的小镇,亲身参与亚马逊仓库的拣货员、小镇家庭护工、电话客服等不同行业的工作,近距离观察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的生存境遇。
布拉德沃斯将自己的调查经历写在了《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一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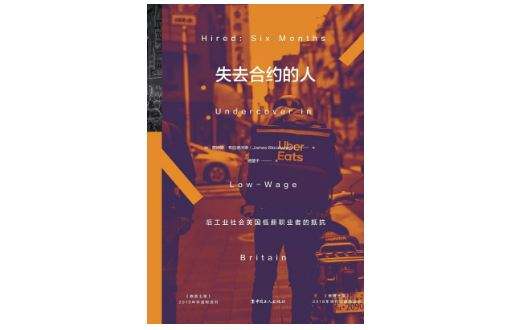
《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 [英]詹姆斯·布拉德沃斯著,杨璧千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8月。
在与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的交谈中,布拉德沃斯提及,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出任何“解决之道”,而是希望吸引读者关注特定的议题,并让大众看到更多零工经济下低薪劳动者的处境。他也并不想写出“枯燥的大部头”,对“有关贫穷、劳动等大问题”做出回应——这可能刚好符合很多读者读完全书的体验。
撰文 | 刘亚光
客观上看,《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并不算一部非常出色的调查作品,虽然作者在记述经历的过程中时常会引用一些学术名词和文献,也会略微提到“平台资本主义”等学术话题,但他并无意提炼出任何具有理论性意义的问题。而180天的调查时间,也并不能够让作者对于整个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做出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判断。
不过,布拉德沃斯的记述依然具有其独特的亮点。他从调查中揭示出为“零工经济”的“自由”话语所遮蔽的阶级差异:大量选择进入“零工经济”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被迫选择这样的劳动形式,通过超负荷的劳动换取着微薄而不稳定的薪酬。同时,布拉德沃斯也记录了许多与劳动者们的直接对话。这些对话的细节中流动着的隐秘情绪,显示出“零工经济”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它同样塑造着一种文化和社会观念。布拉德沃斯表示,零工经济的文化影响是自己关注的一大重点,这同样也是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詹姆斯·布拉德沃斯(James Bloodworth),英国作家和记者,为《国际财经时报》(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撰写每周专栏,文章常见于《卫报》、《纽约书评》。著有《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精英主义的迷思》。
零工经济的兴起:“自由”的悖论
在一篇名为《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的文章中,加拿大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讨论了零工经济的全球增长问题。据他引用的文献显示,现在有400万美国人就业于零工经济之中,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预计将超过900万。2019年,德勤发布的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中预测,2020年美国个体经营者的数量预计将增加两倍。而在欧盟,自由职业者同样是当今增长速度最快的劳工群体。
许多研究者指出,“零工经济”的崛起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削减公共福利、放松市场管制,跨国公司被鼓励不断寻找实现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生产盈利模式,而雇佣关系的灵活性往往能帮助企业应对日益不确定的商业环境。通过废除长期、固定的合同,代之以更多雇佣临时工,企业可以摆脱一系列在传统雇佣关系中需要承担的成本。同时,亚马逊等跨国企业通常将核心资源集中于研发部门,而将基础劳动外包到国外,“零工经济”的兴起也迎合了当下这类跨国资本布局全球产业链的需要。

纪录片《美国工厂》(2019)剧照。
当然,亦有学者指出,“零工经济”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比如,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我们从很早开始就有“打零工”的说法。许多人认为“零工经济”的一大新的特点是与技术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有学者就将零工经济定义为以各种在线平台为中介的灵活工作的集合。布拉德沃斯在接受采访中也谈到,“零工经济”与“打零工”的一大差异是其中的技术因素,他称:“‘零工经济’的兴起与各类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们为远程工作提供了便利,也更方便企业和平台对劳动者的劳动状况进行监督”。发达的网络、普及的智能手机使得平台可以远程招募劳动力,并运用大数据算法准确匹配劳动者和服务需求方,极大地便利了“零工经济”形式的全球扩张。同时,技术也推动着劳动者监控的升级。在布拉德沃斯卧底调查的英国鲁吉利镇亚马逊仓库中,每一个工人手里都有一个手持装置,“虽然没有一名有血有肉的真人主管,但工人们的一举一动其实尽在掌握”。
这是一幅极不“自由”的劳动图景——虽然“自由”一直是零工经济常常自我标榜的话语。“从和我采访对象的交流中我发现,零工经济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所许诺的‘灵活性’”布拉德沃斯说。2019年,劳动力管理调度软件企业ShiRboard的一项针对2000名企业雇员的调查显示了类似的结果:约49%的被调查对象都愿意合理降低薪酬来换取弹性工作制,因为这样可以实现“更自如的工作日程控制”。在布拉德沃斯调研的伦敦优步司机中,持有这类看法的人同样不在少数,然而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发现了困扰之所在:在平台算法的劳动控制下,“自由”往往无法落到实处。

纪录片《美国工厂》(2019)剧照。
与外卖骑手同样,布拉德沃斯记录的优步司机常常也面临着“困在系统”里的窘境。在派单算法的设计中,优步常常利用心理学的专业研究成果对驾驶员进行引导。《纽约时报》2017年就曾报道,为了刺激驾驶员出门工作,优步往往利用人们的偏好设定派单时的目标倾向,让司机在想要拒绝接单时提醒他们距离目标近在咫尺。“零工经济会许诺劳动者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和灵活性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在Uber工作的人,如果您不想在某一天工作,您当然可以选择关闭手机——但这恰恰就是自由与灵活性终结的地方。在零工经济中,实际上你除了拒绝掉所有的工作之外,你没办法‘自由’地选择哪些工作是自己想做的。一旦打开手机,接入平台,劳动者就必须接受公司派遣给我们的所有工作——即使这些工作的派遣往往是由系统设定而不一定符合劳动者自己的意愿或者利益”。
在鲁吉利的亚马逊仓库,布拉德沃斯结识了同为拣货员的克里斯——一名在英国工作的罗马尼亚人。尽管工作繁重且不稳定,他依然愿意选择留在这里签订零工合同而不愿意回到家乡,因为“我在这里谁也不是,但回到罗马尼亚,不仅谁也不是,连吃饭也吃不起”。当听闻他是“自愿”来这个亚马逊仓库工作时,克里斯一脸震惊地说:“你为何做这份破工作?你怎么不做别的?你真的是英国人?”这种惊讶的反应其实恰好体现出在零工经济所许诺的“自由”背后另一种更为深层的“不自由”——大量零工经济的从业者往往生存艰难,且选择这份职业并非出于自愿。

图源/medium.com
这同样与零工经济和科技之间的关系有关。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类似“某某职业未来将有一半的岗位被机器人取代”的预言层出不穷。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素质人才能够留在研发部门,但大量拥有基础技能的劳动者失业的增加使得他们只能选择签署非固定合约的零工经济市场。布拉德沃斯观察到,英国的“中层工作”正在萎缩,工作的两极分化正在悄然发生。1996-2008年期间,英国每10个消失的中等需求工作中,就有4.5个是被高技术需求的工作取代,另外5.5个被更低技术需求的工作取代。《哈佛商业评论》写于今年的一篇行业观察同样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劳动力市场正逐步变得越来越两极化,相对于入门级、低技能工作和需要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作,中等技能工作正在受到侵蚀。而新冠疫情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就零工经济劳动者来说,作为一名衣食无忧、也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城市中产阶级,业余时间开开网约车,和作为一名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完全依赖打零工生存的低薪劳动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而后者往往已经是既有的社会弱势群体——低技能劳动者、语言不通的外来移民等,他们只能选择薪水微薄的工作,并同时承担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缺失的风险。相关研究指出,对大多数零工者而言,他们的收入普遍低于同龄人,收入来源的不稳定往往意味着他们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从事多种副业,或在非正式工作时间工作。这不仅让他们更加辛苦,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样化的劳动风险。

盖伊·斯坦丁《不稳定无产阶级》,2019年6月。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认为,与零工经济相伴随的将是一个全球“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诞生,他将其界定为介于菁英白领上班族、专业人士、传统技术劳工与工匠阶级之间的一个欠缺发展潜力(truncated)地位的阶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阶级的不稳定感除了来自工作保障的缺失,有时还来自身份的尴尬。新自由主义的强化使得劳动力流动越来越便利,如布拉德沃斯所见到的英国亚马逊仓库中的罗马尼亚劳工无法取得本地的公民身份,无法享有政治权利,他们语言使用上的困难也常常成为捍卫自身权益道路上的阻碍。尽管斯坦丁将这一群体视作独立的阶级在学界引来诸多批评,但他观察到的现象却值得重视。零工经济描绘的蓝图是“自由选择合约的人”,但现实中,选择零工经济的人可能恰恰是“失去合约的人”。
原子化与精英主义:作为文化的零工经济
在刚刚到达小镇鲁吉利时,布拉德沃斯就记录下了小镇上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到鲁吉利,第一眼就能看到橱窗上显眼的红色私家侦探大型广告赫然张贴着:伴侣不老实?欢迎和我们洽谈追踪服务。这家商店也帮忙推销测谎仪生意。在这里,忠实与诚实已经逐渐被腐蚀,由暂时性和市场导向原则取而代之。保证人能够立即获得满足,甩了一个男女朋友还可以再换”。
他认为,这正是零工经济的发展给小镇氛围带来变化的一个缩影。在旧的煤炭工业衰退后,亚马逊进驻,大量的煤炭工人转型成为与亚马逊签下无保障合约的仓库拣货员。在煤炭时期,工厂提供的工作十分有保障,更重要的是,一个工厂往往还能为工人们提供一个“社群”,他们相互熟识,从彼此身上获得情感上的慰藉。如今,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安全网”,随着工作的零工化一同破碎了。感情易逝、忠诚难得,不安定感开始弥漫在小镇中。“我看到以前用于社交活动的酒吧和各类俱乐部陆续关闭,当地教堂里的长椅长期空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公共空间。而在政治上,工党就越来越不选择扎根于鲁吉利之类的城镇”。布拉德沃斯认为,这种新的工作状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疏离,使得社会变得“原子化”。

员工抗议亚马逊。图源/businessinsider.com
这种“原子化”的文化正弥散在各个零工经济的工种中。如果平时你经常坐出租车,你一定会常常为各个城市中出租车司机们的“博学”而惊叹。出租车司机往往热衷于用嬉笑怒骂的口吻,和乘客讨论时事热点话题、地方八卦,不得不承认,有时这确实是我们枯燥乘车过程中的快乐源泉。但在布拉德沃斯的观察中,伦敦的优步司机对和乘客谈论宗教、政治、体育等容易发生观点分歧的话题十分谨慎,他们彬彬有礼,不随意打扰顾客,力图保证好平台要求的“标准化服务质量”。同时,传统的出租车司机使用对讲机和同行们插科打诨的场景也不再能够在网约车司机身上看到。2018年,有研究者就通过对滴滴网约车司机的深度访谈,发现算法与智能手机严格限制着司机的行车路线和接单选择,司机也常常因此发生与乘客的争执,同时他们与家人、客人和同行的联系也遭到削弱。
在离开鲁吉利后,布拉德沃斯前往了黑潭小镇(Blackpool),参与当地的居家照护员工作。在2016年,英国的成人照护行业中,有约四分之一是签订的零工式合约。由于家庭照护的对象常常是儿女由于工作无暇照看的老人,这一工作所包含的劳动不仅是体力上的,更是情感上的,然而工作的零工化阻碍了情感劳动的顺利进行。零工照护员培训上岗的流程简易得令布拉德沃斯感到惊讶:“我们匆匆学到清理和更换导尿管的方法,避免沾到尿液的诀窍,同时也学习如何照护对象服药。由于我们通过手机接收订单,而平台对于每天订单的派发有着严格的规划,我们在每一家的停留时间有限,与老人们的情感沟通实在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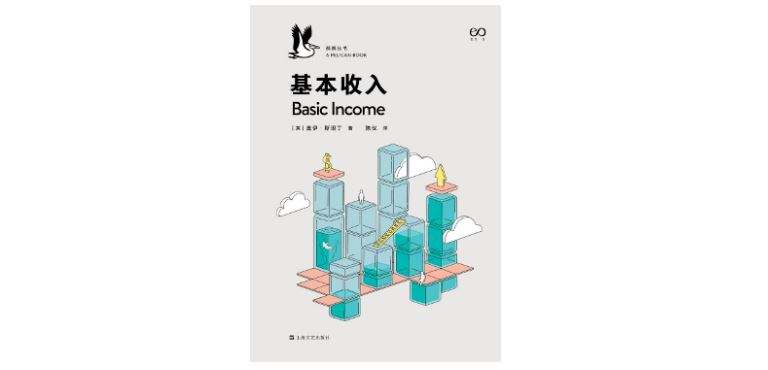
《基本收入》,[英]盖伊·斯坦丁著,陈仪译,企鹅图书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
斯坦丁对这种文化同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虽然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很多从事着低薪、低技能的工作,但拥有稳定合同的低薪、低技能工作并不意味着一定拥有强烈的不稳定感。然而零工化的该类工作却会令不稳定无产阶级无法产生稳定的工作认同感,没有自身社会记忆的传承,这种缺乏生活“锚定点”的状态使得“愤怒、脱序、焦虑、异化”成为这一群体的主流情绪。更值得担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原本恰恰来自于共同的不幸处境,可技术的区隔使得全球范围内的零工经济劳动者很难形成寻求共情的共同体。斯坦丁援引美国政治学者乔纳森·海特的分析,指出长期处于不稳定感中又缺乏支持的个人,容易对生活抱有投机的态度,游走在道德的灰色地带,成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因素(斯坦丁亦指出不稳定无产阶级会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温床,但此观点也受到来自学界的各类质疑)。
“原子化”的人际关系不仅体现在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之间,也体现在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技术相关。在《人物》有关外卖骑手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算法的设计常常以消费者的便利为优先。类似的状况同样发生在布拉德沃斯的调研中——毕竟,我们使用零工经济提供的服务,只需通过手指在屏幕上的简单滑动,“我们不必知道这些商品从生产到运到我们手中的过程里所包含的劳动,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大”,他随后也表示,另一个蓬勃发展的科技形式——社交媒体的发展,也在威胁着这种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共情,“社交媒体会构造许多‘同温层’,我们看到的都是和我们的处境一样的人的生活:衣食无忧、事业有成,这有时让人们变得自欺欺人,以为‘政治’完全是在线上发生的一样。直到我真正走出同温层,处在与他们相同的环境,只能用浸湿的纸箱裹着身子保暖,承受着上百万种陌生又不愉快的感官体验,我才被迫抛弃那些刻板印象”。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2020)剧照。
如何缓解零工经济下低薪劳动者的困局?
从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们的分析来看,这是一个复杂而宏大的问题。在《不稳定无产阶级》一书中,斯坦丁从经济的维度提出了包括创建一套国际认证系统以认证跨国劳工身份、推进教育改革以让低技能劳工获得更多发展自身的能力等措施。而在另一本作品《基本收入》中,他也系统论述了定期无条件付给个人一笔适当数额金钱,以保障其基本安全感的方案。相对于方案本身的解决力,更重要的是他论证此方案的理由。在斯坦丁看来,“基本收入”的方案的正当性并不是一种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正当性,而是一种社会伦理与文化上的正当性。推行基本收入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它有助于从长期上稳定经济秩序,而是希望重新塑造一种强调社会互助的正义观念,并将安全感视为社会伦理的关键目标。
在接受本报采访的过程中,布拉德沃斯也认为“基本收入”方案是一项帮助零工经济中低薪劳动者的可行举措,但他同样将关切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文化和观念上。在《失去合约的人》全书的后记中他写道:“我认为,本书描述的许多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精英主义’的信条广为接受,许多人相信应由能力卓越的少数人来管理社会。一种普遍通行于世的择优录取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保守思想的实践,它希望运用科学方法来剥削他人,坚信人类因其价值而归类于阶级中的位置,且阶级永世不变——精英在最上层,概念上可归为无产阶级的一群人,则落入最底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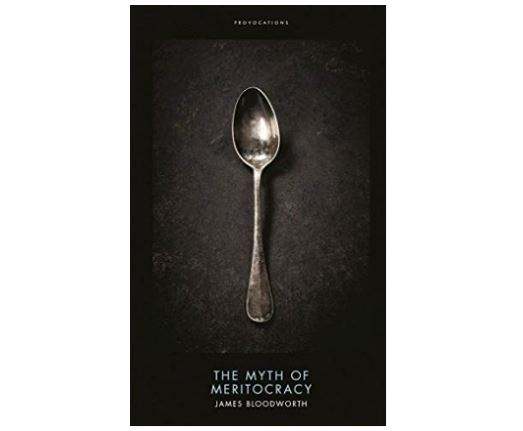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James Bloodworth, Biteback Publishing, 2017.
布拉德沃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将零工经济与“精英主义”(Meritocracy)观念的盛行这一文化现象勾连了起来。今年9月,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出版了新书《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也译作“贤能的暴政”或“精英的暴政”),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桑德尔认为特朗普的崛起背后隐藏着人们对精英主义的强烈不满。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个体自治”的神话不断推动人们将“自我造就”视作成功的唯一基础。“努力就能成功”这类“上升修辞”忽视了不同人群起点上的不平等和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让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们不仅享有物质上的富足,还能获得道德上的优越。而因为种种不幸跌落底层的劳动者则同时还需承担情感上的羞耻感——因为成功仅仅关乎“个人努力”。
对前述斯坦丁提出的“基本收入”的反对意见也可以说明这类观念的流行,许多批评观点认为,穷人天然在道德上有瑕疵,他们领取基本收入之后,无法真正“聪明地去消费”,然而一些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斯坦丁给出的多项研究结果显示,由于领取到基本收入,领取人原本用来缓解不安和绝望情绪的毒品、香烟和酒精等等的消费比例显著降低了。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的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曾畅想在2033年,英国社会整体奉行“智商+努力”的优绩主义信条,使得阶层分化严重,最终濒临革命。无独有偶,写作《失去合约的人》一年后,布拉德沃斯于2017年出版了一本新的作品《精英主义的迷思》(The Myth of Meritocracy),也分析了迈克尔·杨的预言。他认为,如果整个社会正处于对类似的精英主义信条的“痴迷”状态,显然是不正常的:“精英眼中的世界,就如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轮盘赌’,在这种视角下,生活不是一种历史的积累,而是‘每一刻都独立于上一刻’,世界没有惯性、没有遗传、没有积累,任何人都能在任何一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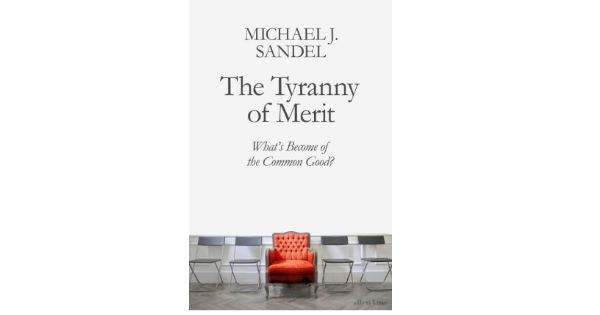
The Tyranny of Merit, Michael Sandel, Penguin Books, 2020.9.
“有许多人给我的《失去合约的人》留言,他们都认为在亚马逊打零工的这些工人们不配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如果他们希望获得一份更加体面的工作,就‘应该在学校里更努力的学习’”,布拉德沃斯讲道。在精英主义流行的现况下,桑德尔呼吁塑造一种全新的公民德性,精英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应当保持必要的“耻感”,对他人怀有一种谦卑与共情。同时,需要重构精英主义的预设,放弃粗暴地将人划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二分法,并能够更多地从“回报”与“薪酬”之外的维度衡量工作的价值。
无论如何,对零工经济与精英主义之间关系的提出让我们意识到,对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困境的解决,政策上的支持十分重要,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看似无形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失去合约的人》的末尾,布拉德沃斯写道:“自由市场的法则并不能让人们都安全无虞。如果自由真的有意义,那必定是指所有人都能生活得有尊严,而非让日渐壮大的消费阶级来指挥另一阶级。”对“自由”观念的重新反思,对“优绩至上”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理念的想象,对劳动之于社会价值的再理解,应当成为每一个人持久思索的命题——这并非仅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零工经济中的低薪劳动者所经历的,即使我们比他们幸运,但在某个特定的场域内我们总有可能是那个缺乏先天“禀赋”的弱者,一个过于尊崇丛林法则的文化终将制造一个困住每一个人的系统。
参考资料:
https://hbr.org/2020/10/algorithms-are-making-economic-inequality-worse?ab=at_articlepage_relatedarticles_horizontal_slot2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8/11/21/the-gig-economy-and-skills-traps-in-indonesia.html
迈克尔·桑德尔:不扭转精英的暴政,民主党仍会面临失败,法意读书。https://mp.weixin.qq.com/s/xH7ZFfKprS7d0Nh8JWXrpg
杨滨伊,孟泉:多样选择与灵活的两面性:零工经济研究中的争论与悖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3)。
胡杨涓,叶韦明:移动社会中的网约车-深圳市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间、空间与社会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47)
作者 | 刘亚光
编辑 | 王青 罗东
校对 |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