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颐
“在暮色中,他们穿过了该死的塔杜萨克、魁北克和三河城。近破晓时分,停泊在一个荒僻的河岸村落。”这是美国作家安妮·普鲁长篇小说《树民》的开头。
好的小说,起笔就会让人觉得隐隐不安,某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譬如,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是这样。也譬如,几年前,阅读安妮·普鲁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时,心旌摇动的感受。

安妮·普鲁(1935—),小说家。出生于康涅狄格州。自八十年代末开始,陆续创作了《心灵之歌及其他小说》《明信片》《船讯》《手风琴罪行录》《近距离:怀俄明故事》等作品。获得了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如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和薇拉文学奖等。
1. 《树民》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恩尼斯·德尔马尔五点未到即清醒,强风摇撼房车,从铝门窗四周嘶嘶蹿入。悬挂在铁钉上的几件衬衫在缝隙风中微微颤抖。” 这是《近距离:怀俄明故事》最后一篇《断背山》的开头。我想,很多人都是和我一样,从《断背山》开始接触安妮·普鲁,从此陷入普鲁打造的荒原、山脉、牧人、森林所组成的北美旧世界。凛冽的风声,沉默的守望,无言的惋叹。
短篇小说紧凑,情节推动迅速。长篇小说多了充足的余裕,可配以大量的情节副线、离题漫谈或其他描写,主干道沿着既定的方向从容前行。长篇小说让读者欲罢不能的奥秘,通常在于一件事引爆另一件事,故事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推动力。
《树民》这样跨越数百年、巨幅宏作的家族传奇,在构思时,就必须确立主题,以避免情节设置造作刻意而显得不够真实,或者像烂片儿一样愚蠢不合逻辑。那么,《树民》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如题所示,树与人,或者说,自然与人。人与树、人与人,如何相依相傍,如何分离飘零,那些失去的与尚且遗留的难以表述的我们的情感与追索。
在那两句时间、地点及其隐藏的信息与表露的文字风格之后,出场的第一个人物,叫勒内·塞尔,他就是这部小说里塞尔家族谱系的源头,一个法国贫困移民家庭的第二代。接着,夏尔·迪凯出场,来自巴黎贫民窟的穷困佣工,是这部小说里杜克家族谱系的源头。勒内·塞尔与夏尔·迪凯都为木材商人特埃帕尼先生工作。
两个年轻人性格截然不同,勒内老实,而夏尔显然有很多超乎自身社会地位的想法。勒内娶了特埃帕尼先生安排给他的米克马克女人,而夏尔从特埃帕尼先生那儿逃走了,在丛林里经历九死一生,然后被一个法国毛皮商团所救,从此混进了生意人的行列。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将沿着不同的轨道走着不同的人生,在将来于某个点上悄然交集,汇合再分开。

《树民》,作者:安妮·普鲁,译者:陈恒,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2.印第安文化如何塑造了美利坚文化?
这部小说没有严格意义的主角,呈现的是家族群像,后代繁衍后代,活着,死亡。新的生命诞生,如此往复。一茬茬树苗,有些长得高,长成了大树,有些中途夭折,有些材质好,有些是庸品,有些生长顺畅,有些遭遇天灾人祸。故事开始于1693年,结束于2013年,十个部分以时间为轴,互有交叉接续,在人物行动效应及事件的连贯上更加自然,20世纪与21世纪的内容轻掠束笔,毕竟,当代的生活来自于往昔,曾经发生的才是根源。
勒内和夏尔都是法国人,可是,为什么说这部小说刻画的是印第安族群记忆呢?
勒内娶了玛希为妻,玛希是一个比他年纪大得多的、很有智慧、对自然了如指掌、懂点神秘巫术的印第安女人,也就是说,玛希事实上是勒内的指引人,是塞尔家族记忆传承的真正缔造者。对于最让人出乎意料的问题,玛希都能给出答案,因为米克马克人已经世世代代以无边无际的想象力洞察了世界。勒内在经年累月的相处中从玛希身上学习。在玛希看来,森林是一个活着的实体,每个人应带着感恩之心与森林和谐地共同生活,无休止地砍伐所有的树是不好的。勒内觉得那只是妇人之仁,森林就在那儿,广袤而无止境,男人的任务就是驯服它。对待森林与自然的两种观念此消彼长,正是整部小说的内核。
在美国的思想文化渊源的探寻和考究里,人们往往追溯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们带来的欧洲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还有一个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天美国社会的基础,那就是美洲的土著文化,即印第安文化。
美洲印第安文化的中心观点之一就是认为自然是灵性的存在,它们有自己的意识,土地创造、养育了人类,土地联结了所有的族人,植根在土地之上的大树就是植物的万神殿,大树的年轮里记载着在时间里发生过的所有痕迹。一方面,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企业家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砍伐森林,另一方面,美国在自然文学书写和环保运动方面又是自觉的先行者,巨木森林被视为美利坚的天赐之物,林肯政府时期就颁布过森林保护的有关法案。《树民》最深层的内涵就是探讨印第安文化如何塑造了美利坚文化,在塞尔家族这条线上是这样的,在杜克家族这条线上同样如此,两条线时而分开,时而交合,最后殊途同归。
夏尔·迪凯改名查尔斯·杜克,投身木材行业,娶了富商之女科涅莉亚,他们生了一些儿女,并且收养了三个男孩子。除了早夭者之外,这些孩子都参与了“杜克父子公司”的经营。夏尔的亲生儿子奥特赫与不知名的帕萨马克迪族女人生下了碧娅特立克丝,碧娅特立克丝与离家出走的塞尔家族的后裔昆陶组成了家庭,从而延续了塞尔家族的血脉,他们的后代脱离了杜克家族的谱系,回归了米克马克人的生活方式。夏尔的养子之一,扬的后代成为杜克父子公司的继承者,在很久以后,坐在财富宝座上的人会意识到,所拥有的一切是取自另外的更有资格的人,只不过,时间湮埋了证据。
情节的这般安排表露了作者的用心。《树民》里有很多无须仔细回味就能察觉的隐喻。杜克帝国的扩张是一次悄然发生的代替,它指向了美利坚文化的“养子”是如何取代了原来拥有这片土地的“亲子”的过程。在印第安人看来,人类和土地一体,土地是永恒的家园。家园一方面代表着亲情、宁静与安全,是人类躯体和精神的归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束缚、封闭和停滞,是人性发展的束缚,自我价值实现的障碍,激发离家欲望的原动力。米克马克人逐渐感知到了族群滞留原地的危机,书里有多处谈及他们试图做出的改变,然而所有行动几乎都限于知识的掌握程度、技术水准、思想观念、种族歧视等原因而失败了。
昆陶与碧娅特立克丝的结合,意味着白人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交融。这场婚姻表面看来颇为美满,可是,一些缺憾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弥补。混血的碧娅特立克丝从小在杜克家族的教育下成长为教养良好的淑女,她在晚年领悟到,昆陶和她在一起是一场实验,她临终时伤感地说,“我无法成为一个印第安人。”这也是昆陶对自己的一场实验,即使在白人世界里长期过着物质丰裕的生活,但当他的族人、他与前妻所生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埋藏在心里的愧疚感、背叛感和耻辱感,与对故土的思念就会立刻涌现,家园在召唤,他必须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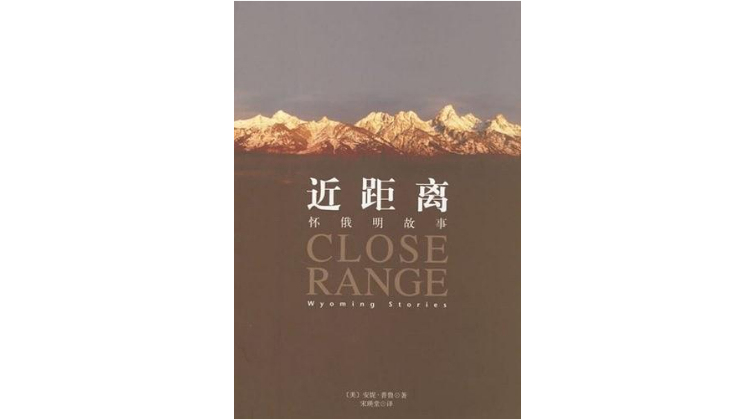
《近距离:怀俄明故事》,作者:安妮·普鲁,译者:宋瑛堂,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1月
3. 鲜明的生态主义和原始主义思想
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拉维妮娅。她出现在第八部分,“光荣岁月,1836—1870”。拉维妮娅是杜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女王”,她以女性之身革新除旧,让这个家族企业成为“日不落帝国”。她的进取之心、唯利是图,与永远澎湃的工作热情、敏锐果断的领导力糅合在一起,正是美利坚民族的特性,是19世纪晚期美国精神崛起的象征。拉维妮娅决策的重要一条,是移师芝加哥。铁路线的延伸、建筑和家居的大量需求,以及大批木材的消耗,是美国西进运动的配套设施建设,是历史的一个侧影。美国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了一个自然生态系统,然后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转攫取最大限度的财富,消失的森林成为工业化进程里不可避免的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印第安人永续生计的权利,他们被迫囿于白人规定的居留地,族群人口急剧下降,遭受种族灭绝、文化灭绝和同化。
这部小说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的政治议题,而且蕴含着更为本真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表达了人们对家园的守护、对家园的迷茫和寻找家园的精神体验。全书对森林风光与伐木人生活细节的描写极其生动、极富感情。巨大的树木亘古以来生长在孤绝的山峰和险秘的、杳无人迹的山谷,秉持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庄严神圣。对于自然的深度打扰,会受到惩罚。
书中有很多奇异的极具冲击力的死亡事故。易洛魁女人切断了特埃帕克先生的腿肌,然后把他紧密地缝合,使他全身的每一个出口,耳朵、眼睛、鼻孔、嘴巴、肛门和阴茎都闭合起来,最后膨胀爆裂而死。吉诺眼看着一根三十英尺长的原木直立起来,径直击中了伙伴的背部中心,他张大嘴巴想要尖叫,可是他的喉咙麻痹了,在那一刻,他的童年结束了。还有那几次大火灾,流动的火焰,蜿蜒盘旋着,追赶死命逃跑的渺小的人类,松木的爆裂声,狂风的呼啸,卷起的烟尘,顷刻颓塌的城镇,人有何能力对抗自然的暴怒?
《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里的好几个短篇是因自然保育联盟的邀请而撰写的,安妮·普鲁具有鲜明的生态主义和原始主义思想,《树民》的落足点也正基于此。在她看来,工业化与现代化经常吹嘘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只不过是在物质层面上取得了微薄的成功,高贵的的野蛮人藐视这种微不足道的成就,土著族群通过亲近自然完成精神层面的满足。只有栖居于自然,栖居于断背山,栖居于米克马克的故园,心灵才有休憩的桃源。所以,普鲁的写作带有理想化的虚幻,《树民》的寓意略显直白,这是该书的不足之处。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所承载的记忆,也许远比我们人类能够书写的,要多得多啊。
作者|林颐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