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徐悦东
一、丁真“出圈”全纪录:从“保护我方丁真”,到“丁真人生选择大讨论”
2020年11月,来自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的藏族小伙丁真火速走红网络,成为近期连续登上微博热搜的“新晋顶流”。丁真的走红始于11月11日,在一则摄影师波哥在抖音更新的短视频中,丁真以其淳朴羞涩的面庞征服了广大网友的心,被戏称为“甜野男孩”。

抖音@微笑收藏家·波哥的短视频截图。
“出圈”当晚,丁真再次出现在摄影师波哥的直播间里。屏幕那头,丁真羞涩可爱的神态与蹩脚的藏音普通话再次吸引一众网络颜粉。与油头粉面的男团“爱豆”相比,丁真的骤然出现,犹如拂面清风,一扫网友的审美疲劳。
然而,也是在那场直播中,摄影师将丁真比作“电子宠物”,引发网友众怒。许多人愤而发言,丁真就是丁真,不是任何人的赚钱工具。而后,微博上关于“丁真将参加选秀节目”的传闻一时四起,#丁真创4#话题几度冲上热搜,并引发一场“丁真不急网友急”的“丁真人生选择大讨论”。
在这场绵延许久的讨论中,不少网友希望丁真千万别“出道”。在他们看来,丁真就该待在老家,骑马唱歌,无忧无虑,而不是成为被资本力量操纵的“工具人”。也有网友认为,丁真可以趁此机会赚钱读书,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吵嚷过后,更多留言则是劝大家不要再“消费”丁真了,让丁真安安静静地生活。
直到“丁真成为理塘县旅游大使”的消息传出,这场争论才彻底宣告结束。许多不支持丁真“出道”的网友松了口气,夸赞丁真做出了“对”的选择。这一回,一幅丁真手举“家在四川”的照片流传开来,再次引发网络狂欢,#丁真说不要再P了#等相关话题再次冲上微博热搜榜。

丁真的微博截图。
就在网友为丁真操碎心的同时,地方官微们也开始了围绕丁真的“抢人大战”:四川的官微借丁真宣传美景,西藏的官微则用“丁真最想去的地方是拉萨”来推荐自家的旅游资源。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在邀请丁真。
从惊叹于其原生态的颜值到“保护我方丁真”,从“丁真成为旅游宣传大使”到“网友寄书给丁真”,围绕丁真的话题热度仍在持续发酵。
可以说,丁真的走红确实符合短视频和直播媒介的传播规律:一方面,他帅气端庄的五官秒杀滤镜下的张张美颜;另一方面,他黝黑的肤色,不经修饰的脸庞又让他从网红脸泛滥的短视频中脱颖而出。在直播中,丁真真诚而羞涩的回应,让网友感觉亲切、真实而不做作,连他的直播问答也淳朴十足:我没有女朋友,我的梦想是赛马得第一。
然而,在“人人都可以是15分钟明星”的互联网时代里,丁真注定将被另一个“丁真”似的甜野男孩所取代。这是因为,促使丁真火爆的社会心理基础,是长久以来公众对藏区原生态和藏传佛教(纯净、圣洁)的浪漫化想象。
与此同时,网友对丁真的原生态想象也依然是“圣洁藏地”想象的延续。在不同的媒介加持下,这种“内化的东方主义”的视角催生出不同类型的符号与叙事。在短视频时代,“甜野男孩”丁真成了“内化的东方主义”的最新文本。
二、跨文化交流与“东方主义”想象:香格里拉浪漫想象的来源
众所周知,“香格里拉”这个名称来自英国1933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部小说讲了一群英国人在飞行中偏离固定航线,最终歪打误撞进入藏区里一个叫“香格里拉”的乌托邦故事。在闯入者眼中,香格里拉与世隔绝,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过着长寿而幸福的生活。

《消失的地平线》,[英]詹姆斯·希尔顿著,陶曚译,果麦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
在学术界,这部小说被批评家视为典型的“东方主义”作品——作者以西方殖民主义的思维,想象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在本书出版时,欧洲正处于二战前夕,“香格里拉”这片纯净美好、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乌托邦,成了当时战争阴云密布下欧洲人的精神避难所。
相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与《消失的地平线》一样,这些故事的叙事套路大多都以“一个西方人不经意地闯入东方秘境”开始。作为秘境的东方民族虽然“不现代”,但他们在精神上具有神秘性和超越性,过得平和幸福、富足美满。而后,这个西方人经历一系列冒险,成功洗涤和净化了心灵,摆脱“利欲熏天”的现代生活,并找回了自我。

电影《最后的武士》(2003)剧照。本片讲述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名感到自我迷失的西方人(汤姆·克鲁斯扮演)来到日本,通过加入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武士社群来找到自我的故事。该文本也是典型的“东方主义”叙事。
从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西方人对藏地的“东方主义”想象和神化有着久远的历史,“香格里拉”不过是其中相对知名的案例。
事实上,最早提出“东方主义”概念的是文学理论家萨义德。他认为,“东方主义”是指一种“西方”视“东方”为对象的视角(在萨义德的语境里,这里的“东方”更多指伊斯兰地区,后也被大家延展至其他非西方地区)。萨义德借此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凝视和想象。“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批判性,是因为西方的这种凝视和想象,代表了西方将东方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认识论和知识视野里,其背后体现的是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不平等世界秩序。

文学理论家萨义德。
这种二元对立可以是“西方是现代的,东方是落后的”,也可以是“西方是理性的,东方是非理性的”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西方人并不在乎具体的东方是什么样的,他们只是把东方当作一面观照自身的镜子,借东方来重新发现西方本身。例如,许多西方人透过对东方的凝视,来论证“西方优越于东方”,从而为其殖民主义提供借口。另一些时候,许多西方人将东方神化成了一个个“香格里拉”,借此表达对现代生活的不满。
同理,“香格里拉”的神话只是西方对自身文明反思的一面镜子,西方人甚至会将整个藏区进行“香格里拉化”。藏学研究者、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的沈卫荣教授曾发表过多篇有关“香格里拉现象”的分析文章。沈卫荣发现,在西方历史上,西方人对藏地的认识总在妖魔化和神化这两个极端间摇摆。一方面,在历史上,许多西方人认为藏地愚昧、贫困、落后,亟须他们“拯救”;另一方面,西方人又认为古老的哲学观念和美好品质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永远地丢失了,但它们却在藏地被完整保存下来。例如,希特勒就曾派考察团去藏地寻找所谓“雅利安人”的来源。
 《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沈卫荣著,谭徐锋工作室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沈卫荣著,谭徐锋工作室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其中,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创立的“神智学”(Theosophy)就对当代西方的“藏地想象”影响巨大。她自称曾跟随喇嘛学习密法,找回了西方已经丢失的智慧。由此,她建立起一种反对科学和进化论的宗教。这种反现代化的看法与二十世纪西方对现代化的反思潮流相契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里,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将伊文思·温慈(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信徒)的《西藏死亡书》改写成了一部使用迷幻药物的指南,对嬉皮士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以对迷幻药的研究而出名,后因贩毒罪被捕,是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除此之外,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的“反文化运动”还衍生出一种混合藏传佛教等东方宗教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在这场运动里,密教的激进性为以毒品和滥交为标志的嬉皮士运动赋予了精神和政治上的正当性。此后,和平、非暴力、环保、平等利他、慈悲、和谐、自然、幸福成为了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关键词,造就西方民众“藏地想象”的主调。香格里拉也就此成为西方人的“后现代精神超市”。
在后来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套话语体系使得西方人成为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们”(此乃唐纳德·洛佩兹的名著书名,唐纳德·洛佩兹在书里以后殖民主义批判了西方的“香格里拉想象”。他们困在对香格里拉的浪漫想象里无法自拔)。就现实而言,这种浪漫化想象跟现实的藏地并无关系,它背后反映的是西方心灵史的变迁。
 《寻找香格里拉》,沈卫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寻找香格里拉》,沈卫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可以说,西方人将自己想象出来的浪漫东方想象硬套给现实的东方,这无异于一场可笑的“精神殖民”。现实的藏地跟世界上的许多边地一样,既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物资匮乏问题,也有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诸多转型问题,很多时候,人们对边地的浪漫想象实际上加剧了它们的边缘性,也无益于边地自身的发展。
三、“东方主义”的“旅行”:“东方的东方主义”是如何被内化的?
当然,“东方主义”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现代中国也有不少人加入了浪漫化想象藏区的队伍里。就跟日常生活中的“刻板印象”一样,这种从自身视角出发的“东方主义”视角似乎很难避免。
沈卫荣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古代,藏传佛教常遭士大夫“巫化”和“色情化”(这显然严重误解了藏传佛教)。明初编撰的《元史》里还提到密教中的“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这些“男女双修”的“房中术”甚至成为元朝灭亡的祸首。在元代之后,密教常常沦为色情小说的题材,比如唐伯虎的《僧尼孽海》。这种刻板印象甚至带到了“女文青进藏洗涤心灵”的系列帖子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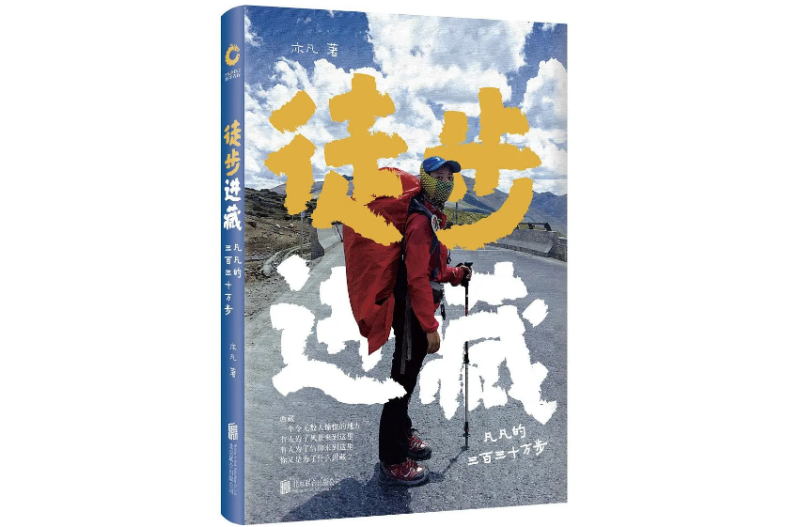 《徒步进藏:凡凡的三百三十万步》,亦凡著,新华先锋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
《徒步进藏:凡凡的三百三十万步》,亦凡著,新华先锋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
除却对“少数民族总是能歌善舞、激情奔放”的刻板印象,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还认为藏区经济落后,亟须发展。在沈卫荣看来,这依旧是“内部的东方主义”的想象建构。如今,国内对藏地的呈现和想象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内部的东方主义”有所区别,反而跟西方同类作品更相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东方主义”已然完成了自身的内化。
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兴起,使得西方的许多反思现代性的话语逐渐进入中国内部,成为“东方主义”内化的培养皿。例如,2001年,云南省中甸县为了吸引游客,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使西方的“香格里拉”这个世外桃源落了地;在出版界,仓央嘉措摇身一变,成了知名“情圣”,人们以他的名义编造情歌,熬出了一锅锅畅销的心灵鸡汤;在文娱行业,描绘藏族家庭去拉萨朝圣的小众文艺片《冈仁波齐》票房居然破亿……藏地已然成为了许多住在大城市的“小资”们寄托“信念”“信仰”“纯净之地”的象征之地。

电影《冈仁波齐》(2015)剧照。
在现代化制造“同一性”的当下,各地的传统特色和文化遗产都值得人类去细心保护和传承。为了建构自身的认同,许多特色和传统甚至会被当地人“重新发明”。尤其是与现代性相异的传统,就会被当代人挖出来加以重视。
此外,在“中心-边缘”的结构当中,边缘群体为了得到承认而迎合中心受众,甚至会出现“自我东方化”的现象,将他人对自己的想象视为真实的,并为此创造了认同。比如,以前有人批评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迎合西方观众的电影。其电影看似“很中国”但实际上并“不中国”。因为电影里充斥着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符号,而不是真实的中国符号(比如中国人并不像电影里那样挂红灯笼)。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剧照。
因此,丁真的火爆其实并无新意。人们对丁真的浪漫化想象,依然处在长久以来的“藏地想象”脉络之中。放在现代都市人更广阔的内心需求图景里,丁真不过是现代都市人渴求“田园牧歌”、“诗和远方”、“逃离北上广”的另一个代名词。网友要“保护我方丁真”,也是要保护的是这个世界当中他们在都市生活中似乎难以企及的纯真和简单。网友们不想让丁真当成被他人赚钱所利用的“工具人”,恰恰是不满自己是一名“工具人”的投射。

李子柒。
然而,丁真跟你我一样,不过是多面立体的普通人。“甜野男孩”也不过只是网友的“诗和远方”。对于丁真来说,他能在网友的情怀寄托和流量的诱惑下做真实的自己,并踏踏实实地为家乡旅游业和脱贫致富做贡献,就是对这场成名秀最好的选择。
撰文丨徐悦东
编辑丨青青子,肖舒妍
校对丨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