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澳]唐纳德·狄侬
摘编 | 徐悦东
众所周知,著名画家高更为了摆脱文明的喧嚣,来到南太平洋的“伊甸园”塔希提岛,醉心于“高贵的野蛮人”的生活,并创作出许多经典作品。毛姆以此为原型,创作出了名著《月亮与六便士》。不过,太平洋岛民是“遗世独立”的“高贵的野蛮人”或许只是西方人单方面的想象。其实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太平洋群岛处在多个文明的交汇地带,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航行者给当地带来了纷繁复杂的文化影响。鲜为人知的是,印第安文明甚至也与太平洋群岛有所交流,这也打破了印第安文明“与世隔绝”的刻板印象。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剑桥太平洋岛民史》,略有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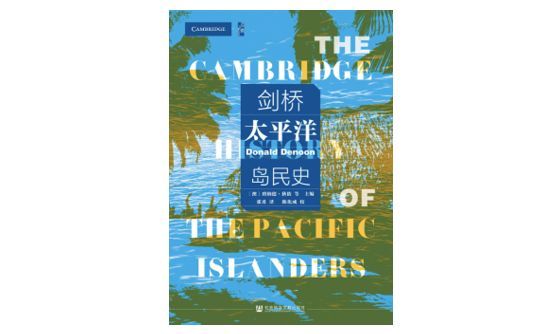
《剑桥太平洋岛民史》,[澳] 唐纳德·狄侬主编,张勇译,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距今约500年时,欧洲人到来前夕的太平洋是怎么样的?
在距今1000~800年时,人类开始定居新西兰北岛和南岛。在距今约500年时,随着更为偏远的查塔姆群岛也被占有,人类完成了对太平洋岛屿的殖民。虽然亨德森岛、皮特凯恩岛和范宁岛(那些波利尼西亚的“神秘岛”)等岛屿曾被人类定居或造访过,但后来都被遗弃了。由于再也没有岛屿可寻,以及东边的南北美洲已被人类找到并与之短暂接触过,殖民就停止了。
在距今1000~500年时,波利尼西亚实现了人口快速增长、农业扩张和集约化。夏威夷人清除了数千平方千米背风坡森林,并形成了集约型旱作农田系统,即在夏威夷大岛及毛伊岛部分地区对甘薯、面包果树和芋头等农作物实行了垂直分区种植。值得商榷的是,人口扩张在欧洲人到来前是否已达到环境上限,人口趋向稳定还是衰退。尽管在夏威夷没有发现确凿证据,但拉帕努伊岛民很可能确实引发了环境危机,在马克萨斯群岛也可能出现过这种情况。
环境对增长的限制也被用来解释夏威夷群岛和其他群岛等级森严的酋长制。
旧观点强调土地战争和酋长的军事领袖身份是有限环境无法承载人口压力的必然结果。新理论认为当地居民在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酋长间的竞争则是发展的动力。尽管我们在讨论等级酋长制和国家兴起时经常援引夏威夷群岛,但其作为国家形成一般方案原型的地位仍有待确定。一方面与其他岛屿“原型”一样,情况的特殊性也很重要。夏威夷群岛在全世界有人居住的岛屿中是最与世隔绝的。如果没有通过贸易或索取贡品与其他“原始国家”或其他社会建立起固定联系,那么其他社会就不会发展成为国家。
另一方面,汤加群岛和萨摩亚群岛恰好处于这种联系之中,这种联系主要起源于1000年前的祖传体系,从包括斐济东部岛屿在内的区域角度来看应被视为一个“世界体系”。直到波利尼西亚人在美拉尼西亚海洋岛东端所谓“离岛”上和在密克罗尼西亚某些岛屿上建立社区,这个“世界体系”的影响才被广泛感觉到。这些波利尼西亚人更有可能是来自西波利尼西亚王朝冲突的难民,而非受到友好接待的幸运漂流者。
在新几内亚岛和美拉尼西亚海洋岛的一些地区,距今1000~500年时的物质文化和聚落形态似乎与欧洲人刚来时所观察到的大体相似,但是在此期间它们在所罗门群岛部分地区和瓦努阿图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诸如蒂科皮亚岛及其邻近岛屿等“波利尼西亚离岛”上,它们在距今约750年时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蒂科皮亚岛的物质文化中,波利尼西亚元素日益突出,一些建筑采用了西波利尼西亚的样式,从西波利尼西亚直接输入了石锛,还在从瓦努阿图停止输入陶器后出现了一些新型人工制品。

高更的《两位塔希提妇女》
在瓦努阿图埃法特岛上有一座这一时期的酋长墓葬。根据口述传统,墓主人是来自“南方”的罗伊·马塔。他不仅控制了埃法特岛的许多氏族,还开创了埃法特岛酋长头衔。在他死后,氏族代表们将他与人祭和“自愿”人牲埋葬在一起。罗伊·马塔被描绘成波利尼西亚移民,而且他的葬礼也令人想起西波利尼西亚酋长们。与此前相比,在这一时期人们更加依赖诸如螫刺钻孔器和蜘蛛螺扁斧等贝壳工具,这表明物质文化引入了新元素,而且陶器生产可能停止了。在阿内蒂乌姆岛的两座酋长墓葬里出土了一组类似的装饰品,这印证了有关酋长葬礼的口述传统。其中一座墓葬的年代可追溯至距今300~400年时,骨骼分析表明墓主人是波利尼西亚人。在埃法特岛以及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的波利尼西亚离岛上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其他几座墓葬遗址,这些墓葬遗址都有着类似的物质文化。
离岛上讲波利尼西亚语的岛民,新喀里多尼亚和瓦努阿图语言中的波利尼西亚语外来词,包括毛伊提基和汤加罗亚神等波利尼西亚文化英雄的当地神话,以及与“汤加人”交往的口述传统,这些都表明在过去700年里离岛受到过波利尼西亚文化影响。交往的性质及影响各不相同。如今生活在所罗门群岛伦内尔和贝罗纳的波利尼西亚人有一些关于皮肤更黑的被称为西提人的口述传统。根据口述传统,当他们从“乌毕阿”(可能是新喀里多尼亚乌韦阿岛西部)来到这里时,他们发现西提人早就定居于此了。在和平共处一段时间后,双方发生了冲突,最终西提人被屠杀。这一故事似乎可被这两个岛屿语言中的“西提下层语言”所证实,从而表明这里的确曾存在过一个与所罗门群岛主岛讲所罗门东南语族语言的岛民有关联的族群。
考古学证据表明,马西姆地区的库拉交易圈、巴布亚湾的希里交换体系和加罗林交换体系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500年前,库拉交易圈对新几内亚岛本土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影响。68虽然口述传统表明希里交换体系形成于大约200年前,但是与密集沿海贸易相适应的聚落形态大约出现在1200~1500年前,并在大约300年前再次出现。到大约300年前时,加罗林交换体系东部岛屿已衰落。
直到20世纪30年代新几内亚高地才与欧洲人建立直接联系,但是间接影响也许始于200~400年前甘薯的传入。甘薯不仅使高海拔地区也能发展农业,而且作为一种旱地作物还进一步提高了早已发展农业的高地地区的生产效率。它最初由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移植到菲律宾,然后通过交换路线又由菲律宾移植到马鲁古群岛和新几内亚西部。尽管甘薯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从来都不重要,但在大部分高地地区却是主食,并在20世纪仍在向高地边缘地区传播。库克沼泽第五阶段(距今400~250年间)的排水系统可能为种植甘薯进行过改造,因为灌渠的规模和式样与现代高地西部的甘薯园圃相同。然而,戈尔森将这一阶段解释为苗床栽培的发展期,并将第六阶段(距今250~100年间)视为甘薯引种时期。在采用新作物之后,对种植空间进行了优化,而且还在第六阶段放弃了库克农业遗址第五阶段的2/3可耕地。到那时,始自第四阶段的沼泽栽培技术已失去主要优势。甘薯使猪群得到大规模扩大,从而支撑了高地杀猪业和交换圈,如恩加地区的蒂交换体系和哈根地区的莫卡交换体系。
 高更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
高更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
加罗林群岛富饶的火山岛不仅通过贸易彼此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通过庇护关系与低海拔的环礁联系在一起。在距今1000~500年时,密克罗尼西亚普遍出现明显社会分层。马里亚纳群岛的拉提结构石柱是地位高者的住宅的地基,其历史可追溯至约1000年前;波纳佩岛南马特尔的巨石建筑始建于750年前。南马特尔由大约92座被狭窄水道隔开的人工小岛组成,总面积为80公顷,其中小岛面积仅为30公顷,岛上有住宅、会堂和墓葬,都在高墙内。根据口述传统,它是邵德雷尔王朝的首都。该王朝在波纳佩岛上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直到距今大约1350年时才因低等级酋长叛乱而瓦解为五个政权。然后,南马特尔基本被放弃。南马特尔巨石建筑开建时恰逢波纳佩岛制陶业终结。
距波纳佩岛480千米的勒鲁岛也有类似的“城市”建筑群。勒鲁岛位于主岛科斯雷岛沿海,是一座人工扩建的小火山岛。与南马特尔一样,岛屿中间地带也有一个“非嵌入式的精英中心”,也由高墙内的住宅和会堂组成,也有运河网。人口在19世纪初约为1000~1500人,包括大酋长等科斯雷岛高等级酋长。迈克尔·格雷夫斯将大酋长视为“酋长中的酋长”,而非绝对统治者,就像波纳佩岛邵德雷尔王朝那样进行统治。他还指出,勒鲁岛的巨石建筑要晚于南马特尔,始建于公元1600年左右,但很快就完工了。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太平洋岛民并不“与世隔绝”
到16世纪时,当地居民的大规模迁徙已完成。在通常描述“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合乎逻辑的分布时,似乎这些文化区域不仅彼此不同,也有别于相邻的澳大利亚、东亚和东南亚,或者美洲。这些术语的历史和用法在第一章中曾被讨论过。在这里,我们试图消除如下两种印象:一是岛上居民彼此断绝了一切联系,二是整个地区在库克时代之前一直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岛上居民与世隔绝和孤立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存在的,但被18世纪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夸大了。对于他们而言,岛屿社会例证了独特的(和更加纯粹的)原型。本文追溯了较小规模的居民迁徙和思想交流,年代通常要比上文所讨论的更近些,从而以互动的证据纠正了与世隔绝和孤立的错觉。
在长达2000年的太平洋史前时期,漂流者似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来自东南亚、南美洲以及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每个岛屿都有大量漂流者。他们可能留下了一些可发觉的遗迹,尤其是如果这些陌生人的身体或文化特征明显的话。在18世纪,一些欧洲人对岛民体征的多样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推断这肯定与东南亚的漂流者或殖民者有关。例如,拉彼鲁兹在1787年确信东南亚人向东航行曾最远到过萨摩亚:这些[波利尼西亚的]不同民族来自马来人的殖民地。马来人曾在不同时期征服过这些岛屿。我确信,迄今为止在吕宋岛和中国台湾岛腹地发现的卷发人种是南半球的菲律宾、中国台湾岛、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瓦努阿图、汤加等岛屿的和北半球的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夏威夷的土著居民的祖先。
 高更在塔希提岛的房子。
高更在塔希提岛的房子。
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和瓦努阿图,他们没有被征服过;但是在那些更靠东的岛屿上却被征服了,因为它们太小了以至于无法让他们从中心地带撤退,于是他们就与征服者混合在一起了……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种族在萨摩亚群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我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其他起源。拉彼鲁兹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解释波利尼西亚人与斐济人等美拉尼西亚人在身体特征、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异。
最近,学术界主流观点已经开始转向反对文化扩散说,因为它强调从本质上对种族进行分类,有时其阐述还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现代学者更倾向于从地方适应和土著能动性角度来解释多样性,但是就像将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那样,他们不仅抛弃了文化扩散理论,还罔顾了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以一种比其代表人物更具批判精神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些学术成果,我们就可以恢复对岛民经历的流动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恰当判断。从定居东波利尼西亚到16世纪欧洲人闯入,跨太平洋航行可能很罕见,但数百年来当地居民的确一直在太平洋边缘航行。如果他们从未被抛弃在意想不到的海滩上,那将是非同寻常的。描述人类多样性的现代遗传学研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流动性的兴趣。
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水手和商人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东南亚贸易。随着船舶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适于航海,他们在异常天气中(例如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有可能幸免于难,尽管其航程被迫终止。一份公元3世纪的中国资料所提到的外国船,长达50余米,距离水面4~5米,可运载六七百人和250~1000吨的货物。一份公元8世纪的中国资料所描述的船更大。在印度阿旃陀石窟,一幅公元6世纪的壁画所描绘的一艘船,有三个高桅杆,一个装有风帆的船首斜桅,复杂的操舵装置,但没有舷外支架。由于加里曼丹岛岛民成功横渡印度洋,定居马达加斯加岛,这表明了一些航行的规模。

波利尼西亚人
亚洲水手在太平洋上也很活跃。有证据表明,在史前时期至少有三艘东南亚船只曾遭遇海难。富图纳岛有一个关于中国人的著名传说(中国在当地语言中被称为Tsiaina)。Tsiaina肯定是在欧洲人到来后才有的一个词语,但是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个传说的主要元素。这一传说被记录下了六个版本。至少两个版本都具有的共同要素包括:(1)这些移民曾在富图纳岛的姊妹岛阿洛菲岛登陆;(2)他们在登陆后挖了一些井;(3)他们不仅与该岛岛民结了婚还生育了后代;(4)他们更改了一些地名;(5)他们一边敲打被称为拉利(lali)的木锣,一边四处走动,并根据回声决定在哪里定居;(6)他们推广了更好的耕种方法;(7)他们推广了经过改良的树皮布制作方法和染色方法;(8)他们最终被推翻,并被屠杀。1843年到来的传教士伊西多尔·格雷泽尔所编撰的富图纳语词典将另外一个创新也归功给了他们,即“moo”这个词被定义为“据说来自中国的一种矮胖的猪”。
上述传说的许多共同要素可以被证实。矮胖猪(moo)仅限于富图纳岛及邻近岛屿。71阿洛菲岛上那个登陆点被称为萨阿瓦卡,该地名在一些波利尼西亚语中被译为“圣船”。挖井表明富图纳岛当时正饱受干旱之苦,因此这次航行可能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在萨阿瓦卡仍保留着一口被认为属于他们的井,它深6米,宽2.4米。与欧洲人接触之初,乌韦阿岛和斐济仍在使用木锣“拉利”,但是直到最近它才在汤加和萨摩亚为人所知,这表明它们在太平洋中部岛屿上是新事物。利用水浇地种植芋头是一个可归因“中国人”的创新,因此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岛屿都不懂这项农业技术。同样,东波利尼西亚岛屿也不知道福图纳岛树皮布的两种制作方法和一种染色方法。这些方法都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发明。
富图纳传说声称,那些“中国人”被推翻是因为他们的统治日益难以忍受。这似乎发生在荷兰探险家斯考滕和勒梅尔于1616年访问富图纳岛之后(参见第四章),因为他们探险队的一位艺术家描绘了岛上酋长们的模样,他们的头发又长又直,梳着辫子,而当地老百姓都是卷发。这些荷兰人还记录了一个专门称呼酋长的词,该词在传教士到来后就逐渐被废弃了。这个词就是“latou”(准确拼法为“latu”)。该词与许多东南亚语言中的“datu”是同根词,意为“国王,国君,统治者”;萨摩亚语中仍保留着该词的同根词“latu”,意为“主要建设者”;斐济语中也保留着其同根词“ratu”,意为“酋长”;在一些汤加人姓氏中也保留着其同根词。富图纳语中的敬词也在传教士到来后被废弃了,但是,仍可找到一些痕迹,而那些汤加、乌韦阿岛和萨摩亚仍使用的敬词显然与富图纳语有着共同的来源和联系。
20世纪20年代,学者E.S.汉迪认为,富图纳岛的“中国人”可能也将汤加罗亚教带到了西波利尼西亚,从而使之取代了那里的印度-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据汉迪推测,汤加罗亚教起源于中国的华南地区。但是,由于汤加罗亚神在波利尼西亚被认为是“海洋之王”,因此上述宗教似乎更有可能与当地居民一起来自苏拉威西岛西北的桑义赫群岛,“tagaloang”在那里意为“公海、海洋”。其他波利尼西亚语词语,包括木锣“lali”,也似乎可追溯至桑义赫群岛。此外,敬词在这些语言中也很重要。桑义赫群岛岛民是杰出的造船匠和水手,由于他们的社会分化为贵族、自由民和奴隶,不禁让人想起波利尼西亚那些受到汤加罗亚教影响的岛屿。
迄今为止,人类在东波利尼西亚定居的最早放射性碳年代是公元300年,遗址位于马克萨斯群岛努库希瓦岛。该遗址出土的陶器碎片明显产自斐济的雷瓦三角洲。马克萨斯群岛的首批定居者显然是汤加人,因为马克萨斯语中的某些词语不可能来自其他地方,如“mei”(面包果)、“maa”(面包果酱)、“puou”(各种面包果)、“too”(甘蔗)、“tokave”(各种小椰子)、“hoho‘e’Kuhliidae”(鱼类)和“kumaa”(老鼠)。此外,马克萨斯群岛还有非汤加血统的定居者,具有美洲血统的定居者似乎是从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来到这里的。
拉帕努伊岛可能早在第一个千禧年中期就有人类定居了。太平洋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里的首批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语言学家将东波利尼西亚语言分成两类,即马克萨斯语和塔希提语,而拉帕努伊语则被认为是单独语种。)然而,首批拉帕努伊岛居民更可能是厄瓜多尔或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因为在欧洲人到来时拉帕努伊岛和东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上种植着大量美洲农作物,特别是甘薯、菠萝、辣椒、26条染色体的棉花、无患子和木薯。从亚洲传入南美洲的葫芦、香蕉和蓝蛋鸡也一定是从东方传入东波利尼西亚的。
在此后数百年里,漂流者显然是带着一些农作物和鸡从拉帕努伊岛漂流到马克萨斯群岛、皮特凯恩岛、曼加雷瓦岛、土阿莫土群岛和社会群岛。起初,这些是东波利尼西亚经济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波利尼西亚人从西部引入了芋头、山药、甘蔗、面包果树和构树等农作物,拥有这些农作物的岛屿几乎遗弃了辣椒、菠萝和棉花,但是甘薯、葫芦和香蕉仍然很重要。斗鸡和一种被大量饲养的家禽也从西波利尼西亚引进到东部,此外还有狗和尖背猪。许多东波利尼西亚词语,包括一些与香蕉和鸡有关的词语,在西波利尼西亚并不为人所知。这表明该地区的早期文化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特色。其中一个特色似乎应完全归因于美洲的影响,即建造大型石头建筑,如土阿莫土群岛和社会群岛的会堂或宗教庭院。然而,会堂(“marae”)一词肯定来自西方(在富图纳语中,“malae”意为“公共场所”)。

波利尼西亚的航行者
大约在公元1100年时,拉帕努伊岛成为第二支美洲印第安人移民的家园。他们属于以安第斯山脉为中心的蒂亚瓦纳科文化。他们及其后代在拉帕努伊岛建造了著名石像摩埃(moai)和小型塔式建筑物图帕(tupa),后者在名称、外观和功能上都类似于安第斯山脉的储尔霸(chullpa)。所有幸存的图帕都被建造成以承材支撑的拱顶,即内墙石材从底部到顶部相互重叠,从而使直径越靠顶部越小,直到形成圆顶状天花板。另一独特之处是把大楣石置于小而低的入口上方。在安第斯山脉,储尔霸始建于公元1100年,停建于西班牙征服美洲时期。
拉帕努伊岛的图帕极其类似于安第斯山脉的早期储尔霸。这两个地方的建筑物都被认为是用来陈列死者骨头的。曼加雷瓦岛附近的特莫埃环礁有一个类似图帕的会堂,叫作奥图帕(Otupa)。另外,拉帕努伊岛的摩埃和图帕的建造者似乎对波利尼西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群岛的口述传统讲述了一个关于“罗图马王子”的故事。这位王子定居博拉博拉岛,并通过婚姻成为王室成员,其子孙到19世纪中期时已在该岛延续了九至十四代。社会群岛其他史前外来者都来自失事的西班牙轻快帆船“圣莱斯梅斯”号。
该船是1526年5月26日从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的四艘船之一。六天后,“圣莱斯梅斯”号在一场暴风雨中与船队失散,该船及其约53名船员从此杳无音讯。这些船员有来自加利西亚和巴斯克等地的西班牙人,还有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佛来芒人。1929年,在土阿莫土群岛阿马努环礁上发现了四门古代大炮,其中两门铁定来自“圣莱斯梅斯”号。这艘轻快帆船夜间在阿马努环礁搁浅,船员们扔掉大炮,继续向西航行,寻找避风港修理该船。他们的第一站是塔希提岛以东400千米处的阿纳环礁,一些船员在这里离开了该船。其余船员来到塔希提岛西北约200千米的赖阿特阿岛东南角的奥波阿湾,于是他们开始在这里修理这艘轻快帆船或建造了一艘新船。在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冀图向西南航行到好望角,然后前往西班牙,起航前留下了一些西班牙人,同时带走了一些波利尼西亚男人、妇女和儿童。
文化传播论者推测,来自一艘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上失踪的西班牙大帆船的漂流者对夏威夷产生过影响。这个理论起源于库克船长抵达夏威夷之后不久。三件重要物品使他的几名军官确信西班牙人早于他们抵达这里。这些物品是夏威夷酋长的羽冠头盔和羽饰斗篷,还有几把铁匕首。军官詹姆斯·金认为头盔和斗篷与波利尼西亚风格“截然不同”,并声称它们与以前的西班牙风格“非常相似”。一些在19世纪初被记录下来的夏威夷口述传统支持了詹姆斯·金的假设。其中一个版本讲述了七名白人男子在库克船长到来之前是如何登陆凯阿拉凯夸湾的。据说,他们的后代不仅“肤色较浅”,还有“相应的棕色卷发”。
在20世纪,对西班牙亲戚说的质疑越来越多。一位批评家指出,夏威夷酋长的头盔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头盔大不一样。然而,据悉在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之间曾有过三艘西班牙大帆船失事(分别在1576年、1578年和1586年)。20世纪50年代末,在凯阿拉凯夸湾的一个洞穴里,曾发现一位被奉若神明的酋长的墓葬,并在棺木中找到两件非波利尼西亚风格的物品。其中一件是嵌在木柄上的一块铁,像凿子;另一件是一段机织帆布。也有人认为,夏威夷头盔模仿的是菲律宾耶稣受难复活剧中扮演圣经时代罗马士兵的演员们所戴的头盔。
同一时期另一艘失踪的西班牙船似乎是在所罗门群岛的波利尼西亚离岛翁通爪哇环礁结束航行的。这就是“圣伊莎贝尔”号。它是1595年离开秘鲁驶往所罗门群岛的门达尼亚探险队的四艘船之一。“圣伊莎贝尔”号在接近目的地时与其同行船只失散,从此杳无音讯。1971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岛(今所罗门群岛马基拉岛)的帕穆阿发现了一些外来陶器碎片和其他独特物品,这表明有船员和乘客曾在那里宿营过。由于翁通爪哇环礁有许多具有欧洲人相貌的岛民,因此自那以后就一直表明“圣伊莎贝尔”号后来搁浅在那里。其他具有类似相貌的翁通爪哇环礁居民已经迁至霍尼亚拉和圣伊莎贝尔岛。
另外三艘失踪的西班牙船只,以及一群被困马绍尔群岛的叛乱者可能在密克罗尼西亚也扮演了类似角色。1527年,“圣地亚哥”号和“埃斯皮里图桑托”号在从墨西哥远航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时失踪。这两艘船连同60名船员似乎失事于加罗林群岛西部的法斯岛和乌利西环礁。在将近70年后的1595年,门达尼亚探险队的辅助船“圣卡塔利娜”号可能曾靠岸加罗林群岛东部的波纳佩岛,这艘渗漏严重的船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波纳佩岛附近。在这之前的1566年,27名“圣赫罗尼莫”号船员在哗变失败后被放逐到马绍尔群岛最西端的乌杰朗环礁。
漂流者影响的全部性质和程度永远不会被确定。与大多数史前史学者相比,这种说法所考虑到的漂流者要多得多(也更多样)。除了外来的漂流者,美拉尼西亚人也从一个岛屿漂流到另一个岛屿,波利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也是如此。进一步研究可能会还原其中一些水手的本来面目,但这些惊人的新发现只是漂流者参与太平洋岛屿定居和移居故事的一小部分。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 | 宫照华
校对 | 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