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作家沈昌文于今日凌晨逝世,享年90岁。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曾于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在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中,他曾称《读书》杂志办刊的方针为“无能,无为,无我”。在沈昌文的贡献下,作为一份思想刊物的《读书》对各路思想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密切注重和读者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既不乏前沿思考,又具备大众化可读性的特点,笼络了一批时下中国文化界最忠实的读者。以《读书》为媒介,沈昌文先生也与诸多思想界的大家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
当年, 为庆祝沈昌文先生八十八岁寿辰,先生的旧识、好友等收集了三十四篇趣事文章,结集成《八八沈公》一书。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出版人、学者、媒体人,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地记述了自己眼中的沈昌文先生。今日,我们摘编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的文章。以下内容摘编自《八八沈公》,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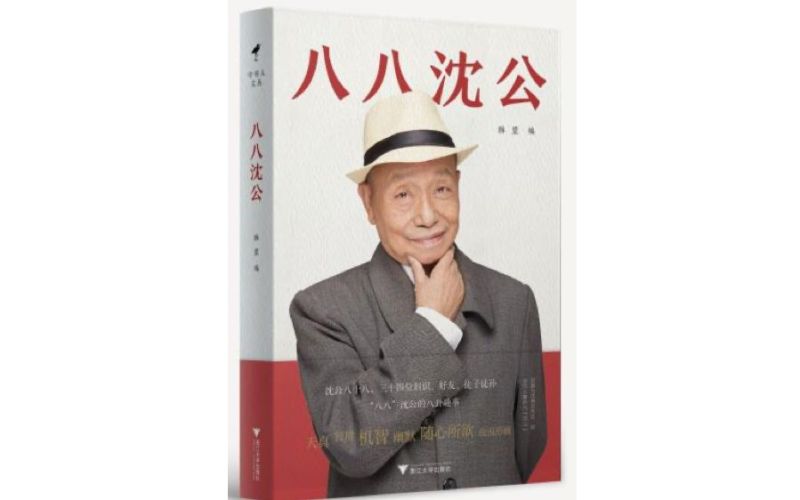
《八八沈公》,作者: 脉望,出版: 草鹭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撰文|江晓原
我与沈公的交往,若以“神交”言之,已有四十年历史,可谓久矣。然而我对沈公的印象,却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这些零碎的印象,有的属我亲历,有的得之于传闻,有的来自文献记载,有的出于个人解读,拼合起来,或许能够形成沈公一个鲜活的侧面。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沈公与扫地僧
我第一次见沈公,是在怎样一个场合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些报纸记者,沈公对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然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那时我的弟子穆蕴秋还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有一天我偶然和她说起记忆中沈公这两句奇特的话,她立刻想到了金庸《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中的少林寺藏经阁扫地僧,大为叹服道:沈公厉害,他是在以扫地僧自况啊!当然,这是她的个人解读,沈公当时是不是在以扫地僧自况,那只有沈公自己知道。不过,以沈公在出版界江湖的勋业和名声地位,真要以扫地僧自况一回,自然也无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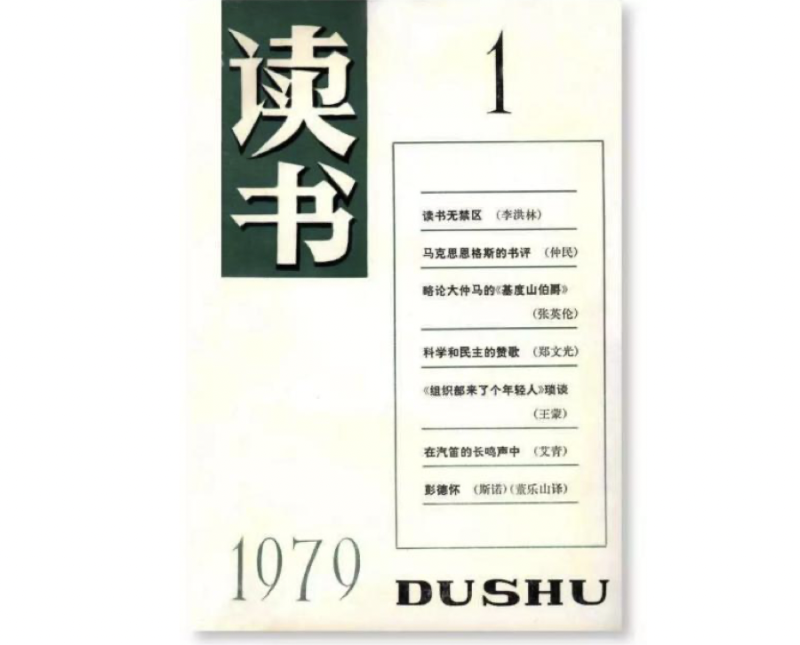
《读书》1979年创刊号
其实我和沈公打交道,可以追溯到整整四十年前。只是说来奇怪,这番交道当时我自己并不知晓,所以可称之为“神交”。却说那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但已经成了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的粉丝。有一次心血来潮,给《读书》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建议他们给自己另外取个英文刊名,不要叫作“DUSHU”——这个建议直到今天《读书》也没有采纳。但令人惊奇的是,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沈公居然一直保存着,而且还在他晚年的书中提到了,并登了信件的照片!这就让我着实受宠若惊了。随着我在学术江湖混迹日久,渐渐真的和沈公有了小小交集。记得有一次我正和一位编辑好友一起在三联的图书中心看书,忽遇沈公,他说他正要在附近的饭店请客吃饭,既然在此处邂逅,就邀我和女编辑一同赴席。长者之命,自当遵从,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和沈公同席。饭局非常愉快,我只记得席上沈公被一众才女包围着,她们燕语莺声,用种种甜言蜜语赞美沈公,沈公则怡然自若,一派老神仙风范。
沈公与“三结义”
沈公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在“‘海豚书馆’缘起”一文中说: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有过一次‘三结义’。……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延用“桃园三结义”的比喻,沈公最年长,自然是刘玄德了,那关、张二位,偏偏和我都是多年的朋友。特别是俞晓群,每次“南巡”上海,必会招宴。在他的饭局上,有多次是他们“三结义”都在的,于是又得到亲近沈公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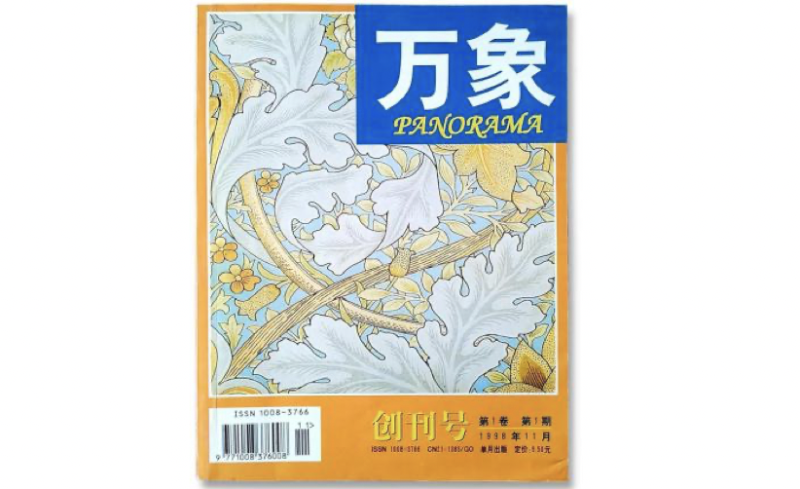
《万象》1998年杂志创刊号
沈公提到的“三结义”成果之一,是 1998 年创刊的《万象》杂志。我为这本杂志写过多次稿件,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份杂志,特别是喜欢她的风格。在沈公“三结义”中的陆灏离开《万象》杂志之后,继任者仍然保持了陆灏的风格,直至杂志寿终正寝。我保存着《万象》从创刊直到 2013 年结束的全套杂志。沈公负责《读书》杂志多年,曾为她付出过大量心血,那肯定是沈公“爱”的对象。当然《读书》杂志也是我“爱”的对象,不过我之“爱”与沈公之“爱”不可同日而语,我只是保存着《读书》从创刊以来的全套杂志,并且不时为她写稿,略效绵薄之力而已。记得那时《读书》杂志正在经历着她历史上文本最不吸引人的阶段——所幸这个阶段早已经结束了。沈公当时有名言曰:
我现在不看《读书》了,只看《万象》杂志。
这话大得我心,因为我当时《读书》杂志也看得越来越少了,只是出于怀旧心理,恋旧情怀,对她的常年订阅依然继续着。那时我也贡献了一句小小的“名言”,这“名言”后来被沈公载入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
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言:‘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
我有幸被沈公品鉴的“名言”虽属玩笑,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读书》不久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沈公先前重视文本可读性的传统,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而与此同时李零也恢复在《读书》上写文章了。

沈公与《读书》杂志之思想及文本
沈公在图书出版界江湖上的惊人艺业,我不大敢置喙,那得是沈公“三结义”中写了三大本《一个人的出版史》的俞晓群那样的资深优秀出版人才有资格谈论的。但是对于《读书》杂志,我自认有一点一孔之见,或许值得说两句。这也是我后来学习了沈公的著作,回顾前尘往事,得到的一点体会和印证。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就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书》创办时的宗旨,竟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将《读书》办成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沈公回忆说:
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
奇妙的是,这番话却帮助沈公领会了《读书》的使命。
现在回忆起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初创的《读书》之所以会吸引我这样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理科大学生,“思想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读书》创刊的前一年,即 1978 年,最让中国科学界兴奋的事,莫过于“科学的春天”,其实《读书》当初的使命,又何尝不是在呼唤人文学术的春天呢?
《读书》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读书》上的文章好读。用学术黑话包装一下就是“对文本有美学追求”。我当时只是感觉《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上的明显不同,《读书》的许多作者学植深厚,还能有一番锦心绣口,所以让我特别爱读,却不知这也正是《读书》有意追求的境界。近读沈公题赠之《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此得到有力印证。里面谈到当时对《读书》上文章的要求,首先是“厚积薄发,行而有文”,甚至“不文不发”。沈公回忆说: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像《读书》这样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是会给她的作者们带来荣誉感的。我想到的最典型也最八卦的例子,是张鸣教授在文章中提供的。他说他在求学时代,室友心心念念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他念兹在兹的却是想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只是老也发不成,让他十分郁闷。想想《中国社会科学》今天的学术地位,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在今天的体制内就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之事,可是在当年张教授眼中,和《读书》相比居然何足道哉!《读书》能被学人如此心仪,它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沈公“不文不发”的提倡之功,诚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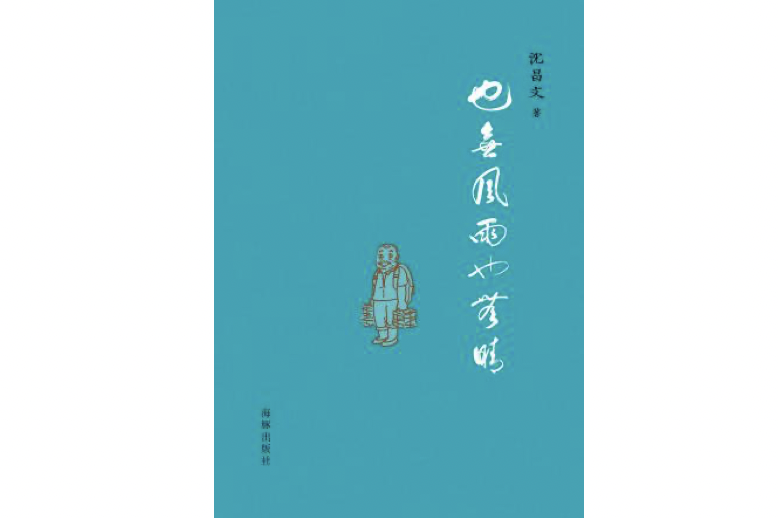
沈公之神仙岁月
沈公晚年,游戏人间,常背着小青年们喜欢的双肩包,自称“问题老年”,还经常拿他和那些年轻貌美的女编辑们的亲密关系开玩笑。女编辑们都不以为忤,她们爱戴他,“宠幸”着他,在饭局上用各种甜言蜜语去哄慰他。旁人观之,竟是一派和谐,殆近于朱熹《诗集传》中所言“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之境界矣。
2015 年 8 月,我的科幻影评集《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在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上发布,沈公亲自前来为我站台,和沈公一起站台的还有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沈公的“三结义”俞晓群、著名影评作家毛尖,他们都对拙著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和推荐。这也许是我和沈公发生过的唯一的一次“工作联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