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丨[英]保罗·迪肯
摘编丨安也
创世科学和进化科学的平衡法案
“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可能会出错”是个强大而有说服力的观点。你会发现,那些更加习惯抽象哲学思考的记者和政客往往会这么认为。当然,这个观点还意味着,如果你曾有过讲授科学哲学入门课程的复杂经历,你肯定会在本科生中找到可预测的规律。甚至科学家们自己也普遍接受以下观点——它来自那些从事前沿实验研究的人们,他们卷起袖口,嘴角叼着香烟,就好像在实在的基本结构之下修修补补一样。因此,这种观点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科学的理解。它甚至成了美国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的判决基础,这些判决关乎高中科学课程的讲授内容。
1981年,阿肯色州通过了第590号法案,它又被称作创世科学和进化科学的平衡法案。尽管措辞有些模糊且表述有些别扭,但其总体信息却非常明确:在阿肯色州的任何一所公立学校,老师给学生讲授生物复杂性如何逐渐从简单的源头进化而来的同时,也必须讲授生物复杂性是如何突然从自发创造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想法的要点在于,学生应该同时知晓这两种理论,以便他们独立得出自己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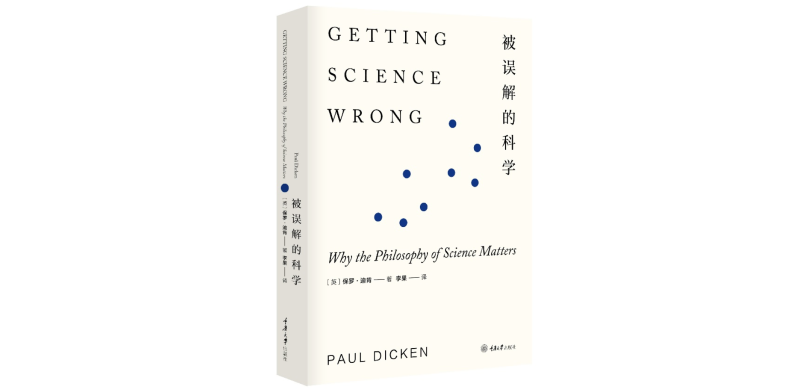
本文出处《被误解的科学》,[英]保罗·迪肯著,李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第590号法案通过后不久,一个由当地社区宗教领袖组成的组织向阿肯色州教育委员会提出了诉讼,他们都主张完全不必拘泥于《圣经》的字面解释。原告方以牧师威廉·麦克莱恩为领导,他是联合卫理公会的执行牧师,其中还包括主教、罗马天主教、长老会、非洲卫理公会教会的代表、犹太教成员以及一些相关的教师和家长等等。他们认为,第590号法案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除了众所周知的保护言论自由以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明确禁止任何打压或提倡某种宗教信仰的政府行为,有人认为,公立学校中讲授自发创造的内容乃是阿肯色州对基督教基要主义的明确认可。
结合专家证人的证词和大量宣传,历经两个月的庭审后,他们的诉求最终得到威廉·R.奥弗顿法官的支持。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乃创世论在美国法院系统中遭遇的第一次挑战,它也标志着美国科学与宗教之间漫长而不堪的冲突的重要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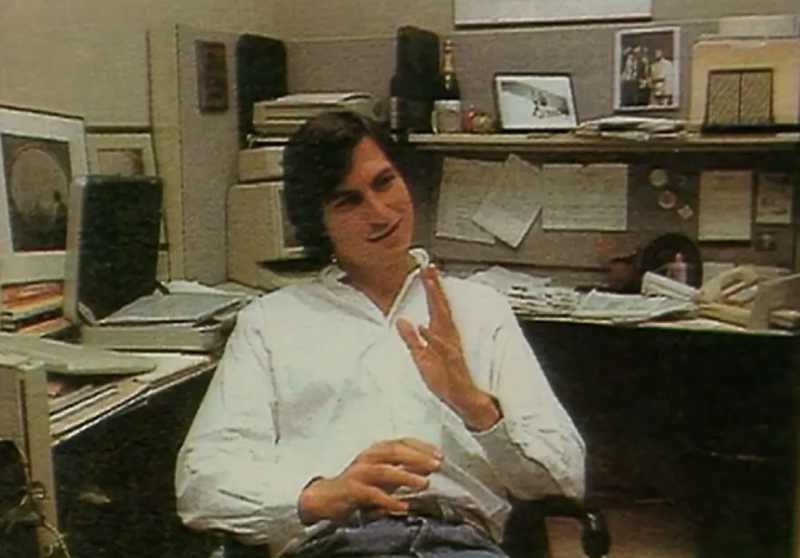
纪录片《书呆子的胜利:意外帝国崛起》(1996)剧照。
这个过程始于1925年,当时,约翰·斯科普斯因为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而被田纳西州起诉。所谓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又译斯科普斯审判或猴子审判)是一场媒体的狂欢,著名政客和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领衔起诉,著名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则负责应诉。斯科普斯被定罪并被处以罚金(尽管这个判决后来因为技术性细节而撤销)。类似的小冲突随之而来,尽管创世论者逐渐失势,但直到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才最终推翻了禁止教授进化论的现行法规。就在这个档口,创世论者突然发现自己已处于守势,他们便转而开始在主流社会越发接受自然选择理论的情况下,为自己的观点寻求“平等对待”。
第590号法案是将创世论保留在学校课程中的诸多尝试之一:这是个游击战的新时代,他们避免与正统科学直接对抗,而是试图从内部颠覆它。有人认为,如果科学方法确实致力于开放与批判探究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对自己珍视的观念的某种宣传——那它就应该对其他观点的讨论持欢迎态度。在一个相当精巧而聪明的策略中,创世论者认为,科学自己才会要求在学校课程中给予创世论平等的对待。
然而,我们旋即应该注意到,创世论的科学依据实际上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完全无关。无论它是否具备其他优点,创世论首先是一种宗教教义。就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案而言,有人指出,第590号法案并非简单地假定生物复杂性乃某种自发创造的行为,而是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生命起源的详尽说明,其中的内容与《创世纪》中的记述完全一致,甚至从全球范围的洪灾的角度对地球的地质情况的解释也是如此。
还有人指出,尽管自发创造并未就生物复杂性提供替代解释,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解释。然而,590号法案并未包含佛教宇宙论、印度教转世的无限循环观念,或者任何美洲原住民的创世神话等相关内容。它也没有为下列观点寻求某种“平等对待”:生物体先是抵达了小行星的背面,然后在某种星际碰撞之后散落在了地球表面;或者,作为某种邪恶计划的一部分,矮小的绿色外星人一直在很远的地方指导人类的发展——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是与美国政府和其他令人生厌的组织相互勾结的产物。

纪录片《科学的故事:权力、证据与激情》(2010)剧照。
简而言之,590号法案仅仅旨在确保平等对待全部现有选项的想法透露出了十足的虚伪:实际上,它明显故意将某些宗教信仰摆在其他信仰之上,因此也恰当地被裁定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明确表述的政教分离原则。尽管如此,世人仅仅从作为一种良好的科学实践的角度认真对待创世论这种潜在观念,也被证明是一种严重挑衅。在一项进化论者后来会后悔的傲慢法案中,合理科学探究的合法定义在阿肯色州地方法院中得到了恰当的商讨。
法案的专家证词有着大量可靠来源,其中包括来自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家G.布伦特·达尔林普尔、耶鲁的生物物理学家哈罗德·莫罗维茨、哈佛的进化生物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以及来自安大略省圭尔夫大学的科学哲学家迈克尔·鲁斯等。奥弗顿法官在其总结中裁定: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自由地展开科学探究,但如果他们结论先行,并且不顾调查所得的证据而拒绝改变,那他们就无法恰当地称其所用的方法是科学的。
换句话说,法官裁定好的科学理论是可以证明为错的——即一个好的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这就让大量关于世界本质的具体主张可以被证明为错,如果的确如此,理论就会被修正、完善或者彻底放弃,而有证据支持的替代解释则会得到拥护。这些特征对创世论都不适用。因此,奥弗顿法官和阿肯色州地方法院都认为创世论不是科学。
事情看上去很清楚。我们以科学的严格定义为起点,这个定义不仅直观,而且受到大众和科学共同体的广泛支持。该定义被用于评估创世论的科学依据,但惨遭失败。地球上的生物复杂性由自发创造的行为产生这一观点,并不在正当的科学探索所接受的主张之列。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回应路易斯安那州的类似挑战时,维持了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的判决,可证伪性白纸黑字写在书上。但不知为何,它并未带来些许改观。
创世论并未消失,而且事实上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2004年,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地区的学校董事会通过一项法案,它要求“平等对待”进化论和某种唤作“智能设计论”的东西——后者乃改头换面的创世论,它被精心设计以满足人们对合法科学探究的现有法律理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何我们对科学实践作为开放式批判探究的直观理解(且经由专家敲定并由法院严格应用),却在撤销伪科学教条的一个如此典型的例子上壮烈地失败了?
当然,一种可能性在于,创世论实际上比我们一开始设想的更加科学,其持续存在就证明了,它实际上符合我们对于何谓好的科学理论的直觉信念。另一种可能仅仅在于,创世论者非常擅长重新包装,并且他们特别善于将自己的想法打扮成法律不适用的样子。很可能实际上二者皆有。但我试图提出第三种更加有趣的可能解释,即我们对科学实践的直观理解存在根本缺陷,而且好的科学与可证伪性全然无关。
波普尔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并不奇怪,可证伪性这个观念理应在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案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卡尔·波普尔在思索和阐述这个观念的过程中——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案的专家证词自始至终都引用了波普尔的作——明确提出,可证伪性为我们区别真正的科学实践(值得我们称颂)和伪科学教条(应被抛弃)提供了方法。它是个专门设计的标准,旨在清除那些声名狼藉的主张和毫无价值的理论,它们只能伪装成合法的经验探究。

纪录片《科学的故事:权力、证据与激情》(2010)剧照。
换言之,它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称手的工具。波普尔思想发展的背景在这一点上能为我们提供线索。他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注定要经历极权主义政府的一些最严重的极端行为,同时也要经历现代科学最具开创性的成功经验。这些事件将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然而,在他批判性地重估自己的政治追求的同时,波普尔也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惊人确证感到震撼。
1919年5月的日食期间,亚瑟·爱丁顿成功地观察到了引力场作用下的光线偏折。这个结果殊为惊人,它需要数月的精心准备,还要将大无畏的天文学团队带至非洲西海岸的一个小岛上,以便展开观察。这也是一场非比寻常的冒险——光线偏折是如此荒谬和震古烁今的预测,乃至科学界很多人都直接将其视为爱因斯坦整个方法之不切实际的证据。成功的结果占领了世界各地的新闻头版。爱丁顿将广义相对论置于最严苛的测试之中,而它也经受住了考验。波普尔喜欢讨论的另一个广受欢迎的例子是精神分析——它是垃圾科学(如果真有这种科学的话)的范例——特别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理论,他在维也纳已对这两种理论比较熟知了。
波普尔认为,在二人的理论中,人类行为不可能与之不协调。如果某人没有按照他们的诊断行事,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条件,而只是因为他“拒绝”这样做。在其后来的作品中,波普尔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他写道:我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将孩子推入水中想要将其溺死;而另一个人为了拯救孩子的生命而牺牲。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术语同样轻松地加以解释。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第一个人心情压抑(他身上的一些俄狄浦斯情节),而第二个人达到了升华。根据阿德勒的说法,第一个人饱受自卑感困扰(他可能需要向自己证明他敢于犯下某种罪行),第二个人亦是如此(他需要证明自己敢于拯救孩子)。我想不到任何无法用这两种理论解释的人类行为。正因为它们总是好用,总是得到确证,推崇它们的人才会将这些例子作为支撑这些理论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电影《模仿游戏》(2014)剧照。
我开始意识到,这种表面上的优势实际是其缺点。因此,波普尔对批判性测试的坚持似乎不仅能捕捉到开放式科学实践中令人称羡的方面,还突出了令人鄙夷的伪科学的欺骗特征。此外,它在哲学上也是令人满意的。波普尔的提议简单而具体。因此,这样一个框架理应在与创世论的法律纷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并不奇怪。
虽然波普尔的观点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但公平地讲,他并没有被当代哲学家认真对待。这种情况部分在于学术不可避免地追求时尚,另外还在于,波普尔无可匹敌的失去朋友和疏离同事的能力。对于一个主张开放心态和批判讨论之价值的哲学家而言,波普尔却臭名昭著地对任何批判自己的观点持敌对态度,并要求他自己的学生采纳绝对正统的观点。但波普尔对科学方法的描述也着实存在困难。
强调可测试性和证伪原则是个极端直接而强大的想法,波普尔将其用到了很多不同的问题上。然而,科学实践的实际情况绝少如此直截了当,波普尔将其后期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处理例外、异常和反例等所有困扰这个简练说法的问题上。与所有简单的想法一样,细节决定成败。
创世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一再被证伪
一个好的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仔细研究之后的结果表明,任何科学理论都能在任何相反的证据面前保存下来——当然,前提是我们愿意在信念体系的其他地方做出必要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的主张与尼克松伪造月球登陆的主张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于,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可以在反驳面前永远不倒,但总有一个节点让科学界最终放弃相关理论。
这个事实仅与科学界及其理论态度相关,它与理论本身的性质无关。不幸的是,这种将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与相信它们的科学家的开放心态混为一谈的倾向十分普遍。这明显是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案犯下的错误。正如他的总结中记载的那样,奥弗顿法官裁定,任何在反面证据面前拒绝修改结论的人都不能称其方法为科学的。但这实际上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科学理论的信息。事情很可能在于,创世论者在修改自己珍视的世界观时显得特别顽固。但那是创世论者的错,而非创世论的错。
重要的问题是,生命起源于约6000年前的自发创造这一观点是否可接受经验反驳,而不是其拥护者实际上将这种观点置于所需测试之下的程度。毕竟,如果量子力学前沿问题的研究者在相互冲突的实验面前明显不愿修正自己珍视的假设,那么我们可能会对他缺乏开放心态感到遗憾,但并不会因此将量子力学本身作为一个不科学的事业而加以拒绝。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旦澄清了世人对理论与理论家所作的刻意混淆,我们就会发现,创世论实际上满足了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案中对科学的刻画。

电影《模仿游戏》(2014)剧照。
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假定自发创造论所描述的生命起源故事带有明显缺陷,它无法与化石记录完好吻合,也无法为当今世界所见的生物复杂性提供令人满意的全方位解释。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无一表明创世科学是不可证伪的。相反,创世科学对地球年龄、全球范围洪水的地质影响,以及动物王国中(至少与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过程的预期差不多)所见的相对有限的变异等问题,提出了诸多具体且高度可测的主张。
创世科学的问题不在于它看上去不可证伪,而在于它一再被证伪,预言也尚未被证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世科学是伪科学的无稽之谈。事实上恰好相反。如果真正的科学的唯一标准在于理论的可证伪性,那么,我们似乎必须得出结论说,事实上已经被证伪的理论都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真正的科学。尽管相反的信念广泛存在,但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案的推论——如果严格应用的话——实际上会让创世论的科学地位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都让局面发生了令人不安的转折。
然而,波普尔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进化论实际上是不可证伪的,这个事实让情况越发复杂起来。他经常抱怨这个理论是同义反复的,并且任何证据都可证明与之相符。正如波普尔所言:实际上,“现存物种是适应其环境的”这种说法几乎就是同义反复。事实上,我们对“适应”和“选择”等术语的使用方式意味着,如果物种不适应环境,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例如,我们可以假设进化论通过持续的变异过程和环境压力,预测了持续增加的生物种类,这样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越来越多的物种会随时间的推进而出现。
或者,我们可以假设进化论预测了,生物体中出现的任何复杂性都为其在环境中生存提供了优势。但实际上,这些描述都不属实。如果我们讨论的环境特别严峻——例如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为食物和栖息地展开的严酷斗争——很可能仅有少数不同的生存策略行得通,因而,存活下来的物种之间并无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讨论的环境特别有利——资源丰富且掠食者有限——那么,在没有任何真正的压力的情况下,无用的适应性便可能大量出现。

《生活大爆炸》第十二季(2018)剧照。
简而言之,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可能性都与自然选择机制相容。在其职业生涯后期,波普尔的确捍卫了自己的立场。他承认,进化论的许多理论基础——例如,描述遗传物质突变、重组和遗传的理论——是能够进行严格测试且可证伪的合法科学理论。然而,波普尔继续坚持认为,经由自然选择得以阐述的更广泛的理论框架则是无法测试的假设,因此无法被视为生物复杂性的真正科学解释。
如何区分“真正的科学探究”和“伪科学教条”?
2006年,科学和宗教在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再次相逢。这次的原告是一群忧虑的父母,领头者是塔米·基茨米勒,他们的案子是关于多佛地区学校董事会提出的“平等对待”进化生物学和智能设计论的建议——家长们确信所有校董事会成员一定都不是愤世嫉俗者,也并非肤浅地要重新包装创世论,但某些情况已完全不同。校董事会的伎俩没有唬住人,法官约翰·E.琼斯三世没花多少时间便支持了家长们的诉求,他判决智能设计论仍然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宗教教义,将其包含在高中课程中显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离原则。
然而,就像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的情况一样,智能设计论的科学依据在判决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而基茨米勒诉多佛的案件则对科学提出了十分不同的定义。专家证词再一次来得很高大上,本案中的专家们有来自布朗大学的生物学家肯尼斯·R.米勒,乔治城大学的神学家约翰·霍特,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科学哲学家罗伯特·T.彭诺克,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的哲学家芭芭拉·福利斯特等人。他们整个抛弃了可证伪性概念,从而便于描述更大范围的科学实践。一般而言,好的科学实践致力于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原则——它主张世界受自然过程的支配,而好的科学理论不能诉诸奇迹或其他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世界的运作方式。琼斯法官在其裁决中对此总结道:
对相关记录和可适用的判例法严格审查后,我们发现,虽然智能设计的论证可能属实(本院对此不采取任何立场),但智能设计理论却并非科学……专家证词表明,自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来,科学一直都仅仅致力于寻找自然现象发生的自然原因。
很明显,智能设计论用超自然力量作为自发创造之原因的做法违背了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原则。因此,琼斯法官和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认为,它不是科学。从前述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拒绝用可证伪观念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公平地说,基茨米勒诉多佛案的推断过程如果继续考虑这些因素,则会好得多。
好的科学理论仅用自然原因解释自然现象这种观念乍一看还挺合理,直到我们意识到,只有基于科学理论才谈得上对自然原因的观念有了起码的理解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让我们换个方式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都同意,科学理论用鬼魂或精怪解释地球为何围绕太阳转,或者磁铁为何会吸铁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是不合法的。但我们拒绝鬼魂或精怪作为其背后机制的原因在于,最好的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它们不存在。

电影《粒子狂热》(2013)剧照。
科学本身决定了什么可被算作“自然原因”或“自然现象”。因此,“超自然”不过意味着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既然如此,好的科学理论仅仅诉诸自然原因的说法不过意味着,好的科学理论仅仅诉诸科学本身所谈论的内容。因此,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的观念是毫无意义的——它以最糟糕的方式诉诸不可证伪性,它不过是说好的科学必须恰好是科学的。这个事态着实令人震惊。
科学与宗教的法律争端始于科学的定义,这个定义旨在诋毁创世论,但实际上却质疑了进化论的科学证据。然而,由于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案中的人们似乎都不理解自己说了些什么,因此,错误的标准刚好遭到误用,从而达到了所需的结果。创世论在改头换面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经过修正的科学定义,但它不仅全无意义,而且结果还与原来的定义一样,体现出一开始就该补救的智性欺瞒。
如果对科学的此番推论构成了广泛法律决策的基础,那么,我们一开始很可能想知道,究竟如何区分“真正的科学探究”和“伪科学教条”。但此处也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想要从课堂上清除创世论或智能设计理论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充足的理由选择渐进的进化理论作为生物复杂性的解释,并将其作为持续研究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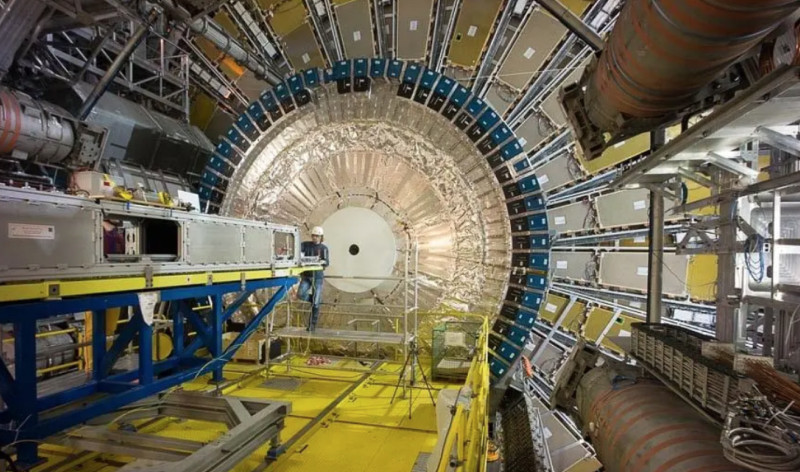
电影《粒子狂热》(2013)剧照。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并不清楚创世论会提出何种研究计划,也不清楚它可能采取何种实验。至少就进化论而言,我们有个潜在的机制解释事物的运作方式,我们也能尝试用它研究世界,并努力改进它。研究DNA及类似的东西可帮助我们治愈疾病。但如果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被一个全能神按照这种方式塑造,那我们就不清楚应该如何努力改善自身的命运(或者即便我们应该如此)。
请注意,这一切都不取决于创世论或进化论是否为真。这是一个支持进化论的实用论据,因为它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有用的框架。这是为课堂上讲授进化论做出的论证,即便最坚定的创世论者也会接受。但不管怎样,这不该是立法解决的问题。它应该是交由讨论和辩论解决的思想市场问题。同样,这也并非建立在小政府或国家干预最小化等政治依附之上的论据。它是个实际的论证,即承认消除一个坏观念的最好办法就是按其自身的方式接纳它,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一旦人自下而上地推动一个观念,它只会越发受欢迎。
然而,通过寻求科学的法律定义,别的观点就可以合法地被驳回,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创世论在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的裁决中是以这种方式被驳回的,而基茨米勒诉多佛校董案中提出的修改后的定义就其目的而言尽管十分明显,但也被驳回了。根据其定义,这个立场主张,对上帝的信仰并非科学,因此人们的意见并不重要。因此,整个辩论都只关乎政治,双方都包含创世论的支持者,也包括了那些试图将其完全排除出公共领域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从这场惨败中汲取两个重要教训。它们并非特别鼓舞人心的教训,但仍有其重要性。首先,简单地说,科学方法既复杂又十分晦涩。法院经由立法确定的各种定义——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科学理论是自然主义的等等——着实糟透了。这些定义并不能与众多好的科学实践范例若合符节,它们常常令糟糕的科学实践范例合法化,至少就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而言,它几乎不具备任何知识内容。
而且,这些定义是由一些实践科学家们提出的。因此,我们应该对任何声称自己确定了科学方法之基本要素的人保持警惕,并对这些主张严加审查。第二个教训在于,我们很容易将人们心中好的科学实践与政治上可取的结果混为一谈。科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社会和政治交往中的仲裁者。毕竟,没有比抨击对手的观点为“非科学的”更能令他们闭嘴的办法了。然而,这个问题又因为上一个问题而加剧,而且似乎无人从一开始就知道“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科学通常被认为是保持理性或者提供合理论据的简要表达——但如此一来,人们心中好的科学实践与政治上更为可取的结果就容易混为一谈了,因为所有人的政治观点都带有他们所认为的合理性。以这种方式,政治的马车往往驾驭了科学之马,而且经常带来不幸的后果。尽管波普尔的方法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他对开放的科学探究精神与民主政府原则的比较却很有说服力。只是我们似乎并未从这个教训中学到什么。
本文选自《被误解的科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英]保罗·迪肯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