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苏敦复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样的朋友能算的上真正的好朋友?我会想起大学班长的说法,“去过他的家,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七八十年代的小城里,父母一辈交了新朋友,总喜欢请到家里吃顿饭,吃不了饭也要请回家喝杯茶,俗称“认认家门”。要好的朋友,喜欢到彼此家里做饭,打牌,甚至接上家用DVD话筒,唱上几曲。平日里晚饭过后,住得相近的朋友,喜欢互相串个门,到对方家里闲坐,聊些有的没的闲话。
今天的我们,交了新朋友总也喜欢约饭,但都会选择商场闹市中新开的或有口碑的餐厅,很熟悉的朋友,会选择卫生质量没什么保障或者吃起来可能会没形象的街边摊,会选择走一走街心公园或者组一局密室逃脱,或者到KTV放歌。更多的时候,欢聚结束,大家就会借着城市灯光下的暗影散去,各自回到家中。
我们已经渐渐不习惯,把家作为社交的场所了。
空间
“家”在居所意义上的私密化
仔细想来,“家”作为个人居所,整体上看属于私人领域,但有趣的是,这个居所中,似乎是理所应当地,一直保留着一块公共区域——“客厅”。客厅,顾名思义就是招待客人所用,是在家这个私人领域中特意预留的社交场所,从古时建筑中的厅堂设置,到现代楼房的居家设计,都不曾摒弃这一公共空间的设置。即便在房屋价格蒸蒸日上的今天,哪怕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仍留有“客厅”这一既定空间的一席之地。
那为何我们渐渐不再习惯将人请进客厅,或者主动去往别人家的客厅进行社交活动了呢?客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套在私人领域中的公共空间,它需要主人先打开私人领域,才能实现它的公共空间功能。于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打开“家”这一私人领域。

《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作者: [美] 那仲良 / [美] 罗启妍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11年11月
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对公共空间的认识存在两个维度的张力。在网络世界中,随着电子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互联技术的多元化,我们在虚拟世界中越来越“亲密”,隐私边界非常模糊。很多不会对身边人吐露的烦恼,觉得隐僻、羞耻的思维与心态,往往会借助虚拟世界倾诉甚至发泄。这种没有边界的自由社交,引发了学界对传播隐私管理的警惕,对社交APP中的隐私边界和隐私规则展开探讨,不断呼吁大家建立“数据化节制”。与此相对的,人们在真实社会中的隐私边界却在不断扩大,隐私意识也不断增强。大到家庭情况、个人收入,小到购买记录、电话号码,都进入我们慎重对待的私隐范畴。家庭居所作为私人领域的性质,也越来越凸显。
现代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居所布局,与中国传统的乡邻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天差地别。犹记得小时候,各家住房一字排开,与领居家的院子,是用稀疏的篱笆隔开的,有时放学回家没带钥匙,就会敲开邻居家的门,从篱笆缝儿里钻回家。听北方的朋友讲胡同、公房、四合院的居住环境,邻里之间更是拥有着大量的公共空间:道路、院场、厨房、卫生间。那时的家庭居所,除了卧房,私密性都不强,这种共享居住环境的状况,使人不会特别注重家的私密属性,对进入这一空间的人要求也就不会太高。
现代城市的房屋设计,基本贯彻了绝对私密的原则。除了楼道里偶尔和面熟的小区业主点头微笑,大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共享带有私人性质的空间。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城市作为一个巨量人群生活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私人的空间,私人空间的合理保障实则有利于城市作为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的凸显,因此这种私密性是必要且合理的。
此外,当下家庭居住房屋的获得方式逐渐固化为商品购买,房屋价格不断上涨,意味着人们获得居所的经济代价不断加大,人们对居所的珍视程度、占有欲望,也会随之加强。此种情形持续时间越长,家作为私人领域的特性就越固定、越突出,人们越习惯家的私人属性,对进入这一领域的“他人”就会挑选得越严格。
时间
成为更宝贵的成本
无论是去往别家串门儿,还是召集朋友至家中招待,都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父母一辈年轻时,作为孩童的我们看着他们一边勤勤恳恳地工作,一边总能有不少闲暇,不知为何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就忙得一塌糊涂。“有空了咱们聚一聚”、“等有时间了一起吃饭吧”、“什么时候有空一起打球”,这些话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既常听到,又常对人说。然而说完之后,能实现的次数却是寥寥。21世纪的都市生活,突然就走向了说不清楚的忙碌中。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许多历史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早在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就超过了50%,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都市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社会逐渐转换为一种新的社会样态,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城市居民普遍感到时间紧迫。
早在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拉里·多西首创“时间病”一词,用于描述“时间不够”、 “时光飞逝”、 “必须加快速度迎头赶上”等现代社会的急迫情景。35年过去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基于时间紧迫的焦虑,并没有随着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所改善,反而愈演愈烈。随着从业人员普遍能力的提高和各行业间竞争的白热化,职场中作为从业者个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加班、学习、培训成为家常便饭,时间成为较之金钱更为宝贵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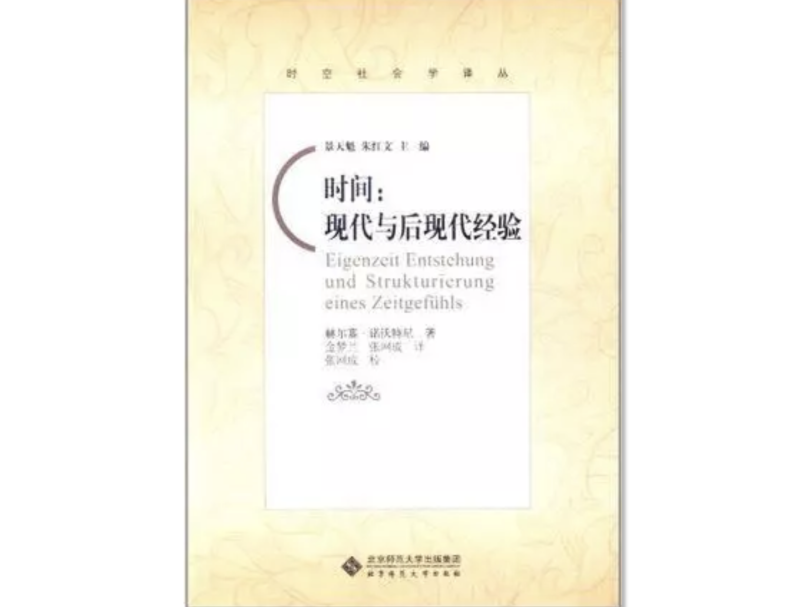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作者: (奥) 诺沃特尼 ,版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工作的忙碌不仅仅是占用时间的问题,更有消耗人们的精力和情绪的问题。2014年,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对北京CBD工作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的被调查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国务院所规定的40小时。” “过劳状态在我国部分知识工作者和体力劳动者中已成常态。”在八九个小时的脑力劳动后,用时下通俗的形容就是“只想躺着”。工作疲惫减损了大多数人外出社交的欲望,也容易令人情绪低落,遑论还要处理家务,一定时期后还要陪伴家人、教导小孩。
除了工作忙碌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城市发展带来的交通时间也越来越长。曾有人戏谑,身处北京,住昌平的和住大兴的谈恋爱,基本就是异地恋。在中小城市中,虽不比北上广,交通时长依旧是常常去往特定地点的重要阻碍。相比于遛弯十分钟能到,坐上公车晃半个小时,足以磨灭“串门儿”这一特定行为的发生欲望。
当忙碌成为生活的主题,交通车程越来越长,城市里的人们开始习惯选择大家的地理中心点展开社交。长时间的工作,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事经济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曾经“下馆子”这一充满贵气表述,现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商圈里吃饭游戏的一条龙供应,既能满足自我娱乐的需求,又能实现朋友相聚的目的,还能省去一个小时买一个小时做一个小时洗的麻烦,成为“忙”与“快”生活节奏下多数人的选择。
心理
社交观念转变与朋友概念泛化
父母辈的社交有一个特点,唯恐不细致,唯恐不详尽。同事朋友间,从家庭成员到来往亲戚乃至三代以外旁系血亲都相互了解得很透彻。而如今我们的社交方式,很多时候唯取共同点,不甚在意交往之人太多的背景。
这一理念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瓦解。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时,提出了在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中,人们身处“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其实,当时无论身处城市还是农村,人员的流动性都很小。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几乎都是世代而居。城市中的工人以厂为家,公职人员也是一个单位、一个岗位干一辈子。当一家人住在你的隔壁,他们大概率就要一辈子和你做邻居;当一个人成为你的同事,他大概率就要一辈子和你一起工作。这样情况下,相互了解的欲望和价值都能最大化,相互了解的可能性也能最大化。故而那时候的社交,“求全”心理很重要。
今时的社会人员流动,似乎无需多言。城市里企业的人员进出之频繁自不必说,就连公职人员也存在大比率的调动、离职,甚至乡邻关系最为稳定的农村地区,基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村民外出务工长期化、村民之间关联市场化、思想观念多元化,也逐渐导致人际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人际关系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期待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更注重“求同”心理,当认识到双方的一些共同点,能够有效沟通一些信息,就足以完成社交行为。

对于聚会场所,我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咖啡馆、ktv等公共空间。时间成本、心理观念是我们选择聚会场所重要的考量因素。
自然,这样的朋友和传统观念中隆重的朋友内涵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动人的心灵鸡汤为我们温情地解释过朋友是什么,情感上深厚的联结,心灵上细腻的碰撞,还有很多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体会与感受。当我们随口说出“噢,一个朋友”的时候,未必真心衡量过“朋友”这个词的分量,或者,只是在使用泛化的“朋友”的语意。若是有情、有义、有信的真正的朋友,相信大多数人的心态会折返回最传统的“求全”中去,我们会希望了解彼此的最全面的情况,最本真的思想,为了能更好地交流,为了能在需要时伸出援手。
如此想来,在私人领域意识逐渐变强、家庭聚会成本不断增加的当下,跨过家的门槛,从普通变得隆重,也变得更有意义。如你仍愿意用私人领域中的公共空间来与人相聚,而对方也愿意不远十数公里赴约,在彼此忙碌中获得的点点闲暇中,胡闹着做出四菜一汤,确是一件美好的事。
串门儿、家中小聚,这件简单的事因为种种原因变得困难起来,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无奈。但如很多好朋友在地域上遭遇分别时,常会说一句,分别未必能常相见,但再见亦如未分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安慰了身处此间社会人们的无奈,我们既已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就培养对待城市的基本心态——现代城市日益需要“城市心性”的调适,同时,珍视每一相聚。
本文刊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2018年1月11日。
作者|苏敦复
编辑|走走 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