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各种需要,人类会对河流进行裁弯取直、疏浚加深等渠道化改造工程。这种工程能降低洪水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并促进航运发展,还能增加可耕种的土地面积。但是,渠道化是一种发挥了工程师自身优势的河流管理实践——河流从复杂的、难以驾驭的、交错的沼泽和河漫滩,被转化成笔直的、线形的、梯形形态——渠道化让河流变得“理性”了。
在渠道化带来优点的同时,也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从摧毁鱼类栖息地到侵蚀河岸,渠道化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因此,河流恢复运动又兴起了。为何恢复河流对生态环境有益?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河流科学与政策教授马丁·道尔多年来一直广泛参与美国的水资源利用与开发、水资源的财政和金融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实践。在道尔的著作《大河与大国》中,他以自身的叙述角度出发,书写了他对美国河流渠道化的反思,并向大家介绍了“恢复河流运动”在美国的发展。
以下内容为马丁·道尔的观察,摘选自《大河与大国》,较原文略有删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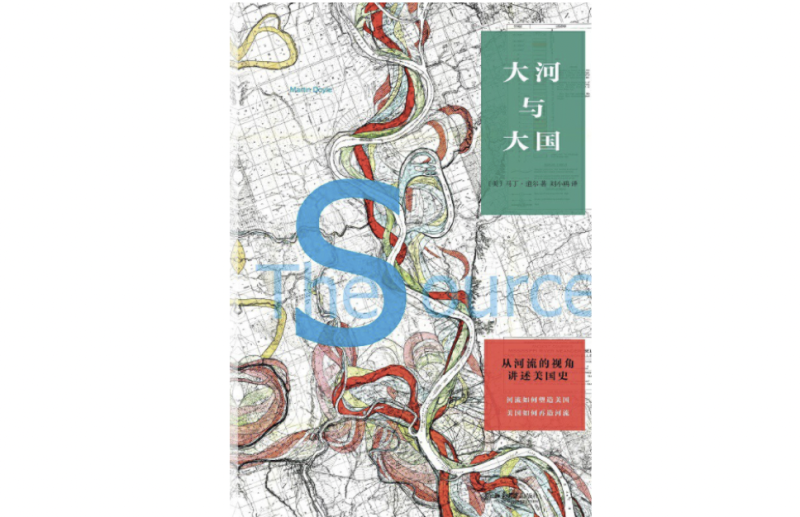
《大河与大国》,[美]马丁·道尔著,刘小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文作者丨[美]马丁·道尔
摘编丨徐悦东
河流会天然弯曲,
裁弯取直不符合自然的进程
多年以来,每当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斯伯勒,坐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把高脚凳上休憩时,目光总会落在县法院旁的一小片土地上。有一条小溪横穿了这片土地,浅浅的溪流刚刚能漫过脚踝,人们可以直接跳过这条小溪。它只比一条水沟宽一点,常年被县里割草机折腾,已经算不上一条河流了,数十年来,这条名为“无名支流1号”的小溪,一直默默无闻地为这个美国小镇输送水流。
但现在,我还是坐在那张高脚凳上,眼前看到的却是一面20英尺高的树墙,由柳树和梧桐组成。穿过这堵墙望去,无名支流1号仍然在流动,不过如今它成了一条蜿蜒的小溪,布满碎石,偶尔传来潺潺声。它已经值得拥有名字了。
如果不考虑神迹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条无名支流的变化有点让人害怕。因为它太完美了。它看上去就是一条河流该有的样子,只是小了点。它有微型瀑布、迷你的深潭和浅滩。河岸边还有微型的石堤,这尺寸简直可以让芭比娃娃和她的男友在这里飞钓了。这条蜿蜒的潺潺小溪在均匀分布的柳树和非自然的瀑布间流淌,小溪的路径出奇地对称,完美地画出一条曲线。
自然创造不出这种对称或简洁的几何图形。溪流能拥有对称的曲流,一定是有人为因素的参与。而这只手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有人说亚当·斯密的手应该有个绿色的大拇指,有人说环保主义者们应该“在绿色中看到绿色”,也有人说应当有“绿色茶党”出现,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这些吹捧绿色的观点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恢复河流成了美国环境经济中蓬勃发展的一部分,讽刺的是,它让吸人眼球但缺乏活力的21世纪碳经济相形见绌,这是河流及推崇河流的人无声地塑造美国经济的又一力证。相反,当美国经济在过去几个世纪经历起伏时,我们如何移动、填满、抽干河流和舍直取弯,以及是否要这么做的想法,都在一同改变。
从范·克莱夫到哈布斯,所有这些恢复工作都是局限于“河道内”的恢复。河道本身被当作了一个固定的框架,所有工作都在框架内完成。大量的石堰和原木坝被建造了起来,但是几乎没有人把河道本身也纳入恢复的项目中。但是在20世纪中期,恢复大型河流的呼声渐高,这些要求提高了改造河流形状本身的可能,也提升了人们改造大型河流的可能。
渠道化确实有用,
但也带来了生态破坏
在马克·吐温的回忆录《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他开篇将密西西比河形容为“这条世界上最弯曲的河流,1 300英里的河流,乌鸦只需要飞675英里”。就像密西西比河上的这种曲流,再加上水流、水深和沉积物的变化,才是生态学家眼中河流具有高度生态多样性的根本原因所在。物理条件的多样性才带来了生物多样性。
然而能让工业化社会接受如此蜿蜒的河流的理由并不多。几十年来,人们原本只是在清除偶尔出现的沙洲或堆积的原木,它们会挡住水流,但20世纪早期的河流工程师将他们的目光放在了别处,他们利用已有的更大规模的疏浚和推土技术,来改造低效的曲流,就像新英格兰的林务员在较小的河流中清除曲流那样。疏浚和推土可以截弯取直,也可以将河道变深和变窄,将水流集中在尽量窄的水道里。

比维奇尔河
除了所有这些,他们还清理了河道中所有杂物,包括原木、树根、树枝和其他所有东西。截弯取直、深挖、缩窄河道和清理河道,所有这些活动一起被归类到了一个笼统的术语之下,即渠道化(channelization),也就是将原本又宽又浅,水流缓慢,又满是漂浮物的河流,变成了又直又深又窄,什么都没有的水沟。
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渠道化在1932年到1955年间发展得最为迅猛,当工程兵团在执行他们新的防洪指令时,他们让密西西比河缩短了150英里。除了密西西比河,在1936年的《防洪法》和1972年的《清洁水法》之间的空档期,11000多英里的河流在工程兵团的工程中被渠道化。同时,土壤保持局也渠道化了21400多英里的河流,通常是在较小河流的源头。全国范围内估计共有约200000英里的河流被渠道化,占美国境内河流的7%。在那些地势低洼的州,河流更容易引发洪水,渠道化的程度更高,比如伊利诺伊州在20世纪中期就有超过26%的河流被渠道化,共计3123英里。而且这些工作并不是推土机离开后就结束的,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维护,因为自然总是会让河流产生曲流,这就需要持续地疏浚不断堆积出的沙洲,并且要在河流自然弯曲的过程中,保护河堤不受侵蚀。
但对于社会来说,所有这些初期工作和后续漫长的维护都是值得的,因为渠道化确实有用。它降低了当地洪水的程度与持续时间,促进了航运,还增加了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或许更微妙的是,渠道化是一种发挥了工程师自身优势的河流管理实践。河流从复杂的、难以驾驭的、交错的沼泽和河漫滩,被转化成笔直的、线形的、梯形形态。渠道化让河流变得“理性”了。
但是在带来优点的同时,渠道化也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从摧毁鱼类栖息地到侵蚀河岸,渠道化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尤其让人警觉的是,渠道化似乎是永久性的。大多数人都认同污染会损害河流的生态环境,但是河流被认为拥有“自净”能力,给河流足够的时间,或者到下游有足够的距离,河流就能分解污染。但是,渠道化却带来了永久性的伤害。在一次致力于解决渠道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渔业研讨会上,就有这么一段话:
当一条河被污染了,它的生态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就像一个人得了严重的急性病或慢性病,河流的行为和功能会被改变,通常是彻底的改变,但完全恢复的希望一直存在。不过当一条河被渠道化后,它就永远地残废了。
当生态学家开始注意到渠道化时,他们才量化这种惊人的效应。在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外的奥比昂河-福科迪尔河水系沿岸,241英里的渠道化减少了95%的水生栖息地和86%的水禽捕食栖息地。在艾奥瓦州的一条河上,渠道化将河流的长度从63英里缩短到了34英里,一项关于这条河流的生态研究,以20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家典型的精辟评论作为结尾:“结果可以清晰地指出,在被渠道化的河段,不利于供垂钓的大型鱼类保持稳定的数量。”同时,这种渠道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看上去似乎是永久性的。从北卡罗来纳州到密苏里州再到爱达华州,在70多年被渠道化的河流中,鱼类群落数量一落千丈。而曾经在河上和河漫滩上生活的哺乳动物与水禽也一去不回。
渠道化的花费也不便宜。美国走出大萧条之后,联邦政府在河流工作上占据的比重就越来越大。渠道化通常是由联邦政府出资,由一系列机构以及改善项目共同赞助。随着对渠道化的批评日益增多,国会也更加注意,导致了1973年一场国会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主题是“联邦政府资助的挖掘机对我们国家的河流做了什么”。在听证会上,负责鱼类、野生动物和公园事务的内政部助理部长陈述道:“河道改善对航运、减轻洪水和农业排水等角度来说是‘改善’,但从可再生资源的角度来看,它们无疑是最具破坏力的水务发展和管理的做法之一。”
渠道化带来的破坏和伤害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过度的,当把环境的代价计算在内后,说渠道化有好处的呼声越来越小。一系列关于渠道化的文章在20世纪70年代刊登出来,它们的标题包括《我们摧毁的河流》《那些曾经的河流》《渠道化:没有出路的捷径》,还有《如何以改进的名义毁灭河流》。
于是钟摆又摆了回来,恢复被渠道化的河流的运动开始了。起初,人们的态度是通过调整施工方法,减少渠道化的影响。联邦公路管理局推荐减少河道缩短的长度,并且重新种植植物。它还推荐在那些被渠道化的河流中,替换或补上一些砾石和大石块,尽量接近渠道化之前河里存在的东西。人们预测将来渠道化还是会继续,但是能以一种伤害较小的方式进行,它的影响能够降低。
人们对于将建造栖息地本身作为渠道化的一部分越来越感兴趣。渠道化继续在进行,但是人们的期望是,纳入栖息地的结构可以纠正许多相关的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工程兵团在被渠道化的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沿岸进行了试验,改变控制河流的结构,从而提高鱼类栖息地。兵团寻找一些方法,在保持渠道化与河道控制的优点的同时,还能恢复鱼类栖息地的一些条件。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沿着河流切割堤防,在河流整治设施上切割出缺口。堤防迫使水流流入统一的河道里,因此,通过策略性地在堤防上开槽,兵团希望在保留驳船交通和防洪的整体功能性的同时,仍然让一些鱼类获得栖息地。在1974年到1980年间,兵团仅在密苏里河沿岸的堤防上就开出了超过1300个槽,除此之外在密西西比河、艾奥瓦河和伊利诺伊河沿岸的堤防上也开了上千个水槽。

比维奇尔河
在规模较小的渠道化的上游支流中,类似的栖息地结构也开始建造出来,其中许多和范·克莱夫与密歇根学派在几十年前推荐的几乎一样。通常情况下,在位于下游的大型河流,以及几十年前经范·克莱夫与哈布斯恢复过的河流中,恢复的重点被放在了河床上的结构上,而河道则被留在那里。渠道化后的笔直形态仍然被认为是现代河流的固定特征。
但对环保人士而言,这些努力就如同用一片创可贴治疗一个心脏骤停的病人一样无济于事。河流需要一场大手术,如果截弯取直和被疏浚的河流在生态上属于垂死状态,而自然弯曲的河流在生态上则很强健,那么舍直取弯就应该能够逆转生态伤害。
相比于范·克莱夫在比维奇尔河的工程,或是CCC所做的努力,在大萧条时期保住了那些没有技能的劳工的工作机会,舍直取弯需要更昂贵的设备和更专业的专家。1974年《河流保护手册》推荐“简单的手工工具、许多力气、汗水再加上心灵手巧,就是参与河流改善项目的所有要求”,并且“河流改善可以独自完成,也可以向童子军和四健会俱乐部寻求帮助”。就像是对范·克莱夫和这种钓鱼俱乐部的回应,作者还问道:“一起钓鱼的好伙伴一起推一块大石头到河流中央,让它变成鱼儿的栖息地,这才会花你多长时间?”如果以在密苏里河下游、萨克拉门托河或佛罗里达州基西米河的规模进行这些工作,需要的就不只是一支童子军或是几个钓鱼伙伴了。这场运动包含了从鳟鱼生活的河流这种小规模工程,到需要挖掘机、推土机和疏浚的大规模工程。这个过去试过错的方法,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更加精心设计的方法。
工程师面对更加复杂的项目,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计划。推土机工作之前还需要设计、预算、蓝图、施工进度和电子表格。更重要的是,工程师需要运用方程进行设计。工程总是按照某种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和工程之间存在鸿沟,这条鸿沟既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鸿沟指的是,工程师希望获得已知的信息和具体情况,尽可能从现有信息中获取精确的信息。科学家则喜欢未知,借助观察和思考尚未被理解的某种现象和过程来获得发现。时间上的鸿沟则是因为基础科学需要走在工程学之前,必须通过观察,确定系统,减少不确定性,直到科学提炼出其本质,也就是一个方程。通过一个方程,工程的能量才能被释放出来。在机动车使用的汽油的发展过程中,热力学和化学的发展必须在化学工程之前。要想重新设计一条河流,需要河流地貌学上的科学发展。这需要的不是对自然河流的直觉概念,而是一整套自然河流的主方程。在20世纪50年代,河流地貌学家正处在推导这些方程的过程中。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河流地貌学都局限在深奥的期刊中那些落满灰尘的书页上,还有象牙塔中的办公室里。地貌学是一门没有归属的学科,它尴尬地处在地质学和地理学之间,而地貌学家的身份则是由一部分科学家、一部分读地图的人和一部分风景解说员组合而成。在迈克尔·翁达杰讲述沙漠地貌学家的书《英国病人》中,地貌学家被描写为“行走在一毫米厚的雾气之下,与用墨水绘制的地图之上,在距离和传奇的纯粹地带,介于自然和小说家之间”。简单地说,他们解读地貌。
利奥波德和沃尔曼提出的方案,
让恢复河流逐渐变成一种产业
在20世纪50年代,当地貌学经历了一场由卢纳·利奥波德带领的量化革命之后,它获得了科学上的“身份”。利奥波德是这批新生地貌学家中的先锋。他最初受训成为一位土木工程师,195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地质学博士学位。相比于像一位地质学家那样将看到的东西画在地图上,或是像一位传统的地貌学家那样描述他所看到东西,利奥波德所接受的折中的教育,让他能够通过代数和微积分来认识河流。沉积物的颗粒不仅仅是在极漫长的时间内形成的地层的一部分,它如同一架正在爬升的飞机上的一颗球。因此利奥波德想要将沉积物颗粒套进方程中,并预测出它们在何时会以何种方式移动。

利奥波德
利奥波德在科学界的名声迅速扩大,当他41岁时,已经是美国地质调查局(U. S. Geolosical Survey)的首席水文学家了。当他在调查局里任职时,他和工程师以及物理学家一同工作,学习分析数据和思考自然世界的新方法。他很快就和那些优秀的年轻同事打成一片,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走遍美国,收集到了大量实地数据。他们利用了利奥波德发明的新定量范式分析了这些数据。地质学和水文工程学的专业报告和学术期刊很快就出现了很多“定量地貌学”的文章。利奥波德自己分析了过去几十年来所有收集到的关于河流的数据,对这一无人涉足的知识领域进行了定量的阐述。当这些新一代的地貌学家测量、绘制并计算着美国的水道时,利奥波德打算着手开始真正改写地貌学,他重新写了一本关于这门学科的书,而这本书将改变世界对河流的认识。
利奥波德在工作上有两个同伴,第一个是约翰·米勒,他是哈佛大学的地质学教授,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利奥波德在落基山脉一同实地考察,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轨迹。不幸的是,米勒在测量新墨西哥州的水土流失时染上了黑死病,在回到剑桥的家里后几天就去世了。剩下半本没有完成的书,利奥波德和另外一位作者一起推进了下去,他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戈登·沃尔曼,他因为一头卷曲而纤细的红发而被人称为“阿红”(Reds)。沃尔曼和利奥波德一样受益于哈佛大学的教育,但利奥波德在中西部和落基山脉中度过了很长时间,沃尔曼则将自己形容为“巴尔的摩人”,他非常熟悉东部的河流与20世纪大西洋沿岸密集的人类足迹。最重要的是,他和利奥波德一样喜欢定量,他们两人很快就成了河流地貌学界首屈一指的作者。
利奥波德和沃尔曼的合作是历史性的,这不仅在于他们对未来河流地貌学的贡献,还在于这也体现了一段历史。卢纳·利奥波德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儿子,后者写过著名的《沙郡年鉴》(1949),这本书优雅地将博物学和哲学相结合。就像蕾切尔·卡森那本《寂静的春天》号召了抵抗污染的运动一样,《沙郡年鉴》则成为荒野和环保运动的圣经。《沙郡年鉴》在奥尔多·利奥波德去世时仍未完成,是卢纳完成了这本书,并将其编订出版。
卢纳·利奥波德和兄弟姐妹的童年都是在威斯康星州索克郡那座著名的“小棚子”里度过的,那里成了环保的圣殿。奥尔多·利奥波德的5个孩子都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环境科学名人排行榜中位居前列。5人中有4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其中三人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卢纳不仅成为院士,还因为在河流领域的工作获得了总统勋章。卢纳的睿智被他作为一个环境活动家的粗犷外表所掩盖了,他离开了威斯康星的小屋,前往怀俄明州牧场隐居,并在那里研究河流和写作。在USGS待了几十年后,利奥波德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尖锐的提问,对粗心的无法容忍,让研究生胆战心惊。

利奥波德在沙郡的小屋
“阿红”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卢纳相反。卢纳钟意牛仔帽和苏格兰威士忌,而“阿红”喜欢领结和马天尼。卢纳在威斯康星州的乡下度过了性格形成的期时,“阿红”儿时则生活在时髦的巴尔的摩街区,在那里,他的父亲阿贝尔·沃尔曼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创立了公共卫生工程和污水工程的学科。巴尔的摩市政府以他父亲的名字重命名了公共事业大厦。在水处理领域,由专业工程学会颁发的最高荣誉依然叫阿贝尔·沃尔曼奖。“阿红”在USGS与利奥波德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回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因为在这个高深的学术领域中的地位,沃尔曼也在科学界出了名,同样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也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包括几十位河流地貌学博士,后来在20世纪末期的河流科学领域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而这些学生都尊敬“阿红”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位温和的圣人。卢纳是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透露着牛仔气息的科学家,而“阿红”则矮小而瘦弱,亲切绅士,和所有人都能随和相处。
但当他们两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合作的这本书为河流科学领域带来了革命,就如同他们的父辈对环保和工程学所做的贡献。他们合作的这本书名叫《地貌学中的河流过程》,这确实是他们父辈令人尊敬的那些工作的一种知识上的延续,是奥尔多的自然科学和阿贝尔的工程科学的复杂混合。这本书,还有卢纳和“阿红”的工作,以及他们学术上的支持者,将地貌学从叙事变成了数学,从描述转化成了预测,从科学家的领域移到了工程师的领域。
这种用新方法带来的思考力量,就是将自然河流转化成了一系列方程式,让河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了。河流的形态可以被分解成图表中的一系列线条。从美国、欧洲甚至是印度无数河流研究中收集到的数据,深潭-浅滩模式从一个理想的特征变成了科学的规则。实际上,利奥波德和沃尔曼指出,他们的数据表明,一整套深潭-浅滩的序列,或者按他们的话说,一整套完整的正弦波形的曲流,会在每6倍河道宽度的距离上发生一次。这就是说,如果一条河是20英尺宽,那一个顺着河跋涉的人就要知道,每走120英尺就会跨过一个深潭-浅滩的序列,这是一个在数学上可预测的节奏。
他们的书中满是这些定量。这些曲流会有多密?河流泛滥的频率是多少?我们应该认为一条河有多宽、多深?人类的直觉被工程的确定性所代替。因为利奥波德和沃尔曼利用了海量的数据,他们似乎是给了读者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工具。
有了这本书,河流恢复运动也改变了原本的方法。它不再是用针对特定鱼类(比如鳟鱼)的需求而设计的特殊结构,恢复的支持者在设计河流的时候,也开始使用河流地貌学中的科学,来模拟自然条件。渠道化的河流被去渠道化,然后舍直取弯,并配备上一些半天然的过去存在的元素,利用利奥波德和沃尔曼提出的方程指导设计。河流恢复不再是钓鱼伙伴的周末爱好,它逐渐成了一种产业。
作者丨[美]马丁·道尔
摘编丨徐悦东
编辑丨何安安 李永博
校对丨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