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印象里,非洲似乎跟落后联系在一起,但是,如今又有很多人看好非洲的发展潜力,认为非洲是全球资本追逐的下一个风口。
那么,非洲会是全球资本追逐的风口吗?在非洲的中国商人和在中国的非洲商人的现状如何?近日,在由天喜文化、甲骨文和天地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被遗忘的角落:世界的非洲与非洲的世界”的讲座中,《穿越非洲两百年》的作者、《一把海贝》的译者郭建龙,《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刘怡,以及《忽左忽右》主播程衍樑一起,讨论了非洲历史和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并对非洲未来发展发表各自的见解。
嘉宾|郭建龙、刘怡、程衍樑
整理|徐悦东
非洲是下一个全球资本追逐的风口吗?
程衍樑:我想问刘怡,你的写作跟国际报道的关联更紧密一点。那在写作意图上,你和郭建龙有什么类似的共同点吗?
刘怡:如果说有相通的地方,那我觉得在科技没有发生决定性革命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从开始到鼎盛、再到平缓——是有一个周期的。大国的周期会长一点,人口和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会相对短一点。
全球资本都在寻找下一个风口。最近大家听说有公司要移到越南去,有人在研究越南或菲律宾的市场潜力。在我印象里,最近5~10年,全球资本所讲的最重要的两个故事就是印度和非洲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不能看产能,我们要看消费能力。在目前的技术条件和全球化的逻辑下,印度和非洲能为世界提供最多的并不是生产的可能性,而是消费的可能性。
目前,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产品是平价的标准化工业制品,就像中国生产的手机、鞋子、衣服。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可以依靠出口LV或跑车等高价产品来让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因为这不符合工业化时代的逻辑。现在的逻辑是要出产可以大规模复制的平价工业品,在世界范围内找到需求,并以此来推动产业链的全球转移和经济全球化的扩散。
这个故事讲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已经讲到了印度和非洲。再过10~20年,也许这个故事还会讲到中东。因为这些地区拥有全球最高的生育率。所以,我们先要确定,哪个地区能够提供大量的消费者,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能让消费者买得起消费品。当然,按照互联网经济的思维,下一步是要贷款给非洲人。凯恩斯在观察世界大战的经济后果后提出,要帮助德国实现复兴,就要贷款给德国人,让德国人买美国的商品。美国的产品卖出去,德国的经济也实现复兴。这个逻辑在最近100年里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20年前,大家都觉得非洲糟得一塌糊涂,没有什么前途。但是,今天大家都在讲,非洲是一个很大的投资风口,可能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引擎。虽然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乐观,但非洲之于世界的意义,可能就处在这两种判断之间。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非洲的地位是在变化的。
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里面写,在没有大型船舶的年代,掌握了马和骆驼的陆上国家,通过争夺一些陆上的地理关隘,就能获得非常大的优势。那时,大家认为海是一个地理障碍。但是,一旦大规模的船只出现之后,海洋不再是障碍。海洋变成了一条条通往全世界所有目的地的通道。在技术条件改变后,不同地理条件和不同地区的重要性也发生改变。目前,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发生彻底逆转,我相信这种变化还会继续出现。
郭建龙:我补充一下刘怡。我是非常赞同他的说法。我写自己的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我也有规划的。我把这称为经济上的梯度转移理论。二战之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从日本和韩国开始。日本的产业转移到韩国,然后转移到中国台湾,接着转移到中国大陆。大家都在考虑,中国大陆的市场慢慢填满之后,下一个梯度是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东南亚。几年前,我问过一些厂商,他们说,东南亚的水池子太小了,很容易填满。

郭建龙
那么,下一个梯度转移的目的地就只能是印度。不管印度有多少问题,它的人口基数和市场是存在的。尽管印度发展得慢,但印度的池子太大,必定会成为世界下一个经济引擎,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除了印度市场外,下一个梯度很可能是非洲。这也是我当初考察非洲的一个目的。
中国的非洲商人与非洲的中国商人
刘怡:我们会把非洲这个历史文化甚至人种差异性都非常大的地区,在日常生活中看成一回事。去年,我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广州待了一个月。广州的朋友可能知道,广州的淘金、小北三院路地区(三元里区块)长期以来是中国从事对非洲贸易的商人区域,那里曾经一度有许多非洲外贸中间商在活动。我发现,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区的非洲商人是不愿意跟其他非洲人相提并论的。
这些非洲商人都是什么文化背景?他们有些人是来自埃及和突尼斯的阿拉伯人,为什么阿拉伯人进入这个地区较早?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不结盟运动中,阿拉伯国家是不结盟运动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角色。那么,来自埃及、突尼斯、阿联酋的阿拉伯商人到了中国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广州的小北路作为他们的聚集区域呢?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新疆和宁夏的商人在小北路的批发市场做生意,新疆和宁夏的商人在小北路一带开了很多餐馆,阿拉伯商人来广州后,发现他们的饮食风俗与阿拉伯人比较接近,阿拉伯人就愿意跟他们住在一块。
后来,新疆和宁夏的商人因为地租上涨搬出去了,这些房屋被阿拉伯商人精准接手。后来,阿拉伯商人也慢慢搬走,取代他们的下一批商人是有着西非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商人。所以,在淘金小北路这一带,基本上都是那些有着西非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商人。反过来,有着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商人可能会住在三元里。虽然这两个地铁站有一两公里的距离,但是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喜好,形成自己的生活圈和聚集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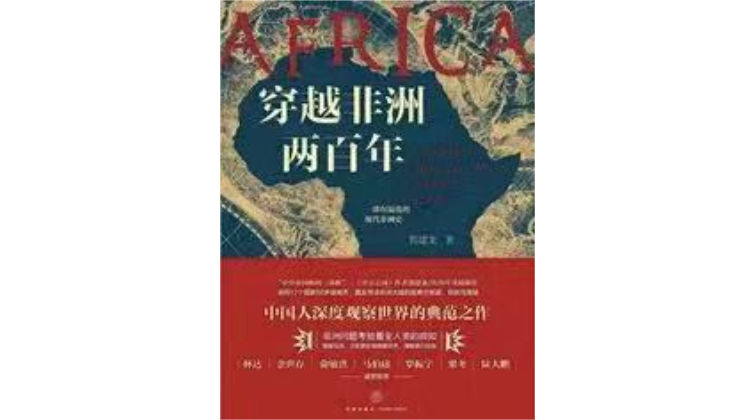
《穿越非洲两百年》,郭建龙 著,天喜文化 | 天地出版社 2020年4月
我问了一些长期跟这些非洲商人做生意的广州的本地人,他们对这种个体商人的小范围批发和转卖活动并无所谓,因为他们的利润率不是很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程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虽然我们利用全球化形成了一个由资本驱动的物流、人力、商品的流通网络,但我们若只安于待在自己的位置,那对于全球大势的认知是不足的。
郭建龙:我在2010年的时候也去过广州小北那一带看过,那时正好是非洲黑人在广州的高峰期。那一片的非洲人非常多,他们根据自己的来源国形成了自己的网络。比如,尼日利亚商人来到广州后,他们就会投靠自己同胞在附近买的房子,然后开始采购,采购完坐飞机离开,过几个月再来一次。通过这种方式,尼日利亚或者刚果(金)等很乱的地方,都会有很多人到中国做贸易。
在中国任何一个开放繁荣的时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港口城市做对外贸易,这些城市都会有一批外国人存在。外国人社区在中国的兴盛程度往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假如外国人的社区衰落了,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
程衍樑:关于郭老师这段思考,刘怡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刘怡:我在2019年在尼日利亚跑了三四个主要地区后才发现,其实华人跟非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可能觉得,中国人跟非洲人打交道基本要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但是,我在尼日利亚看到,华人资本最早跟尼日利亚发生关系是在1950年代后期。
在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短暂春天后,一批搞纺织业的江浙的企业家在1949年之后到了香港。然后,他们在香港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香港的人口规模比较小。尼日利亚在1950年代独立之后是英联邦成员国,它的银行体系跟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体系是互通的。所以,1950年代初期,像江苏的纺织大王刘国钧的女婿就带着纺织工业的资本从上海去到香港,再从香港去到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他们投资建设搪瓷工厂。因为当时搪瓷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搪瓷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当时从香港或中国台湾去到尼日利亚做投资的中国商人,被尼日利亚称为四大家族——当时主要有4个中国家族在那投资办厂。他们还投资搞纺织厂,在当地做建材生意,参与房地产项目。在1950年代开始,华人资本就跟尼日利亚产生了关联。后来,1990年代后,就有个体商人去尼日利亚做外贸。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海外创业者也都去非洲发展了。
我们跟世界的关联和互通的程度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历史要长得多,程度也要深得多。另外,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理论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的经济学者赤松要(Akamatsu)提出的“雁行理论”。根据“雁行理论”,哪怕是像非洲这种被认为相对边缘化的落后地区,在这种全球的产业链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一直扮演着某种角色。

刘怡
我从尼日利亚回来之后,我介绍了一个采访对象给程衍樑。他是跟在我们认知里到非洲去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在美国大学读了商学院,读完之后归国与搞互联网的这帮人一起工作。在他把规则摸清楚了之后,他在中国找到投资人,让他到非洲搞互联网创业。他们的这种模式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我们基本上开始试图去模仿华尔街的模式了。
以前跑到非洲去做生意的华人,有很多人是做传统小商品生意的。尼日利亚有一个中国商贸城,开在一个高速公路的旁边,远远看上去像长城一样,还是鲜红色的,商贸城里有一个很大的绿色的门——这是整个西非最大的中国商贸城。商贸城里卖的都是非常传统小商品。很多人在里面租一个仓库,前面租有门市,商人将商品分销给尼日利亚的各个城市。分销商品利润很低,但这种群体还是存在的。打点这些店面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来自浙江或者福建的商人,他们也不太会外语。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与此同时,我还碰到了许多不到30岁的小伙子,他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们自己来非洲创业,其中包括银行业的人士,他们在那建了尼日利亚本地最大的商业银行。如今出海闯荡,搞互联网创业的中国人,正在试图把在中国成功的一些商业模式移植过去。当然,移植的成果有好有坏。

《一把海贝》,[英]托比·格林 著,郭建龙 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12月
非洲国界的随意性非常强,
衍生出了许多问题
程衍樑:我们发现,非洲国家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欧洲国家的国际秩序很不一样,非洲国家内政和外交的连带性是非常强的,这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吗?这种现象现在还会有吗?
郭建龙:我觉得这个现状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存在的。在欧洲的国王时代,西班牙王位战争就可以变成全欧洲的战争,其实非洲也一样,因为他们的传统上的部落界限在殖民时期被殖民者彻底打乱了,他们现在的国界不是由他们自己确立的。他们现在的国界有非常强烈的随意性。比如,最复杂的地方是刚果盆地。刚果盆地以前并没有成为过一个国家。
在比利时人去刚果之前,刚果盆地是非洲最复杂的区域,那地方有成百上千个部落。在比利时人去了之后,比利时人用一种强行且高压的方式把它们强行捏合起来。在比利时人走了之后,刚果的离心力实在太大。这些部落本身不见得愿意作为一个国家一起存在。所以,刚果存在着很强烈的离心力。要克服这种离心力,就必须用更高压的手段进行捏合,直到大家习惯为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刚果还会分裂。
而且,刚果盆地可以说是整个非洲资源最富裕的地方,这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觊觎,这时就很自然地产生分裂现象。非洲的很多国家都处于捏合的过程中,而这样的捏合,又是前面各种各样的分割与合并产生的必然结果。所以,非洲还处于凝结的时间内。未来可能有些非常国家会分裂,有些非常国家会打仗。但是,有一些地方已经足够稳定了。
刘怡:我们今天处理国际上的边界变迁其实有一个通行的原则,即便不是强制性的:1977年的《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了一个总括性的目标——除非一国内部发生政治分裂和重新建构出一个新的国家,否则在原则上,国际社会不接受一国单方面提出的变更国界和版图的要求。
这个宣言当时主要是为了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亚洲所造成的一系列版图变迁。坦白讲,这种版图变迁不一定是基于公平或公正原则的。当初希特勒提出的“领土复归”的概念,这是基于历史上的人群和语言所覆盖范围确定的概念:假如那个地方现在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或邻国的一部分,希特勒就希望德国跟这个地区进行合并。希特勒认为,这不是吞并,而是让他们回到所属的人种或文化圈里面去。现在,我们杜绝了这种以复归为名的领土吞并行为。
但如今我们看非洲的版图,大家会发现,非洲国家里有很多很直的国界。这种国界基本上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殖民主义在欧洲最昌盛的年代里,像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国划出来的。当时,为了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确立势力范围,这些国家随便画线。所以,在这条线的两边,很可能生活着同一个部落。
非洲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撒哈拉以南萨赫勒地区的游牧部落在今天还依靠季节性的放牧为生,他们每年会像东非大草原的动物一样进行季节性迁徙。萨赫勒地区的游牧部落会赶着他们的羊,越过国界到另一个地方去吃草。这种现象到今天为止还存在。

萨赫勒地区在非洲的位置图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够用一条很直的国界来解决问题。今天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人,但是普什图人只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4%。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国界线是1897年英国划分的杜兰德线。实际上,在杜兰德线的东边,在今天的巴基斯坦的范围之内,还存在为数非常多的普什图人,巴基斯坦现在的总理伊姆兰汗就是普什图族。是不是要把整个南亚范围内的普什图人都整合进一个国家?这在20世纪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去年年底在《忽左忽右》上聊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都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阿盟国家之间的公民出入境和就业有一些便利政策,但是民族国家的雏形到今天基本还没建立起来。我在叙利亚北部采访的时候发现,虽然库尔德人的民族国家化只有100年左右,但是土耳其库尔德人、伊拉克库尔德人乃至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对于全球范围内其他库尔德人的看法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在非洲,如果两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不同,也会导致同一个种族或者同一个部落,在不同的国家里产生差异。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嘉宾:郭建龙、刘怡、程衍樑;整理:徐悦东;编辑:申婵;校对:陈荻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