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巴尔蒂斯痴情于描绘青春期少女的躯体,他的画作在广受推崇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许多评论家在画面中解读出一种潜意识下的情色幻想。但在巴尔蒂斯本人看来,从童年蜕变到青春期的时光,蕴含了所有关于世界的奥秘,画下她们,不是情色,而是祈祷,是寻求存在的意义。
这可能也是为何巴尔蒂斯生前唯一一本回忆录,中文译名取为《向着少女与光》。巴尔蒂斯生前低调而神秘,他认为画家的画作,就是对其思想与生命的最佳坦露。但在生命最后几年,他邀请了传记作家、艺术史学者阿兰·维尔龚德莱为自己辑录下对漫长人生的回忆与反思。阿兰·维尔龚德莱与巴尔蒂斯的谈话持续了近两年,在这些对话中,尽管巴尔蒂斯对自己充满争议的经历(例如与侄女弗雷德里克的同居关系、小儿子的自杀)有所回避,却仍显得坦诚、真挚。
本文是阿兰·维尔龚德莱为这本回忆录撰写的前言。他讲述了自己与巴尔蒂斯毕生难忘的初次会面、长达两年的奇妙合作以及他对巴尔蒂斯艺术观念的理解与阐释。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自《向着少女与光:巴尔蒂斯回忆录》一书。文中图片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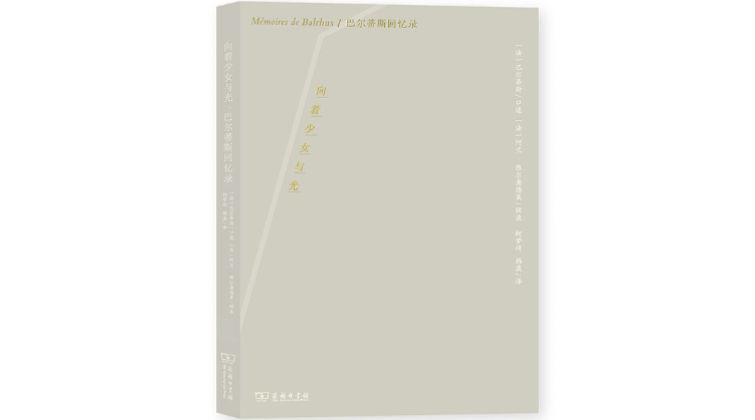
《向着少女与光:巴尔蒂斯回忆录》,作者:[法] 巴尔蒂斯 / [法] 阿兰·维尔龚德莱,译者:柯梦琦 / 韩波,版本:纸上造物丨商务印书馆 2021年2月
原作者丨[法] 巴尔蒂斯 / [法] 阿兰·维尔龚德莱
摘编丨肖舒妍
巴尔蒂斯的一生横贯整个世纪。我们读他的《回忆录》,应该把它当作他的遗言来读。这是他走到生命尽头说的话。这是他屏住气,低吟出来的话,他的气息摇摆不定,渐渐暗淡,但却充满了对年轻时代完好无损的回忆,似乎这回忆又重新给予其生命,让他重新焕发活力。
《回忆录》历时两年写就,在这当中,巴尔蒂斯吐露了许多以往很少谈及的往事,包括那些让他高兴开怀的境遇。他希望我们把这些看作生活的一课,这是一位在思考的画家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正如佩吉所说,“只有传统才具有革命性”,并且具有绝对的现代性。

画家巴尔蒂斯,由摄影师罗密士·迪恩拍摄于1956年。
一
我第一次与巴尔蒂斯和他的妻子节子见面,是在罗西涅尔的木屋里。那时我就知道,我们将一起完成的这部作品将是独一无二的。巴尔蒂斯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他说话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嘶哑而结巴,几乎不可能将过去的这个世纪讲述出来,也无法清晰而富有条理地回顾他的一生,并得到佐证。然而,正如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说:“去吧,到沉默中去,一切都在那里重逢。”在我动笔时,事情就这样慢慢地构建完成。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话说,是聆听私密的歌声,这声音无可琢磨,无所形状,却如“巨大的记忆大厦”持久挺立。
巴尔蒂斯的一生就将在罗西涅尔的木屋完成。在这里,巴尔蒂斯决定在度过这一生之后,将他虔诚而小心翼翼保护的生命回忆,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世人。为什么他的想法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巴尔蒂斯在与我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了其中的缘由。首先,在生命走到尽头,即将慢慢熄灭之际,回忆过去是抗击死亡、追寻他讴歌的生命的一种方式。他不把生命看作一种特权,而是看作上帝的礼物。他每天都想感谢上帝。
因此,讲述和倾诉是继续生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继续他的工作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原因
则更出乎意料。他发现,1993 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约翰·保罗二世周围。我在罗马、克拉科夫以及世界许多地方,对教皇做了多次采访,最终撰写出这位杰出教皇的传记,后来又写了一本关于他的童年的书。知道我是约翰·保罗二世的传记作者,这对巴尔蒂斯来说是一种保证,这样我才得以与他一起工作。他在美第奇别墅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变得十分虔诚,经常到梵蒂冈看望他的波兰同胞。
背景、环境以及项目本身,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巴尔蒂斯便可以开始这浪漫的回溯,穿
越回时光,讲述他生命的长长的故事。直到这时,这个故事他都没有向别人讲起过。我说过,背景是一间木屋,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木屋,像一座隐匿在高山中的东方寺庙,有点吴哥窟的感觉。木屋坐落在山谷中,曾经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家旅馆。屋顶由长而宽的石板铺成,就像贝居安女修会修女戴的帽子,旁边是一个小谷仓,谷仓上面长满了爬山虎,墙面用石灰刷成白色,搭配绿色的木筋,颜色舒适。这曾是主人的工作室。屋内,大型画布在滚动托架上循环滑动,如同一个个神圣历史的无声见证者,在封闭的空间里自娱自乐,因为除了大师夫人和他的孩子,以及极少数的宾客朋友,没有人能进到这里。在谷仓旁边毗连的土地上,有一座俄罗斯枞木屋式,或者也可以说是蒂罗尔(Tyrol)地区风格的马场。马场建得像一个市集,颜色艳丽,诗意地隐藏在山间风景之中,山上牛群的铃铛不停地丁零作响。开往格斯塔德(Gstaad)的小火车从山下经过,总在同一个转弯口呼啸而过,继而消失在森林之中。

巴尔蒂斯曾经居住的瑞士小镇罗西涅尔,图片来源:https://www.wikiwand.com/zh-cn/%E7%BD%97%E8%A5%BF%E5%B0%BC%E8%80%B6%E5%B0%94
火车的轰鸣声就像在抱怨什么,但却一点不令人受惊。相反,这声音让人感到安心,让人欣慰,与莫扎特的音乐混在一起。屋子的主人总爱面对着阿尔卑斯山,平躺在长椅上,不知疲倦地听莫扎特。以前木屋还是小旅馆的时候,歌德和雨果都曾到访过这里。屋子有很多房间,上百扇窗户。外墙上刻有感化人心的语录,提醒着到这里来的人们,无论他们现在的生活多么优渥,总有一天会归为尘土,同时呼吁人们祈祷或冥想,这让这个地方显得有些野性,同时又追寻宗教的慰藉。有时候,透过小格子大窗户,我们会看到一只猫探出头来。这是漂亮的波斯猫米簇1(Mitsou 1)或者安哥拉猫米簇2(Mitsou 2)高贵冷漠地看着来客。后来我才知道,这两只猫经常去洛桑参加一些选美比赛。
屋内的家具是古斯塔夫风格的金色木头制品,一个 18 世纪的陶炉位于饭厅中央,冬日里
会点上火,墙上挂着巴尔蒂斯的几幅画,包括《阅读的科莱特》( Colette lisant )、《猫王》( Le Roi des Chats )、《伏康斯卡公主》( La princesse Wolkonska )……细木柜上摆着一座贾科梅蒂的半身像,几个手持琴弓的猫摆件演奏着音乐,或者静止不动,穿着传统和服的日本小雕像点缀着硕大的窗户。
一队菲律宾女佣穿梭在走廊、厨房、洗衣房和房间中,给猫、达尔马提亚狗和鸟喂食。这
里的鸟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每天对着装有栅栏的窗户歌唱,就像来自东方的俘虏一样。
巴尔蒂斯和伯爵夫人节子(巴尔蒂斯曾是贵族)独自住在这里,他们两人都会作画或沉思。他们习惯在下午五点喝茶,晚上有时会通过巨型电视屏幕看一部屋主喜欢的西部片。午睡时,巴尔蒂斯躺在长椅上,靠近朝南宽阔的落地窗,听着《费加罗的婚礼》或《魔笛》入睡。正是在这种幸福而波澜不惊的和谐中,巴尔蒂斯,这位20 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画家的生活缓缓展开。
现在的工作是追溯过去的历史,保持前后的连贯性,重拾不断遗忘的记忆,然后将选择和保留下来的记忆公布在即将出版的书中。这本书具有持续存在的价值,一种暂时的永恒。我们只保留还剩下的这些记忆,正是这些东西成就并塑造了一个永远的存在。
二
当我们的工作开始时,巴尔蒂斯就提醒我,这将是一本私密的书,是关于绘画的感悟。里面提到的人都值得被书写、被了解,这是他的朋友马尔罗式的“反回忆录”。巴尔蒂斯经常引用马尔罗的话,但马尔罗本人则不希望走进这种“一堆悲惨小秘密”的游戏中来。因此,对这一生的回顾并非建立在隐秘问题的基础之上,比如:他是否真的有贵族头衔;里尔克与巴尔蒂斯母亲巴拉汀( Baladine )和她的儿子们的真实关系如何;作为父亲,他扮演什么角色;他对安托瓦妮特·德·瓦特维尔的感情为什么最终导致他想自杀;缪斯女神赫莲娜·阿纳维(Hélène Anavi)对他的真正影响;他与侄女弗雷德里克(Frédérique)的真正关系,他们曾在沙西(Chassy)同居,在出田节子来到罗马的法兰西学院之前,弗雷德里克甚至是他家里的女主人;他的小儿子之死,那天阳光明媚,悲剧就发生在著名的土耳其房间旁边;他与儿子们僵持的关系,以及他母亲巴拉汀的犹太人身份,等等。

画家巴尔蒂斯与其侄女弗雷德里克(Frédérique),由摄影师罗密士·迪恩拍摄于1956年。
巴尔蒂斯确定了工作会面的原则。我同意他的决定,毕竟,他不想要的东西,我很乐意接受。我认为,传记作者的艺术并不在于找出生活中片面的丑闻,或过于隐私的逸闻,而是以杜拉斯式的方法,存在于令人眩晕的旋涡中,存在于难以辨认的事物中。
因此,巴尔蒂斯对生命的回顾是在一次次偶然的接触和一张张相互关联的网络与桥梁中完成的。我们按照他的节奏,通过他疲劳的入口,经过他闪电般爆发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得以进入其中。有时,夜幕降临在巴尔蒂斯的房间里,床头灯发出昏暗的光,闪烁不定地落在一堆堆的书上,落在他挂在床头的念珠上,落在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上,也落在他床上那堆毛毯、被子和垫子上。有时,伯爵夫人节子坐在我们身边,握着他的手说了一个字或者一句话,便能让沉睡的往事苏醒。她是带领巴尔蒂斯回忆的线索,是他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纽带。
居住在此之人具有的非凡灵性是第一件让我惊讶的事。“画画就是祈祷。”巴尔蒂斯常说。实际上,我们之间许多次交流便是围绕这一点展开。巴尔蒂斯坚持这一点,即里尔克所谓的“敞开”。他说,上帝在地球上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如果不先把这些东西在画布上重现,那就是极大的忘恩负义。绘画就是去完成,是“表达世界而不是表达自我”,是表达敬意。从中我很快明白,为什么他与阿尔贝·加缪或博纳尔(Bonnard)能产生共鸣,以及他绘画中的献祭主题……就这样,我们一步步地走进这片信仰的深林中,回到他的童年,回到他父母还未离异时的甜蜜,回到他的纯真年代。父母的突如其来的离异加剧了他童年的脆弱与敏感,但却由艺术填满。童年是关于他第一部作品的回忆,这是一本用中国画墨水画就的连环画,讲述的是失去他的猫米簇的故事。这是一只捡来的猫,他十分喜爱,但后来却跑掉消失了。童年同时也是同巴拉汀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在图恩附近的贝阿滕贝格(Beatenberg)长期居住的日子。有一天,巴尔蒂斯躺在床上,咳嗽着站起来,在充满松节油的昏暗作坊里,他那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突然发出了光亮。就好像是绘画,以及作画这一行为,突然带给他光明,带他穿越真实的世界。他对我说:“穿越时光,就在这里,就存在于这种感知力之中……”
三
巴尔蒂斯说话时已经接不上气来,有时甚至连意思都表达不清楚,但只要说出第一个字,他就变得滔滔不绝。然后,突然间,他感到疲倦,就让我离开,把他交给照顾他的中国医生刘医生,并为打断他的讲述道歉。
我们一直待在这个环境里,当他再度回归讲述时,他说:“您看,没有什么是按照时间排序的。年表真是又蠢又没用,追踪生命的足迹,追寻我们做过的事情,毫无用处!”他要我们放点音乐,并且总是莫扎特、舒伯特或者巴赫,尤其是莫扎特,他在阿维尼翁和巴黎时,就经常听莫扎特。他对莫扎特理解得很透彻,他的低沉,他的轻快,以及他欲望的力量。房间或者客厅里萦绕着乐声。夏天的时候,窗户对着山敞开着,音符和轰鸣声混在一起——这是小火车像山谷的丝带一样驶过的声音——爆裂开来,又纷纷落下,就像巴尔蒂斯希望他的绘画也像雨点洒在世界各地一样。他的画是对大自然、对年轻女孩之美、对水果坚实的果肉以及对大山的力量的馈赠。他对我说,他一直想画脸和风景,说实话,这是一回事,因为都是在画世界的血肉而已。但并不是画这世界死去的躯壳,而是充满汁液和生命力的肉质的躯体。这是上帝之美,只需这一个字就能让布勒东、蒙德里安和米罗颤抖不已。在巴尔蒂斯眼里,他们都是叛徒。他更倾向与他那些亲爱的意大利朋友为伍,尤其是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曼特尼亚(Mantegna)和乔托。他还从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沙西、蒙特卡维罗、罗西涅尔、美第奇别墅)汲取了大地的力量,触碰到如加缪所说的“世界跳动的心脏”。加缪在去世前几个月曾给巴尔蒂斯寄过一张明信片和他的书《堕落》,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创造春天的你,献上我的冬天。”
因此,巴尔蒂斯经历过的风景是对世界、对诞生、对人、对上帝和对生命的虔诚。他总是用强有力的笔触来描绘它们,在世界所有景观之间建立或重建无形的联系,尤其是东方景观。从他小时候开始,巴尔蒂斯就对东方景观十分着迷,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让里尔克印象深刻。沙西的景观是法国画中最强有力的一种,用粗线条将现代性的结构与大自然的形式连接起来。

《长凳上的特蕾莎》,巴尔蒂斯。
巴尔蒂斯说,画风景就是画存在的意义,画年轻女孩童年的躯体也是如此。从童年蜕变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充满波澜,这本身就蕴含了所有关于世界的奥秘。画这些姑娘不是色情狂的工作,而是在祈祷,因为画弗雷德里克、科莱特、米凯利纳( Michelina )和所有尚未成形的身体,将她们漫不经心的一面展现出来,没有经过任何修饰,这就是在画天使,画在光线下耀眼的存在。
事情就是这样。我从法国另一边的比利牛斯山来到阿尔卑斯山的山脚,带着无法言说的喜悦与巴尔蒂斯相见。我们的会面持续了两年,他的回忆也讲了两年。作为一个世纪以前的贵族,他最终可能只喜欢喧哗与骚动,附庸风雅与傲慢无礼,这让他觉得回顾自己的时代是一种居高自傲。与此相反,正是有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让他没有成为这样的人,原因并非是出于轻蔑,而是一种同情,对被抛弃者的同情,对在他眼里独一无二事物的同情:童年、自然、古人之美,还有传统。
我就是这样认识巴尔蒂斯的,这是我一生中最美,也是最强烈的一次际遇。看着他画最后一幅画,这种体验无与伦比,这是对人生和人性的一堂大课。
这部《回忆录》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并且翻译还在继续。可以说,巴尔蒂斯带来的悸动仍在搅动着当代艺术,以及他的出格和他的丑闻。巴尔蒂斯并没有将自己的世纪解构,与此相反,他用绘画陪伴着这个世纪,用某种方式赞美它,或者说是赞美了他自己的本质、他内心固有的东西。
这本书于 2001 年出版时,他已经去世几个月了,有少数几个批评家反对他的言论。这些人并不了解巴尔蒂斯的极限裸露和他的年纪,也不明白他的人性。他们匆匆了解的巴尔蒂斯,是他的骄傲自大。他就像于斯曼小说《逆流》(ÀRebours)中的主人翁德塞森特一样,将自己的骄傲高高举起。他们喜欢的,是波德莱尔所说的“让人不悦的贵族艺术”,并止步于此。这些人忘记了巴尔蒂斯年轻时,曾在托斯卡纳小教堂里度过无数的夜晚,在蜡烛昏暗的光亮下,临摹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画家的作品。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很深。他们还忘记了巴尔蒂斯用绘画描绘出了他一生的足迹,而绘画则像一种献祭一样,将他指引到此时此地,也就是写《回忆录》时的境况。他们也忘记了巴尔蒂斯在罗西涅尔隐世木屋里所说的话,远远超越了他们从中塑造出的形象。
巴尔蒂斯放心地在这一时间里说了真话,而真话可能让人一时不悦,但却超越了所有的陈词滥调、偏见成见和唯一想法。真话将官方历史的皮囊一一撕开,因为巴尔蒂斯到这样高龄,在他去世之前,已经无所谓失去和获得了,如果有,那也只是陪伴了他一生的荣光与骄傲:
绘画。
原作者丨[法] 巴尔蒂斯 / [法] 阿兰·维尔龚德莱
摘编丨肖舒妍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