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者于赓哲看来,这一“重口味”的、在当今无疑被视作愚孝的行为之所以一直充满争议,是因为围绕它存在一个悖论:割股奉亲是孝道,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合毁伤也是孝道。传统的孝道是父母可以伤害子女,子女却不得伤害父母,哪怕伤害的仅仅是父母传给自己的血肉。同时,中国古代风行一时的割股奉亲也不仅仅只被当时的人们有医学上的意义,它还在特定的时期成为一种孝道的极端自我标榜,成为孝子们的某种社会资本,用以博取声名和政策的优待。这一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同样不容忽视。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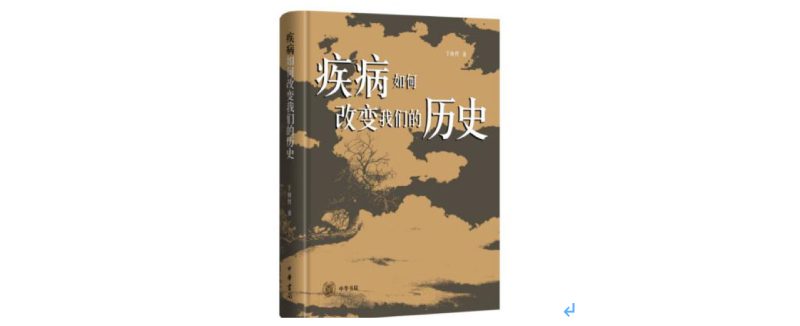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作者: 于赓哲,版本: 中华书局 2021.4
为何古人认为人肉可以治病?
但问题是,这并没有阻止割股奉亲的盛行一时。越是骇人,越是能展现孝心,孝心是需要通过激烈的方式展现出来的。1998年宣化下八里2区出土辽代墓葬1号墓《割股疗亲》图,一老妪做病痛状,一女子持刀正在自割股肉准备下药,其身份应是老妪的女儿或者儿媳。
有人反对,有人推崇,割股奉亲就是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历史长河里。
开篇之前,首先要说清楚一件事——这里说的割股疗亲,与著名的“介子推割股”没有关系。介子推故事是这样的:介子推随公子重耳流亡到卫国,随从偷光了资粮逃走,重耳几乎饿死。介子推把腿上的肉割下一块,与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重耳大受感动。重耳即位后大行封赏,介子推未受封,且不屑与宵小之徒为伍,于是奉母隐居绵山。重耳为了逼他出来,放火烧山,却导致介子推被烧死。但其实,介子推是否曾经割股还是一个疑问。《左传》和《史记》里有介子推随重耳流亡事,却没有割股之事,此事首见于《庄子·盗跖篇》,又见于《韩非子·用人篇》,由于这两篇被历代许多学者断为后人擅增,所以此事实可存疑(包括介子推是否被烧死,也是疑问,《左传》只说“遂隐而死”)。但即便真的有,也只是个案,且与孝道无关。
那么侍奉父母的割股奉亲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极有可能是隋代或者比隋代稍早的时期。原本人们都认为是唐代开元时期陈藏器《本草拾遗》首创割股疗疾,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二《人部》“人肉”条指出:
张杲《医说》言: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闾阎有病此者多割股。按,陈氏之先,已有割股割肝者矣。
李时珍的说法是正确的。比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更早就有了割股奉亲,根据唐开元年间僧德宣撰《隋司徒陈公舍宅造寺碑》记载,隋代晋陵人陈杲仁曾经有过割股疗亲的行为。这似乎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相关记录。
人肉是如何与医疗挂钩的呢?有证据表明,至少在东晋时就已经有僵尸肉可以入药的观念了,刘敬叔《异苑》卷七云:
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
这和后世活人割股当然不同,但反映出当时确实有以人肉入药的“偏方”存在。“僵尸肉入药”的观念其实是某种落后的原始思维模式的残存,这种模式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命名为“互渗律”。布留尔是这样阐释的:“食用一种生物,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与它互渗,与它相通,与它同一……我们知道,某种食人之风即来源于此。”《异苑》文云“僵尸人肉堪为药”,可能反映出这样的一种观念:僵尸历经多年而不腐,古人认为其中一定有某种神秘的物质在起作用,这种物质作用在死人身上可以使尸体不腐,那么作用在活人身上大概也可以使人身不坏,通过吃僵尸肉就可以占有这种神秘物质。
活人肉早期的应用和后世不一样,不是针对所有疾病的,而是被用来治疗结核性疾病。《本草拾遗》原话是“人肉治瘵疾”或者是“人肉疗羸瘵”,“瘵疾”和“羸瘵”就是肺结核。所以说最初人肉入药可能是针对结核性疾病的。《册府元龟》卷一三九《帝王部·旌表》有关于先天年间割股疗亲的事例:“(先天二年,713)孝子王知道母患骨蒸,医云须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许,加五味以进母,母食之便愈,即托他疾卧,不令母知。”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早期割股实例中只有这一则提到了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所谓“骨蒸”恰恰是结核病的另一个称呼。
众所周知,结核病在抗生素类药物诞生之前是一种致命的慢性病,吃肉是治疗方式之一。即如《剑桥医学史》所言:“贫穷是结核病最好的沃土,而充足的高蛋白食谱、不断改善的营养,以及更好的卫生和居住条件则会阻止它的发展。”古代欧洲肺结核患者往往靠食用生肉来补充营养。印度梵文医学经典《医理精华》第8章第9条认为“(对)肺病患者(而言),……鸟肉和野兽肉也是很适合的”,第31章第12条认为用大蒜汁和脂肪或者骨髓相加能使肺病患者强壮起来。唐宋的医书中也不乏此类记载,例如《外台秘要》卷一三引《救急方》“疗骨蒸传尸方”就以皂荚、黑饴糖和拳头大的羊肉块入药,同卷还记载有苏游的见解,他认为应该给患者吃鹿脯肉。《圣济总录》卷九三《骨蒸传尸门》则有以猪肚入药的“猪肚黄连丸”。
可是吃动物肉怎么转变成吃人肉的呢?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灾荒、战乱、赤贫),升斗小民获得牲畜肉类可能比较困难,因此有孝子会自割股肉代替之,这也就是“割股奉亲”首先出现于民间下层的原因。
到了后来,人肉才被人们应用于其他疾病。编纂于宋代的《新唐书》和《南部新书》《册府元龟》已经不知道人肉最初的用处了,只泛泛说人肉可以治病。医学史上,这种药物被逐渐“滥用”的现象并非罕见。
读者或有问:百姓获得一点肉食至于如此困难吗?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对此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郑先生指出食人肉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并且把这种行为分为两大类:求生性食人与习得性食人,认为前者是在饥馑或者战争条件下产生的,后者“是一种食用人体特定部分的风俗化行为”。

宣化下八里2区出土辽代墓葬1号墓《割股疗亲》图
笔者认为“割股疗疾”兼有两者特征。首先,最初的割股疗疾极可能是在战乱或者饥馑情况下出现的,某人在身患瘵疾的尊亲急需肉类之时,在维持日常最低热量的食物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出此下策,属于“求生性食人”。某种机缘之下,尊亲的瘵疾竟然痊愈,也许痊愈的原因与人肉无直接关系(一个人能从自己身上割多少肉呢),但是古人的观念中,总是习惯于把治愈绝症的功劳归于所服用药材中之奇绝者,于是人肉获此“殊荣”,使得这个药方传播开来,成了民间偏方。对于后世割股疗疾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尽管有可能是食物(包括肉食)比较充裕的时代,但他已经不知道割股最初的目的了,只知道这是一个“有效”的秘方,自己的股肉会治愈尊亲的疾病,这样的行为应该归于“习得性食人”。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禁屠也可能导致有人自割身肉,这是有直接证据的。前揭《全唐文》卷九一五僧德宣《隋司徒陈公舍宅造寺碑》:“公(陈杲仁)事后亲,亲病须肉,时属禁屠,肉不可致,公乃割股以充羹。”陈是当地豪族,他之所以割股,当然不是由于贫穷或者饥馑,而是因为当时禁止屠宰牲畜,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以活人肉治病毕竟有悖于儒家伦理,所以只存在于民间医疗活动中,在主流医家那里没有得到承认。现存的隋唐重要医书《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以及官修的《新修本草》里面没有这种内容,唯一一个敢于将其正式记录的就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原因是:陈藏器很“二”。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的作者薛爱华认为:“唐史中没有为陈藏器立传这是对他标新立异的惩罚。”他是一个在当时不入正规医学家法眼的医人。
陈藏器的“药物”可谓光怪陆离、无所不包,例如古镜、钉棺下斧声、枷上铁钉、天子耤田三推犁下土、社坛四角土、市门土、载盐车牛角上土、寡妇床头尘土、富家中庭土、三家洗碗水、猪槽中水、市门众人溺坑中水、自经死绳、故渔网、故缴脚布、产死妇人冢上草、孝子衫襟灰、灵床下鞋履、人血、人肉、人胞、妇人裈裆、人胆、男子阴毛、死人枕、夫衣带等。
可以看出来,陈藏器是个另类医学家,与其说是医学家,不如说更接近巫医。例如“天子耤田三推犁下土”,陈氏说它有“安神定魄强志,入官不惧,利见大官,宜婚市”的效能,“社稷四角土”则有“牧宰临官,自取以涂门户,主盗不入境”的作用,“听人家钉棺下斧声”可以治疗“胬肉”(即“胬肉攀睛”,睑裂部球结膜与角膜上一种赘生组织),“寡妇床头尘土”可以治疗“月耳割疮”(割耳疮)。
不过话说回来,假如没有一种氛围能帮助隋唐人突破传统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合毁伤”的理念,陈藏器也“二”不起来,更不可能有那么多追随者。这种有悖科学和社会伦理的社会风习,与时代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涉及当时的医学思想、外来文化包括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演变、政府对于孝道的鼓励、人民赋役的沉重,等等。可以说,唐朝特有的时代背景使得这个历史怪胎壮大起来。这远非医学本身可以解释的。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美] 薛爱华
为什么说“割股奉亲”存在自我矛盾?
当“割股奉亲”出现时,士大夫们就会碰到难题,一则父母传体受到了毁伤,二则这种毁伤目的在于为父母疗疾尽孝,该如何评价这种行为?既然介子推可以受褒扬,那么割股奉亲者的行为不是也应该受到表彰吗?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士大夫阶层对此反应不一,肯定者、反对者理由似乎都很充足,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的自相矛盾。
士大夫阶层中有很多“割股奉亲”的支持者,例如令狐楚曾云:“纵蜇及肤,口犹难忍。援刀刺股,心岂易安。……天生仁孝,日用元和,忘甚痛于己躯,期有瘳于亲疾,人伦共感,名教所宗。”再例如柳宗元所撰《寿州安丰县孝门铭并序》:“(寿州有李兴割股救父)谨按,兴匹庶贱陋,循习浅下,性非文字所导,生与耨耒为业,而能钟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犹锡瑞物,以表殊异。”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忍受肉体巨大痛苦,是本性中孝心的自然流露,足以感动上天。
而反对者则抓住这些支持者们刻意回避的儒家教条“父母之体不合毁伤”加以阐发,其中最典型的是韩愈。元和年间,京兆鄠县曾经有一个郭姓孝子割股奉亲,朝廷准备进行旌表,韩愈对此大为反感,作《鄠人对》予以抨击:
鄠有以孝为旌门者,乃本其自于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闻其令尹,令尹以闻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门,使勿输赋,以为后劝。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则止于烹粉药石以为是,未闻毁伤支体以为养,在教未闻有如此者,苟不伤于义,则圣贤当先众而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其为不孝得无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当旌门:盖生人之所宜为,曷足为异乎?既以一家为孝,是辨一邑里皆无孝矣;以一身为孝,是辨其祖、父皆无孝矣。然或陷于危难,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乱,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门闾,爵禄其子孙,斯为为劝已,矧非是而希免输者乎?曾不以毁伤为罪、灭绝为忧,不腰于市而已黩于政,况复旌其门?”
韩愈在这里首先指出割股奉亲者毁伤肢体,违背圣人遗训,不孝之甚,然后又暗示这些人是“希免输者”,反映出当时赋役的沉重已经导致许多百姓利用政府的这种褒奖,以一时之痛楚换取未来之安逸。
既然儒家如此自相矛盾,意见纷纭,那么老百姓当然可以各取所需。所以说,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合毁伤”的教条此时已经失灵了。
而且,诸位读者,古人很多行为的背后,其实也是有利益动机的。人的特点就在于此:无论多么高尚的行为,只要有政府的鼓励,就会有矫饰者粉墨登场,就会出现鱼目混珠。
自打割股奉亲这种极端孝道行为出现后,由于其惊世骇俗,所以唐代政府对此大为赞赏,各种奖励措施也来了:首先,旌表门户;其次,蠲免赋税徭役;唐玄宗时期甚至还给割股奉亲的孝子赐官。
对于古代平民来说,赋税倒还在其次,徭役是最沉重的负担,两项皆可减免,而代价无非是一时之痛,何乐而不为?以前就有过靠自残躲避徭役、兵役者,《唐会要》卷三九《议刑轻重》:“自隋季政乱,征役繁多,人不聊生。又自折生体,称为‘福手’ ‘福足’,以避征戍。无赖之徒,尚习未除。”这是种黑色幽默,把为了躲避兵役徭役而致残的手脚称为“福手”“福足”,即便是号称治世的唐太宗贞观时期也没杜绝此类现象,由此引得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七月敕下:“今后自害之人,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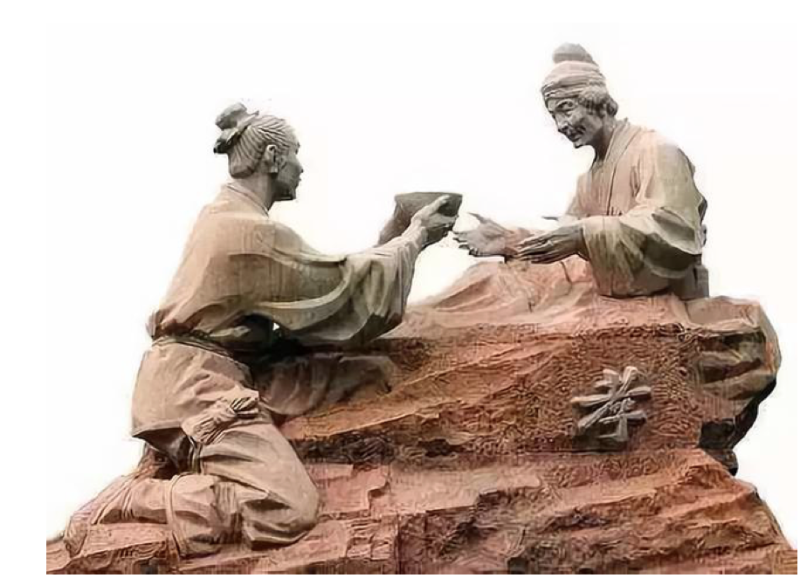
割股奉亲
既然自残手足都可以做到,那么从武则天以后,割股奉亲可以冠冕堂皇受到表彰,正大光明减免赋税,还能落得孝子美名,何乐而不为?于是各种割股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人割肝剜眼以示自己更孝顺(想起了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比惨大赛)。
宝历年间的一件事情从侧面证明了这个现象的存在。宝历二年(826)正月,户部侍郎崔元略上奏:“……其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割股奉亲,比来州府免课役,不由所司。今后请应有此色,敕下后,亦须先牒当司。如不承户部文符,其课役不在免限。”诏从之。可见当时对割股奉亲者蠲免赋役的权力已经由中央下放到州府手中,由此可能出现了伪滥现象,损害了政府利益,使得中央不得不收回该项权力。
但是旌表割股奉亲者的政策并没有因为有反对者而发生改变。晚唐时期此风日甚一日,皮日休《鄙孝议上篇》曾经这样慨叹:
夫人之身者,父母之遗体也,剸己之肉,由父母之肉也。言一不顺色、一不怡情,尚以为不孝,况剸父母之肉哉?……今之愚民,谓己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剸而饲之,大者邀县官之赏,小者市乡党之誉,讹风习习,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执政不以禁。
这个现象在唐灭亡后得到暂时遏止。后梁时“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朱温下令:“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旧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本纪》)朱温之所以要下达这样的命令,估计是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大量百姓以“割股奉亲”为手段逃避征役,于是朱温也顾不得什么孝道了,一举取消了对割股奉亲者的优待。
后唐灭梁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了对割股奉亲者的奖励。后唐自视为唐的继承者,重新提倡孝道、恢复对割股奉亲者的奖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门一开,“割股奉亲”愈发泛滥,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割乳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蠲符不可胜数。”真怀疑在这样蠲符满天飞的情况下,政府是否还有能力保证此事的严肃性,避免出现假冒者。
天成四年(929)四月,程逊曾经上疏说:
臣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乐正子春下堂伤足三月不出而有忧色。民间多有割股上闻天听者,伏以尧代则共推虞舜,孔门则首举曾参,皆以至孝奉亲,不闻割股肉疗疾。或真有怀怙恃之感,报劬劳之恩,孝起因心,痛忘遗体,实行此事,自是人子之常情,不合鼓扇声名,希沾恤赉。伏维陛下道齐覆载,孝治寰区,渐致升平,全除矫妄,乞愿明敕遍下诸州,更有此色之人,不令举奏。所冀真诚者自彰孝感,诈伪者免惑乡闾,咸归朴素之风,永布雍熙之化。(《册府元龟》卷四七五《台省部·奏议六》)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和韩愈的《鄠人对》如出一辙。虽然很中肯,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割股奉亲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种牢固的风习,难以根除了。
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认可这种行为,或至少是睁一眼闭一眼,朱熹就曾经说:“今人割股救亲,其事虽不中节,其心发之甚善,人皆以为美。”(《朱子语类》卷五九《孟子九》)
对于韩愈的《鄠人对》,也有人进行了猛烈抨击。如黄震认为割股奉亲者都是一些缺医少药的小民,其本意在于为父母治病,其孝心足以感动天地,怎么能说这是为了逃避赋役呢?他批评《鄠人对》太过刻薄,《黄氏日抄》卷五九:“剔股以瘳母疾,虽非圣贤之中道,实孝子一念之诚切也,为对鄠人之说者,何忍且薄耶!”他甚至怀疑《鄠人对》不是韩愈所作,并进一步把孝子割股与唐代颜杲卿等忠臣尽忠成仁的举动相提并论。宋朝自建国以来就屡遭外患,士大夫对于“忠”是十分看重的,忠孝本为一体,在这个大前提下,鼓励“孝”是很自然的事情。黄氏的议论就是其中的代表。割股奉亲也就借此继续蔓延。
元代忽必烈政府曾经发布禁止旌表割股奉亲的命令:“至元七年十月,御史台为新城县杜添儿为伊嫡母患病,割股煎汤行孝,旧例合行旌赏,为此公议得上项:割股旌赏体例虽为行孝之一端,止是近代条例,颇与圣人垂戒不敢毁伤父母遗体不同,又恐愚民不知侍养常道,因缘奸弊,以致毁伤肢体,或致性命,又贻父母之忧,……今后遇有割股之人,虽不在禁限,亦不须旌赏,省府准呈仰照验施行。”
明朝洪武时期,已经明令取消了相关奖励,但是割股奉亲者还是大有人在,成为社会痼疾。即便到了西方现代医学全面进入的民国时期,割股奉亲已经被证明在医疗方面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仍然屡禁不止,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渐绝迹。割股之举已经是孝子们表达自己孝心的极致手段,也是社会舆论衡量子女孝顺与否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来,它早已经超出医疗的层面了。
作者|于赓哲
摘编|刘亚光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