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我们打开社交媒体,充斥在热搜榜上的话题大多与善恶有关,比如最近林生斌消费亡妻的事件,还有众多明星出轨传闻等八卦。一方面,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里,道德逐渐变得多元化,另一方面,网上的道德议题经常能引发许多人的义愤和共鸣。网上的讨论或许未能触及善恶更深层次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善恶,存在怎样的差异,又有哪些相似之处?从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善恶意味着什么?技术的进步,又会对人类伦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021年7月9日10:00,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侦探小说作家何家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玮一起对话,直面“灵魂之问”,考察我们的人性与社会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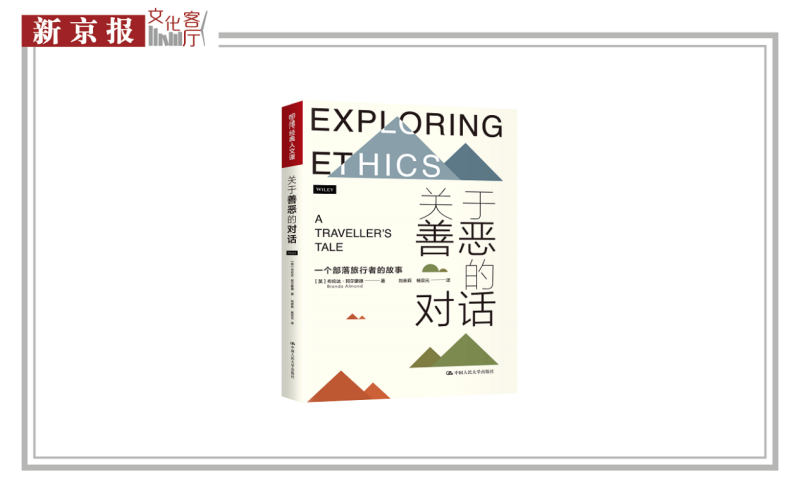
《关于善恶的对话》,[英]布伦达·阿尔蒙德 著,刘余莉、杨宗元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满足个体欲望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
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
刘玮:《关于善恶的对话:一个部落旅行者的故事》的作者是布伦达·阿尔蒙德——一位英国哲学家。她在这本书里面构造了一个场景:她自己出去旅行,然后不小心掉到了一个山谷里,遇到了一群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居民。这些居民跟她有着非常不同的道德和政治观念。之后,她跟这里的居民分别开展了13场对话。
本书涉及了当代道德理论的一些基本主题,比如权利、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生死等。我从头到尾读过一遍,觉得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是一本很有意思又有一定深度的伦理学导论——它构造了场景化、开放性的对话,读起来感觉特别好,可以使我们深入到很多道德问题的根基上去,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
关于善恶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熟悉。每天打开微信、各种APP,看热点的推送,十有八九都是跟道德有关的,比如最近的滴滴下架、林生斌消费亡妻和孩子等事件。为此,我们请来了三位在道德和善恶领域研究都非常有建树的学者,跟大家聊一聊善恶的问题。
这三位学者可以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领域,何怀宏是研究伦理学的,何家弘是研究法学的,周濂是政治哲学方面的专家。我是主持人,我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我想首先请三位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即伦理学、法学、政治哲学的角度,分别谈谈对善恶的不同看法。

何怀宏:我觉得善恶有广义的善恶,也有狭义的善恶。在广义上来说,英文“good”(好)既包含道德含义,也包括非道德含义。它可以是一种价值,是我们追求和喜欢的东西,比如追求卓越或者某种和谐的家庭人伦关系,甚至包括具体的生活品位,也可以说是“好恶”。这跟道德正当、邪恶和规范性的伦理没有多大关系。道德的价值是指那些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和追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善恶”。中文里善恶的含义比较狭窄,基本上指道德价值上的含义而非“好恶”。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近百年来——甚至可能更早——发生了一个巨变:过去,传统社会有比较明确的、主流的、主导的、有共识的善恶观,但在近代以来,这些善恶观被打破了。因为追求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而不是他人给我规定的幸福。既然我们追求平等,我们就应该各有各的追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能一群人主要追求一种价值,另一群人主要追求另外一种价值。
在今天,善恶的观念可能被分解得多元化了。这不光是指非道德的价值,在善恶正邪的问题上,有些人可能还会进一步质疑,现在道德变成相对的。当然,我的观点是捍卫某种共同性。我觉得我们要寻求一个基本的共识作为伦理底线,努力形成或凝聚共识。
何家弘:我是一个法学教师,同时也写小说。其实,我在小说里经常思考人性的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回答善恶的标准问题。法学要探讨人们行为的准则,要给出一个标准,然后根据标准制定有关的规则。在哲学的层面,这是很开放、很超脱的。确实,我们的很多认识是处在灰色地带里,究竟谁是谁非不能简单回答。但是,法律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善恶应该是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的行为标准,不应该是个人的行为标准。
一个独立的个人满足自身的欲望就是善——就像我们说善待自己,这种善并不能作为一个社会和群体的标准。一般来说,利他是善,利群是善,利己不一定是恶,但不是善。这个标准还是太过抽象。不同的群体对善和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群体有自身的利益,他们是会互相冲突的。
除了法学家和小说家之外,我还在国际足联担任道德委员会的委员。有人会问,足球有道德吗?足球本身不是一种很高尚的体育运动,若太讲道德可能就没法玩了。但是,就像何怀宏说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足球里的一些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在绿茵场上是被允许的,但这需要底线。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其实不负责管运动员是否踢假球、裁判员究竟有没有吹黑哨——那是纪律委员会要做的事。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反腐败——查办国际足联和各国足协官员的道德问题。

何家弘
周濂:我研究政治哲学,同时也做伦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何怀宏说,”好“(good)就是我们追求喜欢的东西。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第一句是“这件事情是好的,所以我想要去做它”,第二句是“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应该去做它”。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了很强大的内驱力。我有欲望去实现它,但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反过来说,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对(正当)与好(善)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它们是伦理学中很重要的一对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伦理学跟政治哲学的一个概念区分。伦理学追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过上一种幸福的人生?”这里的关键词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以及“幸福”。政治哲学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这里的关键词是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而且首先追问的是“对”或者“正当”,而不是“好”或者“幸福”。政治哲学要在规范性的意义上追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于是,这就出现了幸福与正义之间的张力。我个人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幸福,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当然,我们是谁?我们因为什么而成为我们?这又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
接着何怀宏的观点往下说,过去100多年来塑造中国和西方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何老师认为是平等。我认同这个看法。回想一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有一种思潮:我们应该追求政治上的平等——每一个个体,无论贵贱贫富,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表达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想法,去伸张个体的利益。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思潮则追求经济意义上的平等。当然,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平等最终还是会反映为政治上的平等。进一步来说,在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过程中,最终会导致在整个社会观念上,我们把追求平等当作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和价值。
今天我们发现,平等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毛细血管当中。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都在追求更进一步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和阶级平等。但是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托克维尔早在180年前就针对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提出了自己的忧思。他认为,在一个等级制度深入人心的社会,再大的平等人们也会视而不见。反之,在一个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再小的不平等人们也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毋庸置疑,平等是一个好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处于一种追求平等的加速过程中,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我想接着何家弘的话说一句,他刚才谈到善恶的标准,对于伦理学和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可以相对安心地驻留在“非善非恶”或“亦善亦恶”的灰色地带,进行所谓的哲学上的玄思,让对话和思考无尽地进行下去。但对于法学工作者和实践来说,他们必须要做出善恶的判断。这种当下的判断是非常艰难的一种实践。
面对犯罪行为,
我们要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刘玮:何家弘老师能不能接着周濂老师谈到的话题说一说:法学工作者对于善恶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是道德的底线吗,就像何怀宏老师提到的底线伦理?
何家弘:法律不是一个很高的社会性行为标准。我们平常说,“法眼看人低”。从法律来讲,这里的“人”都是社会上道德不是特高尚的人,所以我们才需要制定这些规则。如果一个社会中,个体成员都是非常高尚的,那我们大概不需要法律。我们有了伦理的导向,人们会把社会关系处理得很好。但在现实的案件中,我有时候却会很困惑。
我举一个例子,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谈过,十几年前河南有一个农村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很辛苦。后来,哥哥学习很好,上了高中,毕业后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弟弟的学习不是太好,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但是他很顾家,所以他就回家干活,挣钱养家。哥哥考上名牌大学,这是村里人的骄傲,家里人也高兴。但是,他们家出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要交9000块钱的学费。家里没这些钱,母亲说去借。哥哥还有点犹豫说,要不然我还是回家干活挣钱得了。弟弟说,你去好好上学读书,这个钱我来挣。
哥哥去上学,弟弟就到县城的一家公司做勤杂工。有一天傍晚快下班的时候,一个业务员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把一个信封放到抽屉里就走了。弟弟当时感觉信封里有钱,等办公室里没有人了,他禁不住诱惑就打开看看。结果,他看到厚厚的一沓钱,经过再三考虑后,他把钱给拿走了。第二天早上,他跟领导说,我家里有事,要请几天假。当然,公司很快就知道了这事并报案了。在公安局介入后,警察发现他有重大嫌疑,但人去向不明,侦查人员分析,他可能去上海找他哥哥了。所以公安就到了上海。他哥哥开始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公安机关人员对他进行了说服,学校领导也给他做工作,哥哥后来就讲,弟弟确实给他送了9000块钱,说是借的。在哥哥的帮助下,公安把他弟弟抓捕归案。
后来,我看法庭审判的画面非常有感触,弟弟低头不语,哥哥呆若木鸡,母亲痛哭流涕。为什么会这样?弟弟的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哥哥的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我们法律应该怎么来做出判断?
何怀宏:何家弘给出了一个现实的难题。很凑巧,这个例子正好是我在《伦理学是什么》里面引用过的,我做过一些分析,曾借此来引出道德的概念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我对现代伦理的主张更接近于法律和政治哲学的内容。我的感觉是,道德形而上学容易趋于高调,但可能离现实比较远。
我比较认同伦理规范是接近于最基本的法律规范的,但是法律和道德也还有些不一样。在弟弟偷钱为哥哥上大学这事上,我们会在道德上给予弟弟相当的同情;但从法律上来说,盗窃就是盗窃。这两者之间是有张力的。
我们经常说,各大宗教的基本戒律是一样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和道德规范也是一样的,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强暴、不可盗窃和欺诈等。但是,道德评价和法律规范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道德确实会考虑人和人的处境、社会和制度的环境。为什么哥哥上不了大学?这是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的。道德规范应该是更广泛的。道德不仅仅针对行为,也包括动机和背后的环境。
当然,它们起作用的手段也不一样。法律依据的是刑罪相应——它主要是靠硬邦邦的规则,其后面是合法的暴力机器。而道德基本上是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不过,它们也有相通的地方。我们说法律有良法、恶法。法律必须要有一个道德基础才能够有效地执行。大家都听过一句名言,不被尊重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更糟糕。我们内心会给予良法尊重。而遵守社会规则仅仅靠道德的力量也是不够的。这是道德和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方。

何怀宏
何家弘:何怀宏教授讲得很好。虽然从动机方面讲,弟弟情有可原,但是盗窃就是盗窃。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说,弟弟的行为我们很好界定——这是盗窃行为。其实,比较难以界定的是哥哥的行为——哥哥帮助警察把他弟弟给抓起来了,这种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
法律有善法、恶法,这就涉及到我们制定法律规则的时候,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犯罪行为,我们要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唐朝法律就规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为罪。法律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平衡不同利益和价值,要能够“strike the balance”。
但是,具体到制定每个规则的时候,法律的制定者所考虑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些年,我们法律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确立这种相隐的规则?或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应不应该有证言特免权?很多国家有证言特免权的规则,比如夫妻之间就有证言特免权,律师、记者和医生也有证言特免权。咱们国家从2001年开始讨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强调,被告人的配偶或者父母、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证言特免权。
在立法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善?我们的法律要做出什么规定才是惩恶扬善的?这可能需要哲学家帮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选择一条制定法律更好的路径。
何怀宏:何家弘老师说到的这个故事里,其实当时令哥哥最为难的是——警察要他去骗他弟弟到他所在的城市来,大概是为了方便抓捕。在法庭上,他弟弟非常沮丧——我是为哥哥偷钱的,但是哥哥为什么这样骗我?为什么不直接去抓捕?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无形中损害到了另外一些东西,比如人伦亲情的道德。
何家弘:我们制定规则的时候考虑的是价值取向。打击犯罪、查明案件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们还需要家庭伦理的价值,这也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有亲亲相隐的制度。证言特免权的制度就是考虑到了这些价值。
周濂:刚才谈到法律的道德基础,比如“十诫”一开始只是道德律令,但是现代法律把“十诫”中的主要内容都法律化了。法律维系的是人和人之间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的最基本规范,但是仅仅实现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们过上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也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复杂的人性和生活。
所以在法律和道德之上,还有更加幽暗复杂的伦理思考与判断或者每个人对自我的理解。我相信刘玮对这个问题很熟悉,因为这是伦理学要探讨的一个庞大且深入的话题。
除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外,何家弘老师还谈到了法律判决对于公序良俗的影响。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确实特别能反映过去几十年,甚至可以说几千年以来,社会观念的反复和变迁。我注意到何家弘老师提到了“传统”二字。值得思考的是,这里的传统指的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如果是大传统的话,恰恰应该弘扬亲亲相隐。如果是小传统的话,则要大义灭亲。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区别,折射出关键问题上的根本差异,比如,社会应该基于什么原则进行组织才能实现正义?人生应该基于什么价值进行安排才能获得幸福?
所谓证言特免权制度,包括亲亲相隐原则,是希望社会能建立在人和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这种信任关系当然要从亲人开始,然后延伸到朋友、邻居和同事。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容易,它首先会产生在小共同体的生活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人和人之间非常强的情感纽带。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油然而生的、自然而然的幸福感。
人工智能的崛起,
对人类伦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刘玮:何怀宏立足于伦理学的角度,认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规范;何家弘告诉我们,法律是建立在道德规范之上,但同时又有一种引领的作用;周濂从政治哲学和共同体的角度强调,这里面有共同体约定俗成的一些规范在运作。从三位教授的分享中,我们看到的善恶是发挥稳定性作用的东西,法律改变的东西可能多一点,但是也对道德有一种回应式的引领作用。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聊一点更前沿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常会面对新技术对道德的挑战。目前讨论的特别多的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给我们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何怀宏写了一本书叫《人类还有未来吗》,该书讨论人工智能对于伦理学造成的冲击,我想听听三位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独到的观点。

《人类还有未来吗》,何怀宏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何怀宏:我们都被技术笼罩着,今天离开手机我们几乎很难正常生活。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技术以一种我们很难预测其性质和后果的形式出现。未来是个未知数。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持续存在的基本矛盾:人类在飞速发展控物的能力,像上个世纪的上天入地的科学技术和今天的人工智能,但是,我们自身的自控、自制能力并没有相应地获得同步的发展。
我一般不太说道德滑坡。人性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差别,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在人性的范围内,我们可能有接近天神的能力,但我们的道德水平能否达到天使的水平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人就是人,人性就是人性。它会有起伏、改善,但是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人基本上还是一种处于中间居上的存在。
当然,我们也有人性的光辉,但我们很难超越人性的限制。总体上来说,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这些问题还是需要提出来,因为它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而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可以努力争取,这危机中也许有一个转机。我们不知道这个转机来自何处、发生在什么方面。我只是提出问题,现实就摆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一种预防性的伦理、法律的规范,至少要有意识地提前设置一些禁区,比如基因工程绝不能应用于生殖细胞等。
何家弘:何怀宏说他不知道未来,我就更不知道了。人类社会变成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比较守旧的,我接受新东西的速度很慢。我的手机以关机为常态,以前一天开一次,不像有的年轻人一开就是24小时。我一开机大概开10分钟。现在我有微信了,一天可能开两次,有急事可能开三次,但是一般也就开机十几分钟。
我们的工作需要这些新科学技术,像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但它们又在冲击我们的司法活动,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
从职业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司法人员?人工智能会不会让法官都失业?现在有互联网法院,还有 AI的法官。这个法官往往是一个女性,会发出很有魅力的声音,可以回答各种问题,但是它以后就完全可以代替法官来裁判吗?我们可以事先设计好规则,AI的法官就可以做出裁判。但它还代替不了人。有些裁判,包括我们情感的和道德方面的裁判,可能还得要法官来做。
人工智能这么发达,因为它主要靠的就是算法。据说算法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意志,以后可能会脱离我们原来设计的预判和规则,这就比较可怕了。这究竟能走多远?我们希望,人类还有控物能力的时候不要让它走那么远,不能让计算机都代替法官,或者代替其他人的决策,特别是我们有情感,我们有伦理道德的思维分析。
作为一个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还有另外一个对新科学技术的忧虑。科学技术首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但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为什么网络信息诈骗案件这么多?犯罪分子学习科技可能比老百姓学的还快,这也是我的忧虑。
我的另一个感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很多机能不使用就退化了。当然,年轻人退化得没那么快,但如果我们整个人类都如此依赖于这些机器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以后,人类的很多能力都慢慢减退了,我们真的就不如那些机器了?这想起来是很可怕的。像何怀宏教授讲的,人生里的很多东西不是你能决定的了,特别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只能跟着走。到时候,所有法官都变成人工智能法官了,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吧?我们也只能跟着走,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点。
刘玮:两位何老师刚才表达的基本态度还是忧虑的,感觉人还是被动的存在。周濂做过一个讲座,是说人的思维其实就是一种算法,这个观点会不会稍微乐观一点?
周濂:刚才我边听两位何老师聊人工智能和生化技术,边翻看手中的这本《关于善与恶的对话》,我在想,在不久的将来,这本书中的很多主题可能都会消失了。我特别想把何怀宏“人类还有未来吗?”的“问号”拉成“叹号”,但是好像我没有这个能力。
比如“生和死”的问题,有人预言,2049年人类就可以永生了。比如,“幸福”的问题,一旦我们真正发明出快乐机器,在大脑当中插一个芯片,直接进入“虚拟人生”的状态,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任何生活。这样一来,这些伦理学的话题似乎就都失去了意义。
打个比方,刘玮喜欢足球,他可以选择过梅西的生活;我喜欢篮球,就可以扮演乔丹。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过自己想过的任何生活,曾经遥不可及的幸福生活唾手可得,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似乎预示着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但是,我担心这会对人类生活造成一种“连根拔起”的伤害。因为所谓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不正是体现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沮丧、挫折、痛苦,以及偶有所得的那种快乐吗?当所有的挣扎、痛苦和努力都可以被一笔勾销时,我们可以即插即用、过上想过的任何生活时,不同类型的生活的好与坏,个体的自由选择,以及由选择带来的代价就都失去了重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句话将真正成为现实,这个未来一点都不美好。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说的话,更是如此。我们刚才反复在谈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它们曾经塑造了过去几百年的人类社会。福山在2002年写过一本《我们后人类的未来》,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三部曲当中也谈到了类似的忧思。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一旦人类真的实现永生,并且在未来创造出超人类,那只会让少数人获得永生的权利,让少数人拥有可以凌驾于众生之上的那种智力和能力。这将对人类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巨幅改变。
这样一来,人类将会迎来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尼采预言的“超人”就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了现实。但是,刘玮应该很了解,尼采所谓的“超人”并不是一个不同的物种或一个更高级的种族,超人就是人自己——一旦他学会了肯认他真正所是的那个人。这也就是说,尼采的“超人”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成其所是”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成其所是,什么叫成其所是?这要认识到你的本性和潜能,并且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来实现它们。这个过程艰辛无比,但也乐趣无穷。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AI和生化技术,所有的这些努力似乎都可以唾手可得。
人类还有未来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很难把它拉成叹号,因为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我自己在若干篇文章和公开演讲当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就是要用政治去锁死科技。
如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足以让大多数人过上相对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当然,我们难免会遭遇一些难以承受的身体疾病和痛苦,但这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必须要学会跟这些痛苦共存。
过去这几百年里,包括最近加速发展的这几十年来,人类好像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到一种极乐世界,尽可能地避免任何意义上的痛苦——无论是借助于政治的设计,还是科技的进步,人类都要把痛苦极小化,要把快乐极大化。这种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真正实现的话,那就与人生的真义是背道而驰。

周濂
何家弘:咱们学生都有感觉,当年在高考时觉得,考上人大就会很幸福,能考上北大就更幸福了。但是,当你真正考入人大、北大,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幸福。你再读个硕士、博士也还是一样。假如我能挣1000万,我感觉就会幸福,实际上,当你真有1000万的时候,你还想要1个亿或者10个亿。所以,当你一旦得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幸福了。幸福在于过程,尽管有磨难,但我们在追求中能享受那种意义感。
幸福的很大一部分是成就感,记得一个美国哲学家说过,“What you are?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you are not what others think you are,you are what you think others think you are”.“你不是你认为所是,你不是别人认为你所是,你是认为别人认为你所是”。这讲的是社会行为标准对个人行为的塑造。
英国《金融时报》有差不多一整版对我的专访,谈的就是我的两顶帽子:既是法学家,又是文学家。我会开玩笑说:I'm not only a jurist but also a novelist,so I would have some novel ideas about the law。这里面的novel是双关语,一个是小说,另一个就是“新颖”。
写小说时,我总在思考性善性恶,用文学的方法去思维。我觉得人性中既有善缘,也有恶端。在社会中,真正的好人很少,但是真正的坏人也很少。年轻的时候,大家觉得都是好人多,后来大家又感叹说,社会上好人怎么越来越少,往周围一看都是坏人多。作为个体,你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要竞争;但作为群体的一员,要生存就要利他、利群,最典型的就是母爱,这是一种天性。
有时候,做善事也是为你自己,虽然行为本身是利他的、利群的,但你会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或者一种安宁。如果中国社会能逐渐形成大家都以做善事为乐的氛围,上行下效,这是很好的事情。要改善社会氛围,需要好的社会环境,法律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哲学和伦理学是一种行为导向,法律则有惩善扬恶的功能,我们需要双管齐下。
刘玮:刚才周濂提到,用政治来锁死科技;何家弘说,用法律去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那伦理学能在这里面做什么呢?何怀宏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怀宏:伦理学主要靠的是个人的内心信念和社会的舆论起作用,另外还要努力寻求某些共识。有时候,这可能是残存的共识,人们很不容易凝聚共识。我同意何家弘所说的,你要重新凝聚共识的话,就不能太高调。足球道德要求太高调,球就没办法踢了。我也特别同意周濂讲的,做任何事情就是要考虑政治,政治有一种关键的杠杆作用。
我们可以说,首先,物质是基础。没有物质,我们就无法吃饭穿衣,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其次,价值是主导,我们追求什么。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你的追求,但是我们一定会比不追求时会得到的更多。最后,政治是关键,政治是直接和权力打交道的。后面还有合法的暴力,它确实往往是改变事情的关键。
顺应现实,又能撑开一些微小空间
刘玮:我们回到这场对话的意义,这本书谈了伦理、善恶、幸福,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种真正的理性的、实质性的对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反思,对于推进社会的变革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教育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几位老师肯定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能否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何怀宏:我没有对教育做过什么专门的研究。只是说一点:教育的政策需要谨慎,要考虑人性、国情、民情,考虑人们可能的反应和对策。
何家弘:在生活中,人们常常对平等有着强烈的诉求,但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有人这方面能力强,那方面能力差。但是,若我们有平等的机会,社会就会走向公正、平等。在机会平等里面,教育机会平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为未来成就奠定重要基础的一步。当然,教育资源的本身有局限,我们需要好的管理和技术。
这就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对现在的孩子和年轻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是你考上什么中学和大学。其实,人以后的成就跟上什么学校没有绝对的关联。我们要让大家认识到,成功的道路可以有很多条。我们要给他们开辟各种各样不同的成功路径。这样的话,大家的成就观标准就不会这么单一,就不会把上什么样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看得那么重。
我有外孙子和外孙女,我也关注年轻人对下一代的培养。我觉得很多激烈的竞争都是这些年轻的家长塑造出来的。家长们都很拼命,一定得上好的小学,中学得上人大附中。家长的价值定位和追求会促成扭曲。现在年轻人教育孩子,可能还有一个倾向,老怕自己孩子以后受欺负,老怕自己孩子成为弱者,或者是怕孩子成为落入狼群的羊。其实,这对孩子的性格塑造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年轻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狼,我们这个社会就是狼性的文化。
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做好人。现在有不少人转变了观念:我这辈子不做好人,当然也不做坏人,这不好听,那就做一个恶人。因为恶人在社会中会吃香,就像最近很引人关注的某董事长在电梯旁打院士,还有人要改名叫“霸道”。像怀宏教授说的,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走着瞧吧。既然我们都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们就只能不断反思,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途径,逐渐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希望未来会越来越好。

活动现场
周濂:关于教育,我最近关心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中考分流的问题。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很多孩子比较晚熟,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可能要到高中以后才能真正展现出理科或者文科的优势。如果在初中就分流,这会让很多孩子失去实现自我潜能的机会。作为学者,我只能借这个机会发出呼吁,希望能得到一些反馈,期待相关政策的制定,能够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人的观点和专家的意见,进行充分论证,让政策能改进得更加合理。
未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过去的种种制度,各有缺陷和不足,而面对未来,人类的想象力和制度的可能性似乎也已经被穷尽。怎么办?面对日渐逼仄的环境,我觉得作为个体来说,仍旧可以做很微小的一些尝试和努力。
何家弘刚才谈到自信心的问题,这的确是教育孩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我女儿从4岁半开始,因为“peer pressure”开始学习小提琴和芭蕾舞,但很快我们发现,她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芭蕾舞学了一个月后我们就果断放弃了,小提琴坚持了一年半,最后出于家庭所有成员的身心健康考虑也放弃了。放弃之后,我们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同时又会感到焦虑,孩子啥都不会,这以后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就采用了相对比较取巧的方式,不会弹小提琴,我们就练尤克里里,跳不了芭蕾舞,那就去跳街舞,怎么容易怎么来。而且,我们还自我安慰说,在同学聚会的场合中,弹尤克里里也许比拉小提琴和弹钢琴更能博得满堂彩;在公司聚会的环境中,跳街舞也许比跳芭蕾舞更能赢得同事们的青睐。
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道理:现代社会可供个体逃遁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努力去撑开一些小的空间。你当然无能于去全面反抗社会制度和整体的评价体系,但是你可以在顺应的同时保持一些选择的空间。
作为家长,我们都会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非常真实而普遍的压力以及压力带来的焦虑,如果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就必须做出这种小的对策和创造性的调整。
作为大学生同样也是如此。压力无处不在,焦虑如影随形,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经典理论来理解这个时代,甚至批判这个时代,但是在批判完了之后,还是需要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去,做出真实的选择。前两天我给一本书写了一句推荐语,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疏离,不顺从,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同时成为时代中的人。”
现代性是一个欲望的解放过程,无论是物质的欲望还是身体的欲望,它们都不再受到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束缚。欲望成为一个越来越天然且正当的东西。不仅如此,欲望还在被发明、被创造、被肯定,现代的资本主义包括商品经济,其实就是以发明、制造和不断促进、提升欲望作为它的内在的原动力。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更换过很多代手机了。按道理的话,要能够实现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的功能一部手机就够了,但为什么我们不断地换手机?这其实就是欲望被制造、被发明、被促进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是审美的、趣味的以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也使得道德评价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趋势。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欲望的被解放和道德评价的日趋多元化,我们又正在目睹一场物极必反的价值回流过程。比方说,在公共交流平台上,我们时常能够看到道德主义的义愤填膺,己欲立而立人的强人所难,包括刘玮一开始说的林生斌案例。当别人的生活选择跟我心中的道德标准不相符合的时候,有人就会动用网上舆论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无所不在的干预和批判。对于此类现象,我个人还是蛮担忧的。我始终认为,价值多元化是一个现实,只要不堕入相对主义的泥沼,价值多元化还是一个相对合理和正当的状态。
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应该就像这本书的书名那样,形成“关于善与恶的对话”,而不是通过某种强制力——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来终结这场对话。
嘉宾 | 周濂、何怀宏、刘玮、何家弘
整理 | 徐悦东
编辑 | 申婵
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