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史与全球史研究在西方国家发展迅速,两者相结合带来的新视角对于阐释欧洲殖民扩张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研究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在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并试图对排华这样的“老问题”阐释新意,其代表作当属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孔飞力指出,美国白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优势,他们对于华人的恐惧源自经济或政治因素;澳大利亚则更担忧大英民族的白色血统被染黑,以至被彻底摧毁。这两种担忧相互交织,将矛头一致指向华人。在孔飞力看来,当地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是“白澳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对此,费晟在《再造金山》中有不一样的看法。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反省种族歧视问题,并于1975年出台了《反种族歧视法》,强调多元文化共存,但直到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依然“不时有人(虽不是主流)对华人移民感到焦虑和排斥,特别是当发生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社会公共危机之时”。以至于每年华人纪念《反种族歧视法》实施时,都会来到悉尼西部郊区的六福公墓,去祭奠在19世纪淘金热中被迫害的华人淘金者,这不仅因为他们中有人是这群华人死难者的后代,更因为这场种族歧视事件的影响延续至今。
排华的种族歧视根源究竟是什么?这是费晟心中的疑惑,也是他在《再造金山》中致力于探讨的问题。费晟通过研究华人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生态联系,发现另外一种排华的原因:欧洲移民者控制殖民地生态霸权的渴望,与华人移民逐渐展现出来的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形成了冲突。
欧洲移民不仅用枪炮、细菌与钢铁战胜了原住民,还在多元的移民群体中取得生态竞争的胜利。正是由于取得了生态竞争的胜利,欧洲移民及其后裔才主导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殖民地生态,成为维持他们政治、经济及文化霸权原因之一。这也使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华人群体不断被边缘化,甚至在历史研究中他们也较少被关注到,远不如对美国或东南亚华人移民研究那样重视。
华人移民是如何被边缘化的?他们是如何成为移民社会的“他者”而长期存在?
对此,费晟充分利用官方档案、近代报纸等资料,尤其是维多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原始档案,将这群失语者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掘出来。随后,费晟惊奇地发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华人移民不是地方建设的被动参与者和旁观者。他们主动参与了当地的生态建设,并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对生态改造的影响,甚至让欧洲移民产生了生态焦虑,进而发起排华舆论和排华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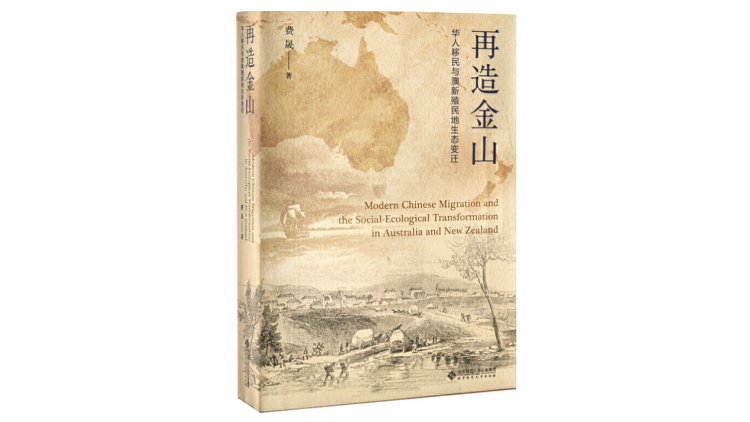
《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费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
海参、檀香木与海豹皮
在极端的“西方中心论”影响下,澳大利亚社会长期回避自己与地理上更为接近的亚洲的交流历史。其实,中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经济以及生态上的联系。大约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海参成为中国人食谱中的一道美味且高档的食物,这蕴含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促使中国商人推动了东南亚海域的海参捕捞与贸易活动。在早期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参、檀香木贸易中,中国实现了长期掌控,其贸易商路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中国主导的海上交通线。
在18世纪70年代,中国巨大的市场价值已经令人无法忽视,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让英国商人开始寻找高利润的对华贸易物品。通往中国的“极东航线” (英国探寻的连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海路)被开辟出来后,殖民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大洋洲海域分布广泛的海豹,它们的毛皮能在广州获得巨额利润。费晟总结道,“如果说海参贸易还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海外交通的延伸,那么后者则完全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在太平洋扩张的产物”。在南太平洋,欧洲势力越来越强势,欧洲人成为不断开辟生物产品新资源边疆的主要推盘手。
在“极东航线”开辟后,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记录。1848年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年澳大利亚首次出现了华人成批输入的记录。华人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十分缺乏劳动力,牧羊业的大扩张引发了大量的用工需求。1848年6月6日,英国运输船“宁罗号”从香港出发,随后到达厦门运载了120名华工,在海上航行三个多月后抵达悉尼。在牧羊业大举推进的185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淘金热在澳大利亚爆发。政策加上资源吸引力共同促进了华人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入澳大利亚。
淘金热与排华兴起
这场以加利福尼亚为开端,蔓延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南岛的淘金热,吸引了大批国际人口进驻,其中包括华人。来自珠三角四邑地区的移民成为淘金华人移民的主力。
其实,相比欧洲矿工,华人来得已经较晚。当华人在1853年后逐渐抵达矿区时,很多矿区表层都已经被欧洲矿工开采过了。华人淘金者所做的工作更多是对前人放弃的矿坑进行二次淘洗,但反复淘洗会耗费大量水源,同时会破坏地表植被与土壤结构。这是华人与欧洲矿工因矿产与水源分配发生纠纷,陷入种族冲突的外在因素。

澳大利亚淘金热。
欧洲矿工指责华人破坏矿区环境与生态,尤其是指责华人导致缺水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事实上,在矿区淘金者中的华人所占的比例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破坏水资源的主要责任人,只是华人动辄几百人的作业方式,让华人破坏水源的印象令人格外深刻。自此,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开始浮现,“华人破坏环境”的负面话语不断被构建。在这个新兴的淘金移民社会,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生态霸权观念正在不断浮现。
《再造金山》所提到的让欧洲工人频繁掀起排华序幕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华人矿工与欧洲矿工的利益之争,华人总是一次性把二手矿土淘洗彻底,让欧洲矿工无法再次利用有潜力的矿坑;华人集体作业规模较大,常常一次几百人,太过显眼;华人能吃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能够主动吸纳外来经验与装备,形成一定的族群就业优势;确实存在浪费水资源、破坏生态的现象。
欧洲移民矿工以生态破坏的话语鼓吹排斥华人移民,同时迫使一味妥协的殖民当局通过排华立法与种族隔离制度强行规训华人移民的生态。尤其在“尤里卡栅栏暴动”后,官方向欧洲矿工妥协的行为也姑息并推动了欧洲矿工的排华活动。1865年,限制华人移民入境法和种族隔离制度最终被制定。华人移民在消极抵抗中熬过了漫长的歧视岁月,这段历史也见证日后殖民地排华话语的基本逻辑。在殖民地社会萌动的欧洲中心的生态观正不断走向实践,从而逼迫华人寻找新的出路。
华人移民的生态改造与适应能力
随后,费晟在书中描绘了华人积极投身于当地生态建设的图景。在极端的种族排斥面前,这些来自珠三角的华人把他们故乡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移植到了新居住区。他们以蔬菜种植业为起点,让被蹂躏和破坏的荒野重新焕发生机。尽管不同矿区华人蔬菜种植业的起步时间并不相同,但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它们几乎各大矿区都已经明显存在,这个规模是值得肯定的。各城市附近都开始建起了中国式的蔬菜种植园,这使得华人不再是所谓的“过客”或“旅居者”。
1865年后,被迫转移到寒冷的新西兰以及炎热的昆士兰殖民地的华人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环境适应与改造能力。由于欧洲矿工并非当地的主体族群,华人矿工也开始注意避免上百人集体作业所引起的瞩目,加上华人擅于改善和操作新技能以及吃苦耐劳、迅速适应新的恶劣环境的精神品质,让华人在奥塔哥矿区不占人口优势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在数个采金场形成了资本优势。
最后,费晟描述了华人资本在矿业开放、水果种植、农业领域的成功案例,譬如华人带来了热带种植物,昆士兰的香蕉本身起源于中国,香蕉产销业的大繁荣最终促成了华人的行业垄断地位等。华人资本空前改造了殖民地的原生态,也大大促进了华人移民与其他移民生态与文化的融合。
19世纪末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兴起的排华思想,不仅仅是因为欧洲人对华人文化或经济竞争力的拒斥,也源于对华人移民生态优势的忌惮。费晟强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所谓“新大陆”殖民地之所以成为“新欧洲”,不仅在于欧洲新移民生态对原生态的征服、替代与改建,更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排挤和压制其他移民的生态与文化。

19世纪澳大利亚排华活动宣传画。
费晟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有海外研究经历的他,优势在于熟练驾驭各种西方理论,比如书中常常提及的“资源边疆”“生态扩张”“系统殖民”理论等。综合而言,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更关注华人移民与周围环境要素,尤其是与其他人类关系的变化不同,费晟在书中提炼出一种书写移民环境史的新思路,即论述以移民为中心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他不仅讨论环境因素在迁徙过程中扮演的作用,还关注移民适应并改造新环境的行为、思想与后果。作者将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与环境史视角相结合的叙述模式,最终诞生了这本值得一读的专业著作。
撰文 | 李轻尘
编辑 | 王青;徐悦东
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