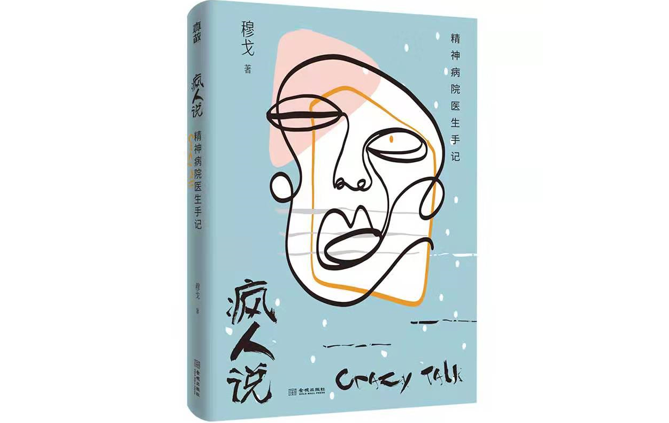
《疯人说:精神病院医生手记》,穆戈 著,金城出版社2021年6月版
老实说,我觉得书中的穆戈(而非作者),可能是我的同行。她在实习单位做选择时,选了精神病院而非法院。然而在后几个故事中,不知不觉回归了犯罪心理分析的角色:她分析纵火犯的心理,也用木偶刺探杀人者的心魔,还试着分析反社会人格的精神基础与社会危害——我猜,这位穆医生很有可能是司法精神病学或犯罪心理学的同行。
猝不及防和另一个自己say “hi”
那是大约二十年前了。在操场旁边的“三教”,孙东东老师给我们上课。教室里坐满了各式来旁听的人。他讲起来就停不下来,需要最后一排助教给他示意,才会说“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他讲了好些“疯人说”故事,疯狂的生命力喷薄而出,是当时法学院里少有的有趣课程。那个学期之后,我决定将硕士论文选题定为精神障碍刑事责任豁免,即Insanity Defense,因为“疯”而做错事的豁免事由。
那篇论文从荷马史诗写起,写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如何看“疯狂致罪”。写到中世纪的精神迷乱者的形象和猎巫者运动,十字架与升起的浓烟。相比之下,保存了希腊文明的东罗马帝国以及更遥远的伊斯兰世界,对于精神障碍者的态度就温和许多,将其视为“着魔者”,甚至允许他们接受治疗。同时出于盖伦传统的影响,将精神障碍的原因归于人的大脑,从而为未来的医学心理学发展埋下种子。之后写意大利犯罪学三杰,特别是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他将异常行为回归了自然疾病,而不再认为是“心灵不虔诚,使恶魔有机可趁”。然后,是现代社会。一边是福柯,明知疯癫是病却一样为了“文明”而进行“净化”;另一边终于是今天的刑事责任精神障碍抗辩——比如NGRI(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标准与欣克利案。然而,这一机制又可能成为脱罪的借口或是剥夺刑辩权利的理由。
为了写这篇论文,毕业实习的时候,我真的动过去北医六院或者安定医院的念头。后来没有如愿。好像是因为我终于选择了更有“钱途”的人生方向。那之后好多年,我们迅速掌握了求生本领,而将荷马、福柯和龙勃罗梭还给老师,束之高阁任其蒙尘。现如今,每日将衬衫扎进长裤,出没在金融街的会议室与交易场,全然忘了当初硕士论文写作时那些在深夜里,被一场又一场盛大的溃败诱惑至冷酷边境,目睹海妖骑脚踏车滑过天际的奇妙时刻。然后,硕士毕业交掉论文,我们迅速地长大成熟,被唤作某律师、某经理而心安理得。
其实有很多法律少年的成长路径,都是如此。直到很多年后,读到这本穆戈的《疯人说》,仿佛平行时空的自己伸手say hi。地铁飞驰渐停,车门打开,是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久违了的尴尬一笑。小说而已,你对自己说。然而那个尴尬的笑容始终都在,提醒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与营生,并非世界或人心的一切——甚至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或那一角上停的一只海妖,正在打呵欠时掉下了的睫毛——我们却当其是宇宙的全部,并为之殚精竭虑、拼杀至电视剧的最后一集。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说回《疯人说》。好几个故事验证了阿德勒的那句老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孩子为了回应父母的期待,迎合父母的扭曲,并酿成新的悲剧。“双重人格,与你共享脐带和灵魂,直至为你而死,请以你的名字安葬我”中的方宇可如此,“家里的猫死了之后,她变成了猫”中的茉莉也是如此。
方宇可为了让父母喜欢,创造出一个擅长学习的第二人格,自己却渐渐消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好像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他们背书很快,我不行,他们算数很快,我不行,爸爸看我的眼神很可怕……我讨厌考试……爸爸妈妈又在吵架,我偷听到了,爸爸说要再生一个,埋怨妈妈身体不好生不出了,又说就是因为妈妈身体不好,才生出了我这么个蠢货……今天考试的时候,我突然没感觉了,醒来的时候考完了,还考得很好,这是为什么?……我有了一个弟弟,弟弟很聪明,妈妈喜欢他,爸爸也开心了,我也会开心的。”到了最后,这个人格吞噬掉笨而真诚的方宇可,替代着他活下去。
而在茉莉的故事中,茉莉为了治愈母亲因丧宠后的崩溃,而幻想自己是那只猫而不可自拔。“妈妈的猫死后,妈妈崩溃了,突然不认识自己了,行为奇怪,大晚上在吃猫粮,茉莉全都看到了,她起先可能只是受了影响,渐渐地,她发现吃着猫粮的自己,会让妈妈冷静下来,她和妈妈的互动,也渐渐成了妈妈和猫茉莉的互动,为了妈妈能活下去,茉莉让自己成了猫。在房间的茉莉似乎听到妈妈在哭,连忙跑了出来,抱住妈妈,似乎是觉得那样的自己不够安慰妈妈,于是习惯性地,喵叫了一声。”
这样的故事,其实不只发生在精神病院。孩子病了,父母才知道送他们上医院——全然不知道自己才是病根。那些并未进入精神病院的孩子,又何尝不是一边在父母亲笔绘制的迷宫里走不出来,一边以爱之名讨好父母的“病”与“爱”?
穆戈很擅长描绘这样的讨好型人格。他们在积累了许多委屈后偶尔爆发,才被人们注意到;可是更多的时候,他们过分懂事地维持着这一切,纵容着父母的扭曲心态——大概因为怕被抛弃,而选择了博父母一笑。这也是一种训练与驯化,只是结局往往并不美好。
所以,有不少问题,都来自四个字:“原生家庭”。穆戈非常诚实地面对着原生家庭带来的“病根”。“逢魔之时,噩梦之眼和人类之眼彼此凝视”中的毕华,小时候跟外婆在山村里生活,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自生自灭”。
而且外婆不许他心有所好,发现他喜欢大片的杜鹃花,“于是那些摇曳风姿的红花就在他面前,被她一镰刀砍了,砍还不够,她连根拔,绿色和红色乱了一地。她抓着大把的红花,牵着小孩回了茅屋,在木桌上,把红花捣碎在盆里,用一根很长的棍子,每捣一下都看他一眼,他走开,就会被她抓回来坐好,直到看她把所有红花都碾碎,倒入热水,端到他面前:‘喝。’
红艳的碎花汁晕开了像血,他看到里面还有蚂蚁,在动。‘喝。’小孩喝掉了。她在腰前肚擦掉了满手的花色,赞扬地摸了摸他的脑袋,小孩看着她衣服上的红色手印,像她刚杀完猪的样子。他又小心翼翼地看那根捣碎了杜鹃的棍子,算着何时会落到他身上。”
即便成了一生的梦魇,他还是想着外婆。“我一惹她生气,她就会消失,哪里都找不见的那种,茅屋里没有,山上也没有,她说不听话的孩子没人要,我一次都没有找到过她,只能等她自己出现……两天后,三天后?不记得了,有时候我饿昏了,醒了她就回来了。”穆戈说,听到这,“我明白了他和水鬼所谓的捉迷藏游戏。人在童年时经历的创伤,会反复在他今后的人生里重演,一个跨不过去的坎,这辈子都会重复去跨,一次失败的寻找,会让人这辈子都关在寻找的游戏里。”毕华如此,方宇可如此,茉莉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
人是精巧易碎的玩具。有时,医生辛苦修好,送回社会,一下子又会粉身碎骨。这是穆戈借齐素这个角色,想要传递的信息:疾病来自社会与关系。齐素和穆戈当然是一个人——甚至刘祀和韩依依,也差不多是齐素这个角色的另一面而己。
齐素是本书中最重要的角色,他年纪轻轻已成为精神病院院长,并带领团队开展“精神干细胞”的研发。然而他在目睹了长达六年的一场网暴之后,开始怀疑个体的治疗效果。他对学生刘祀说:“小刘,你还没明白吗,关键不是个体疾病的治愈,精神癌症的关键,不在脑子里,而在于关系,你今天治好了他的脑子,你一把他放回社会里,关系的癌症,就会再将他破碎掉,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关系的干细胞,我们放错重点了……你能切断他的病,但切不了源,你给他植入干细胞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这个世界毁灭干细胞的速度,他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目光,健康的人都能被目光所燃烧致病,何况一个经历过深渊的人,你治好了他,满足了你的施展欲,可他再度被目光和关系撕裂时,你能为他的绝望负担什么?”
看过《新世纪福音战士》(这部动画已问世三十年,比许多“文献”可能时间更久、传播更广)的朋友会明白,齐素想要的,是一场面向全民的治疗,或者一场“人类补完计划”。他说:“目标不是患者,而是,常人的目光……干细胞源于胚胎,那么精神干细胞,也该源于关系的胚胎,我们该做的,是替这世界重塑一场分娩,让那些所谓的常人,和他们的目光,习惯精神病,当人群中的大多数都是患者,当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与患者其实是同类,精神干细胞才是真的成了。”齐素说的真正的“精神干细胞”,脱离了生物取向,是抽象的,他和刘医生完全相反了,一个想做精神实质化,一个想做精神虚无化,一个要把精神干细胞植入患者,而另一个,认为精神干细胞应该植入的是世间常人。齐素不打算治疗患者了,他打算“治疗”正常人。
一百多年前,胡适在介绍易卜生《人民公敌》时说过相似的话。那是1918年,胡适刊载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 。他写道:“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白细胞)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能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多克芒医生这一类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绝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宝贵的是,《疯人说》写到后来,多少有些《十日谈》与《巨人传》的意味。治疗成为一种对世界的思考。因此,之所以说韩依依是齐素的另一人格,是因为她的戏剧治疗,不但可以治疗精神病人,也还是个唤醒“正常人”的办法。以戏剧传达声音的场景多得很,从酒神到哈姆雷特,不一而足。
法国戏剧大师阿尔托说:“经过这样一次演出,可以期望观众离场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震动。之后,他到剧场去,会像去找医生或牙医那样,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治病,而且完全明白这种体验将是痛苦的。这样,戏剧就逐渐改变了个人的心理状态,从而自然而然改善了社会秩序。”这是一种社会治理,也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治疗”方式。无论在易卜生的时代,还是胡适的时代,皆是如此。有时我在想,齐素想要的精神干细胞,也许就是易卜生和胡适的“白血轮”。假如穆戈能将这些话告知齐素老师,告诉他并非孤单一人,而且,他的愿望分别由刘祀和韩依依在实现着。这样,也许能宽慰其寂寥,安抚其挣扎,请他歆享了牲醴和香烟,给人们以真正的祝福。
作者 | 艾利克斯
编辑 | 申婵
校对 |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