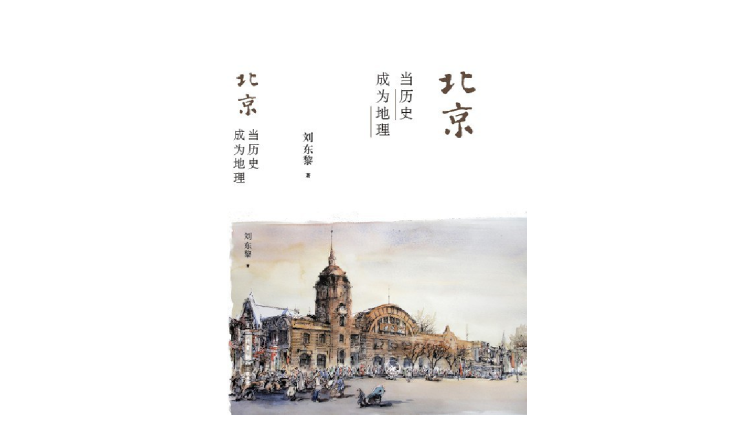
《北京:当历史成为地理》,刘东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版。
钟楼是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标志
钟鼓楼午后的金色阳光沉静无声,充满着玄象和智性,仿佛是对时光的吟哦和歌咏。从某种意义上说,钟鼓楼就像一个巨大的计时器,记录着日升月落、朝代更迭。我们在苍茫悠远的晨钟暮鼓里直接面对时光,面对它那宏大、绵延的存在,以逝者如斯的平静和安详,与永恒息息应和……
出斜街,沿地安门外大街往北,左侧便是红墙朱栏的鼓楼,青砖素瓦的钟楼则位列右侧;它们共同构成了北京中轴线壮美逶迤的余音——如果说故宫是北京城中轴线的高潮,而鼓楼和钟楼,则是中轴线的意味深长的尾声。时至今日,在元大都如同棋盘一样经纬分明的街道设计里,唯有钟鼓楼所在的街道,依旧忠诚地遵循着往昔漕运的走向和布局;作为一种年代久远的报时工具,钟鼓楼见证着北京城几百年来岁月的变迁,也见证着一代代北京市民庄严而生动的流水生涯。在元、明、清三个朝代,这里都是北京城的报时中心。
1272年,钟鼓楼被精心建造在元大都都城之中,成为古代都城的司时中心。从那一刻起,钟鼓便成为传递时间的使者,启闭城门的信号,在一代代北京人的心目中,树立起一种特有的神圣与威严,同时满足了报时、施教、扬威的需要。钟鼓楼日益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是一切实体存在的要素之一,“声与政通,硕大庞洪”,“以时出治”,又能昭示法度、安定民心。回味“钟鼓楼”这个名词,就会令我们悠然获得一种历史和时间的纵深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暮鼓晨钟,以一种空旷廖远的宏大意境,使古老都城的人们逐渐对钟鼓之声产生依赖,渐而转化为尊崇,达到了空前的教化效果。
此时我站在钟楼下,北风正大。仰望天空,感觉天幕正在一片一片被撕开,四面八方都是风的通道和碎片。岁月嬗递,钟鼓楼仍不失往日的华丽和庄严,虽然高楼上早已传不出晨钟暮鼓的肃穆与清朗,然而心绪依然在历史的四野八荒无序地蔓延,不知能否跨越七百年的时空。元宝脊上的阴阳瓦和兽头瓦在改变着气流的走向,扩张着声音的通道;而时间的弥天洪水在通过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也使他们看到了它更真实的茫茫无声的面容。
钟楼是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标志。元代《析津志》载文:“钟楼,至元中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后来毁于一场莫名的大火。明永乐十八年(1420),钟楼在元大都的万宁寺中心阁的旧址重建;发声“清宵气肃,轻飙远扬”。
历史的宿命有若轮回,不久钟楼又毁于大火。到了清乾隆年间,乾隆认为钟楼是紫禁城的后卫,那口大钟则是中国的皇钟;于是“柱棁榱题,悉制以石”,钟楼再次重建,而且第一次采用砖石砌筑,从此令钟楼消除了火患。两年后钟楼竣工,喜欢舞文弄墨的乾隆皇帝没有忘记洋洋洒洒写上一篇惊世奇文,以垂范后人。
一个深居在老北京灰墙青瓦的四合院里的隐士
现在的钟楼分上下两层,底层是拱券式砖石城台,上沿四周建有雉堞。四面开券门,券洞内呈十字相交形,中心相交处为一边正方形“天井”,往上与二层相通,可仰望大钟。钟声通过“天井”的共鸣,产生巨大的振波,向古城四方传递,浑厚的钟声,十余里外都能听得见。
钟楼所有窗户均是罕见的石雕窗,四周有汉白玉石护栏,内部东侧筑有七十五级石阶直达二楼。二层建筑独成一体,坐落在城台之上。正方形汉白玉须弥底座,上沿四周镶嵌着洁白的石护栏。重檐、歇山顶,上覆黑琉璃瓦绿琉璃剪边,显得精臻凝练。券门两侧有汉白玉镶边的拱券式暗窗相衬,窗心是古拙淡雅的砖雕花草图案。大额枋、檐檩、斗拱、檐椽等均为石料剔凿而成,上面仍保留了清式旋子彩画,两侧山花均为琉璃砖拼制而成的金钱寿带,饱满遒劲。
对钟楼雄伟的飞檐杰阁,乾隆皇帝曾有过这样的赞誉:“尺木不阶,屹然巨丽。拔地切云,穹窿四际。岌业峥嵘,金觚绣甍。鸟革翚飞,震辉华鲸。”而报时的巨大铜钟,铸有“永乐年月吉日制”的印记,即悬于楼中央八角形木框架上。铜钟重约六十三吨,居然比大钟寺里的永乐大钟还重十多吨,可称中国古钟之最。其以响铜铸成,声音淳厚绵长,据称“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
华夏祖先对于时光的流逝有着切身的体认,漏、晷、钟、表……种类繁多的计时工具表达着他们对时间的敬畏。钟鼓楼曾经是北京人最熟悉的声音,不论是文武百官上朝,或是百姓生活,都要倾听“击鼓定更撞钟报时”的韵律。从钟声鸣响的那一刻起,人们就感觉到时间在那一瞬间忽然显现。而平日,它潜藏在琐碎和繁杂的生活表层之下,没有响动,没有声息。
钟楼内部建筑结构与声学原理的统一,使钟楼这座古代建筑更独具特色。重建后的钟楼,不仅巍峨、壮观,而且把建筑结构、共鸣、传声三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天井”与“十字券洞”的贯通,恰似上下两个重叠的共鸣腔,使钟声回旋千腔体,产生共鸣。不仅钟声得以扩大,而且更加圆润动听。只是不知道这钟中之王是如何铸成,如何运到这里,又是如何挂在这梁上的。
民国时期,钟楼被改为通俗电影院,据说因为营业不佳,时演时辍,后来干脆辟成了自由市场。虽然远不如鼓楼院落大气,但是因为紧邻民房,钟楼显得清雅幽静,有种超然于世的感觉。有时你会恍然感觉,钟楼就像是一个深居在老北京灰墙青瓦的四合院里的隐士,展现着深邃的文化风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鼓楼位于几条重要马路的交会处,楼前车水马龙,从古至今都是附近街市的标志性建筑,宛如一位披着光鲜的铠甲每天准时站岗的卫士。透过密密交织的叶隙,往上,能看到鼓楼的翘角飞檐。

钟鼓楼。《北京:当历史成为地理》插图。
太阳已经西斜了,这是一天中最适于登高的时光,崔颢就是在这一时刻登上了黄鹤楼,李白就是在这时刻登上了凤凰台,辛弃疾也一定是在这时刻登上了北固楼。鼓楼虽然总共就只有两层,但想要上去的话,任谁都得费些力气。登上鼓楼,向南可见什刹海水波清浅、景山万春亭巍然屹立,令人感觉钟鼓楼的声音虽成绝响,但是它的存在已凝固成一种悠远之美。
鼓楼二层展示有一件古代计时器的模具,据说称作“铜刻漏”,已有近千年历史,原物已经遗失,但就其仿制的外形看,共有四口水箱依次相叠,有一个造型逼真的铜俑双手持铙,每到固定时间就会自动撞击,创思之精巧,令人击节。另一件名为碑漏的,虽已失传无法仿制,但仍能让人悠然想见时光奔涌给先人带来的灵感与内心的共振。
在以这个报时建筑为中心形成的浓郁生活氛围里,鼓楼在漫长的岁月中,成为引导城市生活起居的地点。如果说故宫是草芥之民绝无可能踏入的皇家禁地,而鼓楼一带,则已逐步过渡到平民百姓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和意趣的衔接点下,演出过多少王公权贵和草根百姓生死歌哭的故事?历史像一个巨大的涡流,一切都在其中变得混沌不清了。
钟鼓声延续着我们对时间和历史有意味的倾听
鼓楼到清代时已经重修了很多次,保持着相同的建筑规模,它的报时功能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负责击鼓撞钟的銮仪卫因而废止,经历了这一场历史的重大变迁,钟鼓楼从此就成为失语的沉默建筑。
当然也不能让它闲置,京兆尹薛笃弼动了脑筋,将鼓楼辟为“京兆通俗教育馆”,开创了民国时代对民众教育的先河。为了使国民永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国耻,薛笃弼还一度将鼓楼更名为“明耻楼”,展出了大量的国耻照片和实物,据说被八国联军刺破的一面大鼓,陈列在鼓楼内,警示后人。后来,鼓楼改为“第一民众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钟鼓楼一直作为群众文化馆而存在。
钟鼓楼的钟鼓声不仅传达了报时的声响,更传达了一个广阔悠远的历史和文化的信息,雄奇高伟的建筑,延续着我们对时间和历史有意味的倾听,让人在悠长的回音中有所感悟。在钟鼓楼被设为报时中心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都是作为商业标识而存在的。在七百多年前的元代,大运河的终点码头距离鼓楼不远,当水势浩荡的漕运河流从周边迤逦而过时,鼓楼自然就成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加上南端是宫城,北端是集市,这里很容易就涌现出无限的商机。什刹海和积水潭一带成了百姓游憩的好去处,在当时就有帽子市、皮货市、鹅鸭市、珠子市、柴炭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加之当时的贵戚、勋臣多集中于此,购买力集中,可以想见其一时的繁盛。
北京城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心脏就此形成。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充斥着丰富的色彩、音响和气味,使这片街区保持了一种不衰的活力。到明代,大运河终点已然抵达大通桥,中轴线也随之东移,整个北京城呈现向南发展的态势,随着城市机能的变迁,钟鼓楼一带逐渐从喧嚣走向平静。什刹海的湖光水色,开始吸引着京城里豪门权贵、文人墨客的眼光,这一带也因此走向了游赏休闲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到了清代,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尤其钟鼓楼地区是正黄旗和镶黄旗的驻地,有着极强的消费能力,这也更带动起钟鼓楼附近的繁荣发展。
没有了漕运码头汹涌的浮躁和喧闹,钟鼓楼地区开始变得树荫匝地,充满了闲适悠然的趣味。一种新的潮流出现了:一些王公贵族看中这里汇聚着什刹海和积水潭得风望水的气势,纷纷在什刹海边择地建房而居,鼓楼地区越来越热闹。众多的商号也闻风而至,鼓楼前及烟袋斜街陆续出现了很多铺面,钱庄、茶馆、当铺、浴池、烟社、布店、米市、饭庄云集。《红楼梦》中写的“恒舒当铺”,其原型就在鼓楼前。当这一商业区鼎盛之时,王府井、西单等商业街区尚默默无闻。直到今天,我们在地安门外大街上还可以看到不少真正的北京老字号。
七百多年来,旧鼓楼大街的宽度始终没有大的改变
民国初年社会的变革,钟鼓楼之间又变成为百姓设场游玩的所在。西风东渐,钟楼之下开始有了电影院,中国特色的“平民市场”自然也在发展,不少商贩和民间艺人长期活跃于此,把这里变成日趋繁华的民间商肆和娱乐场所,使之有不输于天桥之感,钟鼓楼开始有越来越丰富和独特的精神魅力。朱光潜1936年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的散文《后门大街》中写道:
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百支光烛的电灯,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
民国时期鼓楼商业街的光与影如此耀眼,令人神往。据说在当时,就连前门的谦祥益和豫丰鼻烟铺,都到这里开起了自己的“北号”,吸引了北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鼓楼合义斋、福兴居灌肠等,也都在这里起步扬名四九城;还有个名声在外的鼓楼市场,以物美价廉著称,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尾货市场。新旧商家一茬一茬地交替着,见证着鼓楼和钟楼永不止息的生动脉息。
这个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遗存,留给人们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深刻的生活记忆;“晨钟暮鼓”声虽然只有象征意义,却也成为老北京人记忆中永不消失的场景,它映衬着万家灯火,离合悲欢。
随着天色由晶黄转为银蓝,沉睡了一夜的城市苏醒过来。鼓楼前的大街上店铺林立,各种招幌以独特的样式和泼辣的色彩,在微风中摆动着;骡拉的轿车交错而过,包着铁皮的车轱辘在石板地上轧出刺耳的声响;卖茶汤、豆腐脑、烤白薯的挑贩早已出动自不必说,就是修理匠们,也开始沿着街巷吆喝:“箍桶来!”“收拾锡拉家伙!”……卖花的妇女走入胡同,娇声娇气地叫卖:“芍药花——拣样挑!”故意在鼻子上涂上白粉的“小什不闲”乞丐,打着小钹,伶牙俐齿地挨门乞讨……
这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在自己那部代表作中描述的景象。一部《钟鼓楼》,写尽了钟鼓楼周围四合院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每天听着钟声、鼓声作息的日子,正是他们,书写了一幅北京平民生活的当代画卷。
1961年,刘心武从北京师专毕业,成为钟鼓楼附近中学的一名教师。在柳荫街居住的十几年间,他经常在什刹海、烟袋斜街、鸦儿胡同、花枝胡同一带活动,梦想着自己的事业和爱情。日子久了,老北京的世态人情,他们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慢慢也渗入到他的思维和感觉中,给予了他创作的冲动。钟鼓楼作为亘古不变的时间意象,在他的思想和气质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小说《钟鼓楼》中,钟鼓楼有如一道苍老而悠远的目光,将人的悲欢、历史的变迁,定格在时间的瞳孔里。铸钟的帝王将相早已灰飞烟灭,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而《钟鼓楼》虽然沉默地依身于寂寞的书架,却封存着一种敦厚安详的旧京气韵和人文气质,为这城与人的交融作着历久而弥新的见证。
七百多年来,旧鼓楼大街的宽度始终没有大的改变。从景山上登高北望,在黛色西山阴晴不定的云影之下,北京的各色楼宇在景山脚下静静铺陈,气态高古的鼓钟楼仍在以一种严格的比例,沉默地耸立在中轴线上,仿佛在顽强地证明和凸显着某些事物的重要和庄严。从元代始建以来,曾经历雷击、大火,直到清代仍不断重建修缮,钟鼓楼现在仍安稳地立于大地之上。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中的北京形象,美国《时代》周刊曾把北京钟鼓楼评选为“消失前最值得一看的地方”:如果你有时间,的确应当到鼓楼一带看看。不必有什么旷日持久的乡愁,只需到钟楼与鼓楼之间的地段烤几串羊肉串,喝一碗炒肝,要盘爆肚,或许只是面对某条胡同坐定发呆,看从你身旁淡然走过的居民、低矮平房顶上随风摆动的杂草,以及沧桑老树的影子。屹立几百年的钟鼓楼,自会向你提供历史的模糊残片,让你转眼就从熙来攘往的现代,跳跃到悠远平和的从前。
风渐渐地大了,我听见城楼上的木门木窗被吹得咯咯直响。在一瞬间的恍惚中,钟与鼓再次被击响,那空空荡荡的一唱一和,把远山涂染成了最纯粹的金色,抖落光阴的尘土。钟表里的刻度,静默地周旋于一切之上,那是淹没万物的滔滔洪流,是宇宙神秘的意志。在岁月中日渐古旧的钟鼓楼,会在沉思中被唤起超越时间的崭新生命。钟鼓楼附近的春风秋雨沉静无声,充满着玄象和智性,是对人类永恒时间的吟哦和歌咏。我们在苍茫的水流之上直接面对时光,面对它那宏大、绵延的存在,以逝者如斯的平静和安详,与永恒息息应和。
原文作者 | 刘东黎
摘编 | 安也
编辑 | 王青
导语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