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想象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这样一组关键词——盛唐、长安、诗人、退休官员和农夫,他们会有怎样的生活方式?有没有途径彼此重叠?他们凭借怎样的心态和观念,来进行各自的生活?他们幸福吗?自豪吗?有什么烦恼和希冀?
这样的提问太生活化了,把古人当作邻人并不容易,我们大约只能依靠想象,“脑补”他们的生活情形。当然,一切想象都有现实为基础,普通人想象唐朝人的生活,无非是依靠经年累月获得的经验、知识、审美感觉,例如学过的历史教材,读过的唐诗、唐传奇或是穿越题材的网文,看过的唐代题材的电影电视比如《大明宫词》《妖猫传》之类,听过的“古风”音乐或戏曲,以及我们在现实中的人生阅历与情怀寄托。
《长安未远》也可看作一种对长安生活的“想象”。 所谓“想象长安的方法”,其一,是指历史写作需要有基于当前社会的想象力,作者可以区分古今的变迁与差异,但也要有勾连古今的想象力;其二,是要有意识地借助文学文本的想象,以文学的审美和感悟,带动历史书写。
撰文丨张向荣

《长安未远》,徐畅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
郊区的力量
与许多在历史中灰飞烟灭的繁华都城不同,长安不仅是西汉、大唐这两个伟大皇朝的帝都,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尽管历代长安城的地理位置有变化,昔日的皇宫今日可能是乡村,但其历史基本上是连续的。因此,文化风貌的传承和文献考古的实证,促使围绕着长安的学术研究长盛不衰,正如徐畅在《长安未远》导言中提到的“长安学”。与之呼应的,是今天的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把长安、洛阳等古代名都当作偶像去追慕、崇拜,不同城市的“粉丝”为自己的理想城市争论在古代史上哪个更重要,他们相互攻讦,令人啼笑皆非。
正因为长安的辉煌,才使得其周边显得暗淡无光,甚至令全国其他的城市也不那么重要。大一统时期的帝制中国,“帝都”对全国的资源和人才有很强的集聚和吸收效应,历史的书写和记录也大都围绕着驻在帝都的皇室展开。不妨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期,临淄、邯郸、大梁等许多诸侯大国的都城都比较繁华,此外还有一些因为当时的“国际贸易”而兴盛的商业都市如定陶。尽管这些城市的繁华程度与汉唐长安无法相提并论,但它们彼此没有主次之分,在天下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所以当时的人才不必非要集中到一个城市去求取利禄,而是或在本乡本土活动,或是周游列国自我推销。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许宏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5月。
秦汉建立帝国,这种状况逐渐开始改变。西汉建造长安,最初只是建造了宫殿,连城墙都没有修筑,换言之,秦汉的都城是围绕着宫殿才形成,而不是在城市里建造宫殿。杨宽曾说此时的长安城是“内城性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许宏也说长安“大都无城”(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三联书店2016)。随着汉帝国逐步消除地方诸侯的威胁和郡县制的日益成熟,西汉长安城在面积没有太大变化的前提下,人口和功能建筑迅速扩大,皇宫从长安城的西面“溢出”,建造了建章宫等新宫殿;居民区从长安城的北面“溢出”,在城外形成了人口众多的近郊;同时,西汉长安的“远郊”也就是陵县也变得繁华起来。
秦汉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强迫地方豪杰迁徙到都城周边居住,这样既能消除地方势力的威胁,也能充实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加劳动人口。秦祚日短不提,西汉在连续几代帝王执行这一政策后,长安周边依托皇帝陵墓形成的陵县逐渐成了繁荣的卫星城。许多政要、贵族都把庄园安在这里。这些陵县就构成了西汉长安的郊区,在宽泛的意义上,它们也是长安的一部分。

唐人李思训《京畿瑞雪图》局部。
从汉长安到唐长安,其间经历了东汉移都洛阳、“大一统”局面在南北朝的暂时中断,“帝都”的特征确实有了显著变化。比如唐长安城面积远远大于汉长安城,位置向东南移动(见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年版);再比如,城市规划从秦汉时期以宫殿为核心转变为以坊市为特征。但是,帝都与京畿的结构关系是否仍然如昨?汉长安与三辅陵县,唐长安与畿内,是否也有相似性?那些“五陵轻薄儿”们是否还过着相似的日常生活?
《长安未远》虽然没有对汉唐长安做直接比较,但仍然回答了上述问题。全书的展开基于唐长安与京畿关系的描述,共分为四编。第一编“聚落地理”描述长安京畿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物产以及畿县所辖的乡、里、村。作者的方法主要是在现有研究成果和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新出墓志提到的乡村名称进行考订修补。普通读者除非有特定的兴趣,倒也不必细读,借助文后附表能得其大概,不妨早点移目第二编“户口居民”。

电视剧《大明宫词》(2000)剧照。
这一编在全书中最为显眼,写作也最为漂亮。作者发现,居住在京畿乡村的士、农、工、商以及西域中亚移民,各有进退之法,新任官吏视京畿为仕途的高起点,退休官员则试图在此葆有对朝廷政治的参与度;“体制外”的处士、书生在这里维系着一种与“体制内”的朝廷及贵族若即若离的状态;此处的平民脑子更为活络,鉴于京畿地区耕地数量少,加之与长安的切近,他们往往不安于稼穑,更愿意为官宦阶层出工出力,供应花木,贩卖木炭,搞“第三产业”。在这一编,作者以两章的篇幅重点写了京兆韦氏、杜氏两个望族,以及作为文官诗人的白居易的京畿生活。关于白居易后文还要详谈,这里重点介绍作者对士族京畿生活的考察。
对唐代世家大姓的研究,当然首要聚焦其在朝廷政治舞台上的表现,研究其家族成员出仕情况、是否担任宰辅等高级官职或成为皇亲外戚、家族出现过哪些名宦等等。本书则另辟蹊径,考察士族在京畿的居住及生活。结论指出,尽管士族在长安城内数代为达官显贵,也长期占据大量市坊屋舍居住,但是,京畿仍然是他们失意退守、标榜郡望、经营别业的根据地。换言之,士族们之所以能够维系家族长盛不衰,其秘诀并不仅在于为官朝堂,也在于扎根于京畿的乡村。
作者的这一结论,令我想起了清代小说《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前托梦给王熙凤的教诲:“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不免有一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慨。

电视剧《红楼梦》(1987)剧照。
在此基础上,作者顺利进入到第三编“基层控制”,进一步探讨上述生存方式之所以成立的帝国体制,也就是长安与京畿的权力结构关系。作者以三章的篇幅勾勒出如下图景:一个平民生活在此时此地,既要接受国家机关通过官僚科层和户口制度的有效控制,也要考虑到本乡本土的“地头蛇”,还要小心翼翼地端详“外来户”——你不知道这些陌生人背后是高官显宦还是皇亲国戚乃至皇帝本人。当然,作者的笔下也不乏平民与这些权力的互动,犹如宋怡明在其著作《被统治的艺术》(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版)中,对明代军户与朝廷进行博弈的“日常政治”的描述,唐代长安京畿的小官甚至平民,既有因靠近天子而培养出的越级反映问题“告御状”的不俗能力,也有“皇城根下”睥睨一般官僚的“刁民”特征。
上述第二、三编是本书讨论最精彩,写作亦通俗可读、富有趣味的两部分。最后一编“生活世界”严格说来与前三编的逻辑略显脱节,更像是作者把尚未交代但理应交代的内容做了“打包”汇总,有两章,分别探讨京畿乡村民众的生计,包括家庭收支情况、农桑稼穑等;以及民众的宗教观念和神祇鬼怪。这两章单独阅读倒是颇有趣味的。
重识“文史哲不分家”
“元和元年(806)是白居易在长安的第七年,也是他校书郎任满,三年闲散生活结束,面临下一步选择的时刻。这年春天,他退掉了租住的宅邸,也无心去观赏西明寺、慈恩寺、秘书省的牡丹花,唐昌观的玉蕊花,与密友元稹在永崇坊的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时事……四月,两人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白居易入第四等,二十八日,授盩厔县尉……”
以上这段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古代题材小说的开头,出自《长安未远》探讨白居易在长安京畿居官生活的描述。这段话里,白居易卸任旧职、经选拔转任新职,以及与元稹的交游等重要事件及时间点,都是有史料依据的。不过,作者如何知晓白居易“无心观赏”?这应是作者基于白居易的行迹以及留下的诗歌进行的合理揣测,也可以说是一种“想象”。
作者对白居易在京畿的短暂生涯进行了个案研究,写得摇曳多姿,层层递进,值得把玩。先描写白居易所任职的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的地理风貌,主要是与长安的距离有多远,时人用什么交通工具来进行这段行旅。虽说是京畿,也有一百三十多里,若是单人骑马也需要一天一夜,若是车行则需数日。白居易到任后,看到的还是一座刚刚从兵火里重建的小城,而他的工作主要是判案和迎来送往,“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三年任期里,他数次被“借调”回长安。宦游之外,作者还着重描写白居易亲身参与征税,以及关于民生或者说民不聊生的政见。众所周知,白居易的诗文和政治活动与此大有相关。在描述白居易的京畿生活与政务处理之后,作者的结论落在了贞元、元和这一时期白居易的城乡观念。但这不是作为诗人的白居易,而是一个前途可期、不过眼下只是普通下级官吏、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的年轻人的城乡观念,因此,作者发现此时的白居易一心想回到长安,回到台省,回到帝王身边。他对京畿乡村并没有多深挚的感情,等他真正表现出远离政务、寄娱诗酒的态度,已经是晚年了。

电视剧《白居易》(1994)剧照。
《长安未远》的白居易个案研究,我认为是本书最有趣的章节之一,但据作者在一次访谈中所说,她一度“曾把白居易文提交读书班,大概由于写法‘特异’,问题意识不够明确,并未得到正面评价;而随后也尝试将此文投稿核心刊物,仍遭冷遇。”(见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2021年6月8日:《七个问题|徐畅:从京畿城乡社会的多样性理解唐帝国》)。之所以读者有这样的异见,大概是因为读者的角度和关注点不同。
多年前,我刚读中文系的时候,古代文学老师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文史哲不分家”。但这句话,在古代哲学、古代历史的研究者那里似乎不常听到,盖因这句话委实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而且有趣的是,古代文学在哲学、历史那里,往往只是作为边边角角的史料所用,或者干脆被认为是“小道”而颇不重视;倒是古代文学自己的研究总往哲学思想、历史背景、人物行迹等方面靠拢。文学自身的审美、修辞、风格,除非是做专门的美学史、艺术史之类,很难被史学研究特别是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等所采用,文学研究难以真正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场域。例如,倘若一首诗歌对补充史料很有价值,那么即便写得再差,也会受到重视;许多名诗反倒没有这份“殊荣”。
而另一方面,古代历史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冲击可谓是“摧毁性”的,倘若把人大复印资料里近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拿来看,会发现许多过往的研究在今天很难再令人提起兴趣,那些诸如风格的变迁、审美的特点、文学史的分期等话题都时兴一时,现在基本归于沉寂;至于套用各类西方文艺理论、图解各种“主义”的研究更是令人味同嚼蜡,读这些研究真不如重温几遍文学作品。真正沉淀下来的,更多的是史学和文献研究的成果,比如作家的生平考证、作品的辑佚辨伪等等。当然,这不仅是国内独有,翻阅这一时期的海外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日本,也一样存在类似现象。文与史虽然号称不分家,但“史”好比长安,“文”好比长安的郊外,其地位并不平衡。
在此,这也不禁促使我们思考,“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是否可以有新的领会?文学文本能不能摆脱史料的定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回归文学在古代真实的地位,例如《诗经》,就要将其视作“经学”而非“诗歌总集”;例如汉赋,就要将其视作政治文本,而不是修辞和文字的狂欢。另一个思路,则是阅读《长安未远》里白居易这一章节所给予的启发,就是将文学作为史学研究的翅膀,以文本的审美、诗心的揣测等文心、诗思来升腾历史的书写。
《长安未远》之书名,便取自诗人王建的“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寄广文张博士》)。这首诗在书中不断被引用,是对全书的高度概括。在白居易这一章里,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例如,白居易为居官京畿的宦游生涯写下“最爱近窗卧”“不忆城中春”等闲适的句子,也写下“折腰多苦辛”“簿书堆六曹”等感慨案牍劳形、迎来送往的句子,但最终还是极度眷恋长安,日夜想回到长安,这些相关的诗句未必有何种实证的史料价值,但若借助这些诗歌,深入诗人的内心,以诗人之眼观看当时的世界,对历史的沉思自然别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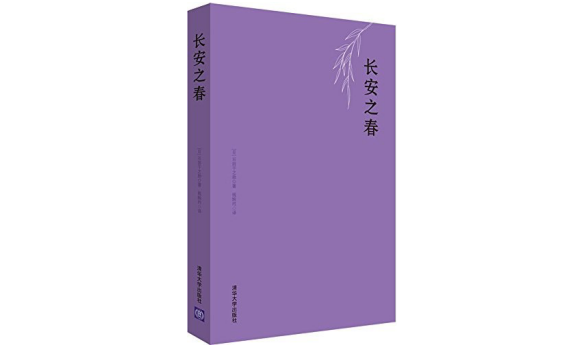
《长安之春》,[日]石田干之助 著,钱婉约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这又令人想起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据说作者是在几乎通读了唐人诗文后才写下这本书,散文的笔触,诗心的感悟,当然可以纳入文学文本;但这又是一本考证唐人风俗生活的史学著作。文与史,在书里结合得相当奇妙。
回到《长安未远》,关于那个最令读者熟知的写新乐府的白居易,作者也探讨了他的这一诗学取向与在京畿亲身从事基层政务的关系。以往谈论白居易,对他关心民生疾苦、开辟新的诗歌语言,多是从其理论主张来谈。而通过本书大致可知,白居易实则是以诗歌书写的方式来介入政治,他有真情实感要抒发,但主要不是发牢骚;他有心要变革诗坛,但不纯粹出于文学革新的理论目的。诗歌,是后人想象诗人生活的途径,在本书也是想象长安的方法。书中这段白居易的个案、人生史,对在古代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之间建立有效且平衡的关联,是很有意义的启发。
《长安未远》首要是一部学术著作,按理说其阅读受众不会很广。但作者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格局之外,着力描摹、呈现、讲述唐代长安及京畿居民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和心态状况。因此,这种在场感、还原感,成了本书得以吸引不少非专业人士的原因。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2019)剧照。
这令人想起近年来流行的一些古装影视剧,比如《长安十二时辰》等,且不提片子本身是否卖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们越来越关注古装剧的服饰、化妆、道具能否做到了精准还原,是否真的符合历史场景。抛开个别观众过于钻牛角尖,忽略了影视剧首要是情节和表演的极端主张,这一现象说明了观众也好,读者也罢,对通俗文艺产品的考究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与之相关的一些专业学术论著自然也能走红。这是值得肯定的现象。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对书写、对叙事有特殊要求的学科。《长安未远》的题材,契合了当下城乡关系、都城及周边关系的社会心态,自然会吸引读者;作者的叙事又特意强调了人生史、心态史的书写,更容易召唤读者置身其中。读者与作者就在这种互动里,形成了良性的阅读与写作。
最后回到本文的主题,所谓“想象长安的方法”,其一,是指历史写作需要有基于当前社会的想象力,作者可以区分古今的变迁与差异,但也要有勾连古今的想象力;其二,是要有意识的借助文学文本的想象,以文学的审美和感悟,带动历史书写。
不过,本书并没有深入提及彼时唐代京畿乡村对长安有怎样的反作用。或者说,京畿仅仅是被动成为长安的影子、使女吗?是否对长安自身的变迁,例如坊市制度的破坏与消亡、长安居民的来源等,也有其特定的影响呢?这一点,本文也无法知晓,只能以读者的身份同样来一番“想象长安”了。
作者 | 张向荣
编辑 | 罗东
校对 | 薛京宁、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