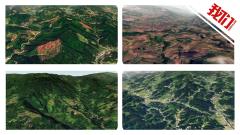9月,丰收的季节。工业化改变了千百年来的农耕方式,联合收割机驶过平坦的大地,粮食在机器出口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的情景,成为人们对丰收的印象。然而,在工业化还未覆盖的青山碧水间,仍能找到那些最原始的农业模式,在那里,人们刀耕火种,艰辛劳作,用双手和脊背获取丰收。其中的一些场景,在今天,被称为“农业文化遗产”。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云南哈尼族梯田的丰收现场。林下有村,村下有田,田间有云,这里有千年传承的人类农业史奇观,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批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涵盖4县12个乡镇82万亩梯田。和自动化大机器相比,哈尼族农户的丰收,格外的艰辛,也格外的珍贵。
哈尼梯田丰收。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拍摄 制作
云上梯田,人背马驮的秋收
9月17日早晨,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几个村民蹲在下山路口的一个棚子下避雨,脚下放着镰刀、编织袋、绳子、鱼篓。雨不太大,但很突然,打破了他们收获的节奏。
又有人走过棚子,脚步并没有停留,冒雨下田,他邀来帮忙收割水稻的亲戚朋友已经聚齐了,不能久等,下一家人还在等着。
箐口村是单一的哈尼族聚集村寨,位于哀牢山南部,村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也是哈尼族梯田文明形成的初期。

9月17日,等待收获的哈尼梯田。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箐口村具有典型的梯田文明特征,寨子建在山上半部,村寨上方,是茂密山林,森林中丰沛的水系,沿着山坡蜿蜒流淌,穿过村寨,浇灌着延伸到山脚的层层梯田,最终汇入山谷。
村口悬崖边一个小广场,是村民们休闲的地方,也可以作为观景台,往下望去,梯田边上深绿的野草,把金黄色的水稻分割成一个个小块,梯田一层层往下延伸,一直延伸到山谷云海中。
林下有村,村下有田,田的下面,则是变幻无方的云海,仿佛梯田就建在云上。有收割完的小块梯田,水光倒映中,也有云彩在摇曳飘荡。

俯瞰梯田里劳作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刚冒雨下地的人们,已经走到了自家的梯田中,远远往下看,只能看到几个灰黑色的小点,在田里慢慢地移动。其实他们的速度并不慢,几个人乃至十多个人排成一排,弯腰挥动镰刀,成熟的水稻被一排排割倒,在田里脱粒。
梯田上的田埂很窄,山路曲折陡峭,不管是汽车还是三轮车,抑或是自行车,都无法通行。脱粒后的稻谷只能通过马驮或人背的方式,运回家里。

收获后的村民人工背运稻谷。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雨一直没停,田里收稻谷的人们已经有了收成,下山的路口,有人回来了,他们背着装满稻谷的编织袋,一根结成圈的绳子,一边套在粮食袋上,另一边则缝着宽布带,套在额头上。背着稻谷的人低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在湿滑的山路上慢慢往上挪。
林田村水,千年农耕文明的奇观
上千年来,哈尼族的人们,都延续着这样的生产方式。研究显示,大约1300年前,哈尼族的祖先迁徙到哀牢山一代,在群山峻林中,筑成家园,在绵延的山坡上,一层层开垦梯田,用千年时间,造就了人类农业史上的奇观。

哈尼梯田,人类农业史上的奇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一位从事保护哈尼梯田文化的当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哈尼族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千年传承中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传统农耕经验,这些经验围绕着梯田系统,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的生态发展模式。
“从山顶到山谷,最上面是森林,其次是村寨,然后是一直延伸而下的梯田,贯穿三者的,则是从山顶上流下的水,它滋养森林,供给人畜、灌溉梯田,最终形成了哈尼梯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循环生态的农业系统,”当地梯田管委会副主任崔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哀牢山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博物馆展示的资料显示,哈尼梯田处在亚热带山高谷深的深切割中山区地带,海拔高度从144米到2939.6米。2000多米的海拔落差中,山谷的热空气上升,在山顶形成云雾和降水,滋养了茂密的森林,形成了丰沛的水系,这些森林中的水,终年不断地从山顶流淌到山谷,为水稻种植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
崔尹工作的地方,就在距离箐口村不远的哈尼梯田博物馆中,博物馆并不在城市里,而是建在山坡梯田和森林的交界处。
这也是所有哈尼族村寨选址建设的模式,在漫长的历史中,哈尼族人在山顶森林的下面,寻找相对平坦、且水源充足的地方,建成了许许多多的村寨,并依托村寨,开垦出无以计数的梯田,然后引入山上的流水,灌溉梯田,把蛮荒中的大山,变成滋养后代的良田。

在大山中开垦出的良田。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这样的奇观,放在全球,也堪称奇迹。2010年6月,哈尼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6月,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5处世界遗产。
这是一处庞大的遗产。仅“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就包括红河州的元阳县、绿春县、红河县、金平县等4县12个乡镇,梯田总面积约82万亩。其中,元阳县有19万亩左右,除此之外,有些未列入保护区的地方,同样还保留着大量梯田。
梯田劳作,用最传统的方式生产
接近中午,风停雨霁,阳光普照,四周大山上的梯田中,都是水稻金黄色的光芒。
61岁的李有华,戴着一顶窄檐帽子,穿着带有背带的防水雨裤,扛着打谷工具,从家里出来沿山路一路往下,和他一起的还有妻子和三个亲戚。

李有华站在金黄的稻田中。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三个亲戚是来帮忙的,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习俗,每到农忙,几家亲戚一起,互助合作,在最快的时间里完成秋收。
海拔落差2000多米的梯田,水稻成熟的时间并不相同,这为村民们的互助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几家人联合,从山下往山上收,每一家都不会错过季节。
来帮忙的三个人中,有李有华妻子的姐姐和姐夫,他们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过去许多年中,两家人一直合作种地,从3、4月份犁地插秧,到9月收获。
合作耕种的人们,也有分工,割稻子的主要是女性,脱粒的主要是男人们,打谷机是一个三部分组合而成的简易农具,底部一个浅浅的长方形盒子,盒子的两边放着两块倾斜的挡板。
前方割稻子的人,把割好的水稻成捆放在割完的稻茬上,后面的男人,抱起稻捆,用力在盒子里摔打,成熟的稻谷飞溅,被挡板挡住,落在盒子里。当地人把收割水稻叫做“打谷子”,或许就是源于此。

打谷子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李有华和姐夫李振远共用一台打谷机,两个人站在长方形盒子的两头,同时摔打“谷穗”,很快,盒子就装满了。同时,两人的帽子、脸、胳膊、衣服上都溅满了泥点。
打完一小段距离的稻谷,李有华他们就会推着打谷机往前,打谷机底面平滑,可以在放干水后的泥上滑行,但人不能滑行,一脚下去,腿就陷入齐膝深的泥中。
稻黄鱼肥,和大自然共生的人们
距离李有华家的稻田不远处,另一家人也在打谷子,这里人更多一点,接近10个人,4个男人用两台打谷机脱粒,速度更快。半个下午的工夫,一块长长的梯田就收完了,一个个装满稻谷的编织袋被马驮上山,打谷子的人们,随后转战下一块地。

打好的谷子用马驮走。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62岁的卢长生坐在田埂上休息,正在收割的,不是他的稻田,而是侄子的,田里劳作的,多是来帮忙的。
不远处的田埂上,放着一个鱼篓,里面已经装了半篓鱼。这些鱼是插秧后放养在稻田里的,这种稻鱼共生的模式,在哈尼梯田中随处可见,因为不打农药,也不用化肥,所以梯田水很适合养鱼。
发现鱼的都是前方割稻子的人,每过一会儿,就有人喊,“来拿鱼”。后方打谷子的人,则暂时停下来,拿起放在田边水渠或水坑里的鱼篓,踩着泥泞走到前面,装好鱼,再放回水中,一天的劳作结束后,这些鱼仍然是鲜活的,拿回家,晚上的餐桌上,就会多一道“稻花鱼”。
稻田里的鱼,以水中的虫子为生,对防治水稻虫害有一定好处。但也因为不投喂,所以产量不高,鱼普遍都不大,最大的有一两斤,更多的只有巴掌大。

小朋友捧起稻花鱼。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这样的稻花鱼在外面很受欢迎,最贵的时候,可以卖到每斤六七十元,但因为产量低,外销的并不多。
李有华没打算出售这些稻花鱼,他准备留着自己吃。李有华有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留下4个上学的孙子孙女,由李有华夫妻照看,这些鱼,祖孙6口人,其实也吃不了多久。
林田村水、高山奇观、稻鱼共生……李有华他们,并不懂得这些词汇,或者听说过,但并没有思考过它们的意义。
曾经在元阳考察和调研当地梯田文化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河告诉记者,“在当地,哈尼族人在梯田农业生产中,构建了一整套生活方式、生产秩序、节日礼俗,并且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文化的连续性。在旁观者看来,这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对他们来说,这些生产生活方式,这些礼俗文化,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
“遗产”里种田的人,一直在慢慢变老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还延续着传统的生活,现代化的大潮,也在影响深山梯田中的人们。
从箐口村的山路往下,沿路两侧的梯田中,打谷子的人,大部分都是老人,很少看到年轻人。他们基本上都和李有华的两个儿子一样,在外务工,并没有回来。卢长生告诉记者,年轻人基本不种地,也不会种。甚至卢长生自己,也曾在外打工,近几年才回乡。
36岁的李华,是极少数回乡秋收的年轻人之一。李华和丈夫一直在外打工,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在城里。家里只有公公婆婆,因为年纪太大,无法下地劳动,只能他们回来打谷子。但回来的只有李华一个人,她的丈夫和孩子仍留在城市里。
李华家里的水稻,前两天就收完了,和李有华他们不一样,李华没有找亲戚帮忙,因为她要继续回城上班,无法回帮亲戚。但李华也有自己的方法,雇人。

田里收稻子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雇一个人打谷子,一天100-120元左右,如果管饭,价格还要低一点儿。这样的市场,在绵延无尽的大山和梯田中,出现的时间不短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样的方式。和互相合作帮助的方式相比,拿钱雇人,更简单,也更直接,对外出务工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经济的。
27岁的马伟,也选择了雇人。马伟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以前马伟一直在深圳打工,今年因为做了一个手术,所以在家休息。母亲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承担耕种的劳动强度,尤其是秋收。马伟告诉记者,不光可以雇人收割,驮稻谷上山的马匹,也可以雇,按袋算,每袋10元左右。
下午4点左右,马伟家的梯田收完了,受雇的人走了,他母亲和另外一个来帮忙的亲戚往山上背稻谷,马伟不能干重活儿,只是帮忙拿着镰刀、鱼篓上山,脚上的运动鞋干净、洁白,粉色的外套和黑色的裤子上,也几乎没有泥点儿。
“这些年来,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哈尼梯田,保护他们的农业文化,包括对森林生态的保护、哈尼族村寨的修葺维护、山林水系的养护等,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崔尹也表示,哈尼梯田的保护,同样面临着农业劳动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多,愿意务农、会务农的越来越少。
遗产延续,需要外力帮助
有人在尝试改变。在当地的一家粮食加工厂中,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把哈尼梯田中特有的红米收购过来,加工成梯田特产,这可以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他们还在尝试以订单农业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指导农民生产,帮助农民以更好的价格销售粮食。但即便如此,也无法真正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基地里的农户,或接受他们的订单进行种植的,也同样是老人居多。
“人天然会追求更美好、更富裕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仅凭农业本身,已经不能为乡村居民提供富裕的生活,也无法承担乡村公共设施改善的成本,哈尼梯田这样的农业遗产,确实保留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也要看到,艰苦的劳动,已经不成比例的收入,越来越难吸引人留下,强求他们留下,既不可能,也不公平。”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保护文化遗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想要有效地保护,还要引入外部力量,比如政府的投入、通过旅游吸引外部的资金人才。”
在李河看来,这些仍旧保留着传统农耕方式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不仅仅只是当地人的生活形态,“在以前,那里的文化,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但现在,除了仍是他们的生活之外,还有展示传承的意义。哈尼梯田所负载的文明和历史、文化和记忆,可以也必须要转型。”
李有华、卢长生他们,也正处在转型之中。
下午6点半左右,夕阳西下,落日最后的余晖散入稻田,李有华他们放下镰刀,撤出打谷机,背着稻谷上山回家。

夕阳西下,村里背稻谷回家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身处元阳县梯田的中心区,箐口村在此前已经完成了村庄整理,家家户户的小楼整理得干净整洁,弯弯曲曲、高低错落的巷子里,石板路和石头台阶平平整整。在受疫情影响之前,这里是梯田旅游的核心区域之一,村里有人开客栈,小超市、小卖部也比一般的村庄更多。
穿过半个村寨,把稻谷放在楼上,妻子送亲戚回家,李有华在门口收拾带回来的鱼,孙子也在旁边帮忙。一个多小时后,东西都收拾好了,妻子做好了晚饭,油炸的稻花鱼摆上桌子,祖孙6人坐在桌边,这是一顿丰收季的晚饭,简单,但又有些特殊。李有华不知道这片梯田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但他知道,桌子旁边的4个孙子孙女,长大后很可能不会和他一样,还要挑着肥料下田,背着稻谷上山,他们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有更好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