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货们的十一假期,却是嘴巴的加班周。朋友宴席上的佳肴、鄙陋小巷的小吃、自己做的拿手菜……这个假期,最让你忘不了的美食记忆是什么呢?
我们喜爱美食,因为对许多人来说,食物与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有某种特殊的关联——它可以提供特殊的记忆、生活中的慰藉和掌控感,乃至个人的文化认同……换句话说,食物仿佛一枚特别的“碎片”,从中可以涌现出一个人的全部的“生活世界”。
然而,今天的食物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正在被打破。“现在很多食物缺少阳光和乡愁的味道”,我们常常听到类似的感慨。与这种危机相伴而行的是,食物的呈现方式也逐渐趋向“奇观化”:一方面,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网红餐厅”的盛景图像,纵然它们往往不能提供优质的饮食体验,却也总有人愿意为之买单;另一方面,那些曾默默无闻,作为计划经济孑遗和公有制象征的食堂也在近期频繁作为奇观出现:医院、机关单位的食堂制作的月饼在今年中秋节期间受到追捧,甚至被哄抢抬价和仿冒……
本期读刊,我们和大家聊聊食物在味觉享受之外的独特意义。在下文中,作者借助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灵韵”思想,分析食物如何在前现代社会建立起人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为什么这种联系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淡薄;而食物呈现上愈演愈烈的“奇观化”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
联结世界的方式:
为什么我们总能在食物中找到慰藉?
“食物是很安全的享受,人们可以毫无恐惧地在其中放松自己,在其中找到自由与慰藉。”《鱼翅与花椒》的作者扶霞·邓洛普曾这样说。
在笔者看来,食物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主要有两种体现方式。第一种方式如邓洛普所说,食物部分充当了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的维系者——让人们意识到,生活世界是安宁的,可掌控的。

《鱼翅与花椒》,[英] 扶霞·邓洛普著,何雨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版。
如果说在第一种情况下,食物支撑起的是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食物可以与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如特定的时空地域、记忆片段,乃至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关联。例如,《晋书·张翰传》便提到“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正因为鲈鱼和“秋风”“吴中”之间的关联,才有了“莼鲈之思”的典故。而鲁迅的文章《社戏》则将食物与童年往事,幼时玩伴联系在了一起。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食物常常能与我们与世界之间建立起特殊的关联,可能是一段儿时的故乡回忆,或是建立一种文化认同,带来心灵的慰藉。食物的这种特殊性,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食物的“灵韵”。
“灵韵”是本雅明用来谈论艺术品的概念。 在本雅明眼中,灵韵关涉到作品的“语境”,意味着作品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艺术品的诞生、存续和展示都离不开独特的语境,而灵韵正是被这种语境所造就。例如,某一大师的画作独一无二,任何复制品都无法取代本尊;这是因为大师只对原作倾注了他的创造力,也只有原作,才在其诞生、存续和展示的过程中经历了独特的历史。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瓦尔特·本雅明著,李伟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在这种意义上,本雅明用以形容艺术的“灵韵”同样适合于食物。几乎在所有人眼中,总有一些食物承载了特殊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来自于它们与人们生活世界之间的具体关联。由此,这些食物具有了独特的、区别于其他食物的灵韵。
并非所有的食物都同等地具有“灵韵”,具备“灵韵”的食物往往也具有特殊性。例如,笔者的祖母喜欢在西红柿鸡蛋汤中加入裹着蛋清的肉饼,而这样的做法并不常见。正因如此,笔者只有从这样的西红柿蛋汤中才能感受到“灵韵”,而餐馆中其他做法的蛋汤都仅仅是西红柿蛋汤而已。
如果说灵韵以特殊的食物为载体,并具有多样的体现形式,那么,又是什么赋予食物以“灵韵”呢?这关系到传统社会的食物生产方式。
首先,在传统的食物生产模式中,人参与了食物生产的大部分流程——从食物的采购,到原材料的制备,再到成品的制成。某些时候人们甚至会参与食物的种植和养殖。正因参与了食物生产的全过程,人们才可能从中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相比之下,当下生活中的许多工作已然在分工体系下被拆解得七零八落。正如卢卡奇所说,在高度分工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对工作全流程的“掌控”。同时,从事简单重复的机械运动,也难以令人们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正因如此,食物维系了一种难得的“整体”感,部分地使人免于意义的缺失和经验的支离破碎,“粘贴”起了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
其次,传统的食品生产大都是在自然的共同体——家庭和传统社群中进行的。黑格尔认为它们“自然的伦理实体”——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家庭成员以及社群成员之间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正因如此,自然共同体的成员们会在制作、享受食品的过程中不分彼此,亲密合作,共同分享。如果说当下的生产分工,如卢卡奇所指出的,会带来一种“静观”和“孤独”的态度:每个人仅仅完成自己的部分,对他人的活动漠不关心——那么在自然共同体中,情况恰恰相反,人们集体参与食物的制作,分享最终的成果。即便有一些成员不直接以劳动的方式参与,他们的态度也绝非“静观”。因此,食物与特定的人物、记忆发生了关联。

Jennifer A. Jordan, Edible Memory: The Lure of Heirloom Tomatoes and Other Forgotten Foods, 201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另外,自然共同体的“特殊性”也在食物中得到了体现。一方面,由于置身特定的环境,自然共同体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色。正因如此,食物会带有“乡愁”的味道。此外,自然共同体没有采用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它们的食品生产也非是为了满足普遍化的商业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具体成员的各不相同的“口味”。因此,自然共同体制作的食品,从制作方法到口味,都是特殊的,每一餐都是“独一无二”的。
由此,在传统的食品生产方式中,食物之“灵韵”的各种特点都能得到解释: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带来了掌控感;生产方式的自然共同体属性则揭示了食物与生活世界何以发生联系。然而,恰恰在当下,随着食品生产方式的调整,食物的“灵韵”也处在危险之中。

美食类纪录片《沸腾吧火锅》剧照。
当食物与生活世界脱节:
标准化生产、景观化外形、人造“灵韵”运动
正如人们所感受到的,食物的“灵韵”处在危险之中,而“灵韵”的消逝又首先来自于传统食物生产方式的消逝。
在当下,食物的生产几乎也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本雅明语),大多数餐厅都采用了标准化的食物配比和调味方式,甚至直接以料理包,或中央厨房提供餐食。这些做法旨在以标准化,大规模的生产来尽可能适应标准化,普遍化的“口味”,进而塑造标准化、普遍化的“口味”。
由此,人们一方面不再参与食品生产与制作的流程。不仅消费者变成了单纯的“食客”,就连生产者也未必参与了食物产生的全部流程,而是仅负责其中的某一步骤。因此,这样的制作流程不再为人们的自我实现和掌控感留下空间。相反,人们对食物的态度变成了单纯的“静观”和“吞咽”,更因为与生产流程的分离,人们对于经过重重不透明流程,最终到达自己手中的食物反而多了一份“猜忌”和“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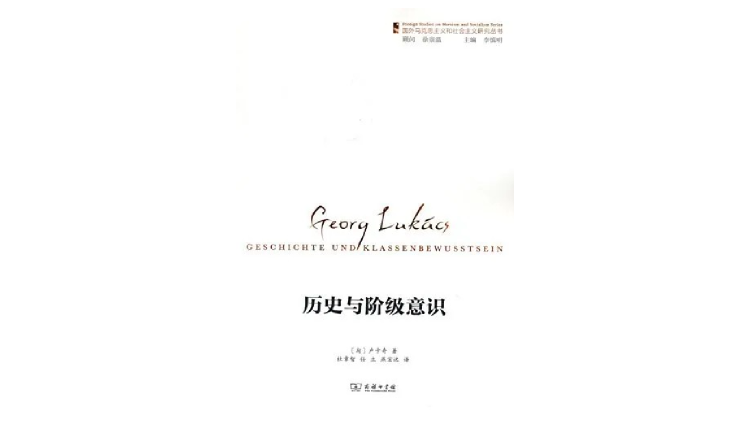
《历史与阶级意识》,(匈)卢卡奇著, 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其次,以如此方式生产的食物也不再针对具体的人和他的“口味”。相反,这样批量化制作的菜品旨在满足更加普遍化,标准化的味蕾。如果说食品的灵韵本身也需要视频的独特性来承担,那么在机械复制的时代,这样的“灵韵”也随之消失。
正如艺术的机械复制时代消解了艺术品的“灵韵”,食物“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也令“灵韵”处在危险之中,令食物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在当下,当食物向人们呈现自身时,它们不再是一枚浓缩了生活世界的碎片,而是一幅充满诱惑的“景观”。在这样的“景观”中,“灵韵”本身也常常被挪用为一种卖点和噱头,被收编为消费主义的符号。
对于食物的“景观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景观化”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食物本身转移到符号意义和“表征形式”上。例如,奶茶店雇人排队,打造“门庭若市”的假象在业内已然是“标准动作”;而一些“网红日料”更是营造视觉盛景的好手:将切片的牛肉堆成红白相间的小山(虽然肉片之下小山主体部分是冰块);菜单上满满铺排着高清、高饱和的美食特写;另一些网红餐厅更是将“乘船用餐”“汉服拍照”作为卖点……而在种种景观中,制造“灵韵”往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某日本料理商家宣传图。
一个例子是,不少糕点店铺都青睐“手作”的卖点。仿佛在“手作”的标签之下,每一份商品都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属性,承载着独特的匠心和文化内涵。此外,带有灵韵的食物往往承载地方性文化,而这些地域文化的符号也被广泛挪用:湘菜馆子里必定装点着成串的红辣椒,港式茶餐厅里也少不了写着繁体字样的招牌……仿佛通过符号的堆砌,它们所售卖的菜品也重新获得了灵韵,恢复了与生活世界的关联。
然而,恰恰在这种制造“灵韵”的运动之下,掩藏着一种自我颠覆的逻辑。无论如何堆砌符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些餐厅注定无法留住真正意义上的“灵韵”。因此,越是吸引那些为追寻“灵韵”而来的食客,这些食客也就越容易在这些符号的“提醒”下意识到灵韵的丧失。由此,食客并没有真正被“伪造”的“灵韵”“遮蔽”,而仅仅是出于无奈:身在异乡的他们或许依然会前往这些餐厅,在各色符号中享受一场置身生活世界的梦境,但对于“灵韵”的丧失,他们也同样心知肚明。

《新京报》曾爆料,网红“老月饼”的生产环境十分糟糕。
摇摆在消费主义与生活世界之间:
食堂月饼为什么受欢迎?
被“制造”的“灵韵”之所以被人接受,一方面是由于“景观”确实俘获了人们的眼球,甚或是部分地塑造了人们看待食物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许多人接受被制造的灵韵也是无奈之举。正因无奈,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挽留真正的灵韵。在这种姿态的驱使下,一种新的消费趋势开始出现:近段时间,单位食堂开始广受追捧:例如在中秋之际,人们惊讶地发现,相较于被刻意打造成景观的网红月饼,这些单位食堂制作的、带有计划经济孑遗和公有制痕迹的月饼用料扎实,价格实惠。因此颇受欢迎。
的确,作为公有制的孑遗,食堂并不需要像一般餐厅那样,在成本-营收的问题上秉持着严格的理性计算精神斤斤计较,甚至牺牲食品安全来实现成本管控;更无需将自身“景观化”,进而虚增自身用于营销宣传的资源。正因如此,食堂可以做到“安全放心”,也可以做到“价廉物美”。
但更有趣的是,除却价廉物美,食堂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灵韵“的守护者,部分地恢复人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以校园食堂为例,在高校食堂中,食堂师傅属于“职工”的序列,他们与学生的交往远比单纯的商品提供者与消费者更加密切:很多时候,学校会创造机会,让师傅和学生一起参加晨跑、读书等活动,一些地域性学生协会也会与当地籍贯的食堂师傅有所联络,即便是在打饭购餐的过程中,一些比较外向的师傅也会乐意与同学们攀谈。而更加频繁,日常化的交流使得学生的个性化口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例如,很多同学都会回忆,一些常去的窗口的师傅会认识自己,甚至记得自己的饮食偏好。同时,学生自己也可以在特定的时机参与到食物的制备过程中,不少高校都有后厨参观、厨艺比赛等活动。

带有鲜明学校特色的的药膳月饼。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食堂所在的校园或单位本身便构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生活世界,而食堂作为这一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所生产的食物也自然而然地与之发生了关联。在这些食物中,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充实,而没有被抽象为普遍的、标准化的商品交换关系。
这样的食堂模式如今已不那么常见。但毫无疑问,在许多年前,这样的就餐模式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因此,“食堂”的名号在今天仍然能唤起人们的回忆,乃至一种“归乡感”——食堂制作的食物足够可靠,甚至可以从中构筑出人和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关联。因此,对于有过食堂回忆的人而言,食堂在今天依然带有“灵韵”;而即便对于没有这类回忆的人来说,食堂的价廉物美也足以成为一种吸引力。
然而,这样的文化符号在今天也处在“争夺”的焦点之中,在很多时候同样会遭到“收编”。例如,许多餐厅热衷于将自己命名为“XX公社”。它们用上世纪风格的搪瓷杯,领袖画像,宣传画,乃至颇具时代感的服务员着装来装点自己,尝试营造某种“公社感”。同时,单位食堂制作的月饼也会在持续的营销曝光下成为新的景观,并被哄抬出远超所值的高价。正如今年中秋节火爆的“精神饼”,这款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院食堂推出的月饼,反而因为它与“精神卫生”之间的联系成为了狂欢的焦点,甚至被冠以“精神饼”之名,遭到炒作哄抢。因此,在追捧食堂之时,人们依然摇摆在“灵韵”与消费主义构筑的景观之间。

成为网红的“精神饼”。
阿格妮丝·赫勒曾提及现代性之下“故乡”的消逝,而食物之“灵韵”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一过程的注脚。如果说古人还可以在“莼鲈之思”中借食物的灵韵找到自己与故乡的联系,那么在当下,灵韵的消逝不免令人发出更深层的,“何以为家”的叹息。
作者 | 谢廷玉
编辑 |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