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剧《鱿鱼游戏》成了爆款。为何这部剧会爆火呢?
它虚构了一个封闭环境中的比赛系统,乍看是对“一二三木头人”、拔河、打弹珠等童年游戏的复刻,实际上这个比赛系统却借此进行了残酷的杀戮竞赛。

《鱿鱼游戏》剧照。
于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像主角成奇勋这样的小人物刚开始都是抱着半好奇半侥幸的心态参与的,可是加入比赛系统后,逐渐做出种种违反道德、背离伦理的举动。例如,骗朋友去送死,欺负病弱的老人,甚至亲自将深爱的妻子推向绝路……
有时,系统的规则也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惨剧。比如在赛前默许乃至鼓励参赛者互相残杀,先淘汰掉其中的弱者,因为他们不适应之后的比赛。这显然就有纳粹暴行的影子。
诸如此类的剧情盖过了故事中闪现过的温情与关怀,令观众在震惊之余不免也反躬自省,思考为什么普通人会配合系统,制造出这样的邪恶。也让普通人再次反思:我们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路西法实验”的启示:
好学生也可能变身恶魔
对于邪恶,人们往往较少深思,因为它离日常生活似乎很远。
什么是邪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为之下的定义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
为了“探索人类本质的黑暗面”,津巴多设计了极具争议性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把一幢教学楼改造成监狱,并让学生志愿者分别扮演狱警与囚犯。三十多年后,在《路西法效应》一书中,津巴多还原并剖析了整个实验。

《路西法效应》,作者:[美] 菲利普·津巴多,译者:孙佩/陈雅馨,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10月。
原来当时让他深感吃惊的是,预计两周的实验进程还不到一半,事态已经接近失控,出现了严重的霸凌、虐待等现象。原本崇尚“爱与和平”的学生,一旦被赋予狱警的身份,纷纷变成残暴的恶魔,以至于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而那些被分到犯人角色的学生,刚开始还不甚情愿,很快便顺从地融入角色,不再反抗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
这一实验结果使津巴多把焦点指向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人类历史上为何会出现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等暴行。他总结道,邪恶并不是某些坏人或暴君的专利,恶劣的环境会产生潜在危害,能够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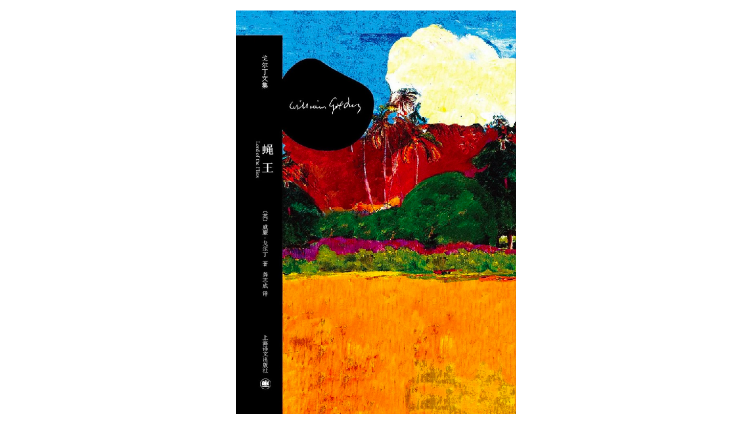
《蝇王》,作者:[英]戈尔丁,译者:龚志成,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7月。
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蝇王》早已设想过,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即使一群儿童也可能建立起惊人的暴政,乃至残忍地杀死同伴。类似地,津巴多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纳粹大屠杀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看似和蔼的邻居也有可能成为杀人狂。
然而“恶劣的环境”并非从天而降。它是如何生成的?或者,用津巴多的话来说,“谁有权力规划设计出这个行为环境,并且用特殊方式维持它的运作?”在《鱿鱼游戏》中,系统的幕后黑手是看透人性幽暗的财阀,以及有着病态爱好的全球权贵——他们头戴面具,在酒池肉林中欣赏杀戮。这样的设定过于简单和脸谱化,也许便于普通观众理解剧情,却无益于深入揭示主题。

《鱿鱼游戏》剧照。
游戏测试人性:
在虚拟世界里学会思考道德、警惕邪恶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只需换一个视角便能发现,身为《鱿鱼游戏》观众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这场生存游戏的参与者。“希望看到更残忍的厮杀”、“两个只能活一个,迫切想知道那对夫妻档会怎么做”,这些都是观剧时的常见心态。创作者利用了这种心态折射的幽暗,令观众照见自己人性中的局限。
也许《鱿鱼游戏》还只是看破不说破,名导迈克尔·哈内克的《趣味游戏》则更直白地解释了上述这点。打破第四面墙的哈内克不断挑衅观众,让滥施暴力的凶手直接转过头来和观众对话,并通过任意改变剧情走向、几乎是嘲讽式地迫使观众承认自己对这种(尽管只存在于画面上的)暴力也是认可的,至少是欲拒还迎的。

《趣味游戏》剧照,剧中演员会打破“第四面墙”挑衅观众。
比起《鱿鱼游戏》,《趣味游戏》与观众建立起更直接的互动,以此搭建了一个由影片和观众共同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观众会感受到自己人性的底线一再被测试。不知是否因为激怒了包含影评人在内的观众,《趣味游戏》当年的票房相当糟糕。
如果说大多数影视作品囿于传统形式,与受众的互动尚且有限,那么电子游戏的风行恰好补足了前者的这一弱点。由于其自带的交互属性,电子游戏为玩家体验各种系统开辟了一条通途。许多电子游戏都竞相在剧情和游戏方式中融入哲学思考,那些难以取舍、几近残酷的道德选择纷纷被丢到玩家面前。只要沉浸感做得出色,玩家就会被放置在类似成奇勋们的位置上,仿佛得到一张加入“鱿鱼游戏”的号码牌。
在某些开放世界的游戏中,玩家可以随便殴打或者抢劫路上的NPC,并轻易逃脱惩罚;当然,你也可以严格要求自己从头到尾不做任何坏事,只是这并不会给角色带来任何实质性奖励。在这样的系统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遵从内心的道德律——即使那些NPC做得像《失控玩家》的主人公那样栩栩如生。

《失控玩家》剧照。
让人更直接体会道德困境的是《这是我的战争》。游戏背景设置在战争末期,炮火令城市几乎成了废墟。玩家作为幸存的平民,要想方设法使自己和亲友活下去,一直撑到若干天后战争结束。由于物资匮乏,角色很容易陷入饥饿、疾病、寒冷、抑郁等各种负面状态,所以获取生存物资成了游戏中最重要的行为。
问题是,战争中物资是稀缺品。于是,一位母亲在风雪中敲门,跪求你把仅剩的食物送给她即将饿死的孩子;或是你的亲人病势沉重,隔壁街区的老人恰好有一颗保命药,但他不会给你,除非你偷窃或者使用暴力,无论如何,老人失去了药就意味着他注定会因你的行为而病死……玩家会频频遇到这样的随机事件,没有一个决定是轻松的。
被戏称作“致郁良方”的《这是我的战争》试图探讨一个沉重的命题,即:在远离正常社会秩序的极端系统里,如若提高生存概率的代价必然是作恶、牺牲他人,那么,人性中悲悯、克制、正义的那些部分,与人类生存本能间的冲突,究竟是否有调和的可能?在游戏中做出何种选择,本身只是玩家采取的游戏策略的一部分,不必经受道德的诘问;但经由虚拟世界学会拥抱良善、警惕邪恶,才是游戏过程所附赠的更宝贵的心得。
拒绝参加游戏的人:
抵制不人道的指令是英雄之举
《鱿鱼游戏》像一记警钟,提醒观众勿忘正视人性的深渊。在它身上,人们不难窥见其他反乌托邦作品的影子。例如十年前的《饥饿游戏》,二十年前的《大逃杀》,都是此类影视的经典。
三十年前在中国公映过的美国电影《过关斩将》曾因惊悚与刺激程度而轰动一时,它火力全开,批判娱乐至死的电视工业。施瓦辛格主演了一个孤胆英雄,一路击败“冰场杀手”、“电锯狂人”等以屠杀为乐的对手。系统在此以综艺节目的形式出现,假借娱乐和竞赛的名义对人实施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最终将血腥的杀戮合理化。所以,《过关斩将》也很可能是《鱿鱼游戏》的灵感来源。

《过关斩将》电影剧照。
上述作品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即主角在关键时刻都选择冒生命危险,去抵制系统所制定的规则。就像P.K.14乐队一首歌曲的名字,他们都是“拒绝参加游戏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份拒绝,才得以部分或完整地保留了人性中的良善。津巴多的研究显示,身处恶劣的系统中,大多数人或是顺从、屈从,或是被劝服、受诱惑而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始终有少数人拒绝服从不符合人道的指令。
和平庸之恶一样,平庸的英雄之举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你当然可以跟随系统,跟随权威,跟随大流,那样看似最安全和有利;但也始终可以选择遵从内心的道德,对系统说不。在这方面,独立游戏《遗忘之城》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它发生在一座古罗马城市中,这里的市民相信神明制订的“黄金法则”——即“一人作恶,众人受难”(这个设定的灵感源自罗马军队中通行的“十一抽杀律”)——统治着他们的生活。

《鱿鱼游戏》剧照。
问题是,对什么是“恶”,黄金法则并没有具体解释。于是,这个小型社会演变成了一个森严的系统,大多数人非但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也谨防身边有人做出逾矩的举动。但即使如此,仍有些人试图打擦边球。玩家也必须不断试探黄金法则的底线何在,才能在一次次失败后找到这座城市的真相。
这个故事似乎表明,即使一个被设定的环境看似严酷无比,身处其中的人们仍有机会设法找到空隙,对系统发出质疑和挑战。在今天的世界中,这样的启示仍具现实价值。
作者 | 张哲
编辑 | 走走;青青子
校对 | 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