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读诗:细雨湿流光》,作者:三书,版本: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
三书自述
我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
马栗树开花的时候,我收到编辑的约稿短信,长长的一段话,诚意满满,铺在手机屏幕上。
时隔数年,编辑还记得并信任我,这让我感动,又感到意外。不敢自诩为诗评,但重读古诗词,写个人化的读诗笔记,的确是我近年来一直想做的事。为什么找我,一个既无名师加持、亦无教授光环的小人物?
我没有问编辑,而是满口答应下来。既然找我,必独具慧眼,我要做的就是认真。相信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事做好,就无所谓大事小事。
我问马栗塔状的花簇:“你们的美是用来享受,文学也是如此,对吗?”它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就这样,去年四月,我们的栏目启动了,编辑已取好名字——周末读诗。又是周末,又是读诗,多么安逸的时光,能否成为一个可供神游的远方?我们期待着。
读什么诗,怎么读,编辑让我自己决定,要求是每期大约三千字。找诗不难,难的是好诗太多,一时不知先读哪首,就好像写一个故事时,你想同时从所有地方开始。
多年来,我有抄诗的习惯,并非坚持,而是和饮食嗜好一样,抄诗已成为生命的本能需要。知足常乐,这句规劝可用于节制物欲,但对于精神体验,我们最好还是贪婪一点。遇到心爱的诗,我不仅会把它背下来据为己有,更要抄在本子上,一遍一遍地咀嚼,好诗是可以吃的。特别是汉语诗,字词的音和形同样重要,耳聆其音目视其形,会调动你更丰富的联想。
从私人手抄本上开始选,从我最爱的那些诗开始。我想,这么好的诗,读者应该也会喜欢的,万一不喜欢,那就是我读的方法不对,或者我的文字太乏味。所以,责任和压力都在我这边。
怎么读?我的理论是凭直觉。我自己怎么爱一首诗,就怎么把这首诗分享给读者,不是对诗的阐释和理解,而是分享对诗的体验。读诗应当是审美的过程,应当以诗的感觉读诗,给读者启发和灵感,以及适当的留白。
定性之后,我对自己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写在小纸片上,每次写的时候,就摊在面前作为提醒,避免写作自动打滑,避免说出空话套话:1、说人话,说自己的话。2、写最重要、最本质的话。3、向潜意识挖掘,写未知的。
这三点提醒不仅对读诗,对所有的写作都适用,而且事实证明也很管用。至少写的时候可以监视自己,最大限度地减少偏离文本的漫天跑马,或不着边际的鸡汤八卦。
读诗是美学体验,基于这一认知,读的时候尽量撇开文学史,非必要不唠叨作家生平。你可以爱一首诗而不必懂它,更可与一首诗心有灵犀而不必调查作者的经历。
对于从小被灌输的八股式读法,诸如“反映了……”“抒发了……之情”“采用了……手法(手段)”“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等等,相信我们都深恶痛绝。我们感觉被教条化,感觉自己没有被表达,甚至感觉被侮辱了。
还古诗一个真面目,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除了上述的粗暴读法,古诗的现代性也尚未被充分挖掘。现代性不仅是用现代语言书写现代经验,也应当包括对古诗感受力的重新激活,用现代的视角使其焕发新的光彩,并将古诗转化为我们自身经验的一部分。用诗人张枣的话说,就是把传统当作先锋来处理,寻找原型汉语人和集体记忆。
如果从能量层面来理解,我们就更会明白,古诗并不在过去,而是活在当下(包括未来),因为语言文字与诗人心灵的能量是超越时空的。读诗就是回到当下,感受诗的能量场,让其振动发生在你身上。当它发生时,你就会感到幸福,好像回忆起被遗忘的另一个人生。
写文章每周都有压力,每周的读诗都是新的历险。即使烂熟于心的诗,要说给别人听,如同要写一个很亲密的人,你会忽然不知从何说起。诗不可说,说不可说的,怎么办?只能旁敲侧击、点到为止。
哪里有挑战,哪里就有惊喜。每期读诗,读每首诗,在写文章时,总会有新发现。哪怕读了一百遍,下笔的时候,时有想不到的灵光一闪。和创作同样,读诗对于我来说,也是跟随语言的一场探险。带着自己的情感、经验、个性、心智和想象开启一首诗,我对即将出现在笔下的文字满怀期待。诗句的存在超出其含义,其奥妙部分在抵达之前,大多是未知的,不能心急,得等它们自愿现身。
一般周三全天写稿,为了留有余裕,我会在周二想好如何导读,即为什么本期要读这些诗。周二晚上,把本期选的几首诗读两遍,看看有什么想法跑出来,记下关键词,然后睡觉,交给潜意识去运作。不知大家怎么看,我觉得潜意识里有一个真人,那个人从不睡觉。此法颇奏效,第二天工作时,就会有新的发现。每篇文章能有几段令我惊讶,至少有几句这样的文字,我就稍稍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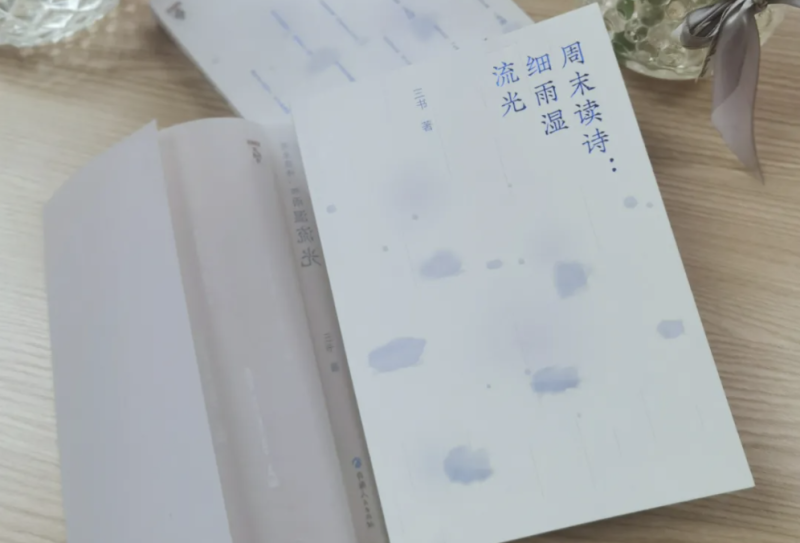
记得早期在评论区有一条留言,某位读者很好奇这篇文章写了多久,说自己读完总共花了二十二分钟。我不知道这位读者是不是觉得读了很长时间,还是说文章写得很认真,可能二十二分钟对于公众号阅读算很长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我的确写了很久,差不多在电脑面前边想边写七八个小时吧。有时为了核对一个细节,可能得花一两个小时查资料。我不是为了快餐阅读而写,至少这些诗大家得读慢点。
其次,和写诗一样,功夫在诗外。我很喜欢每周一篇的节奏,既可以保持写作的状态,又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和酝酿。一天一篇攒出一本书,只要全力以赴,完全可能,尤其是散文和阅读笔记之类。但读诗还是慢些好,我自己整个一周的阅读、所闻所思、所写的零散文字,都可能以某种方式滋养并进入这周的读诗。
每周六,我会期待看到编辑最后定了什么标题,配了什么画。取个好的标题很不容易,既要准确把握文章的核心,还得“戳中”读者的兴趣点,这方面我做得不好,我的原配标题绝大多数都被编辑换掉了。编辑为文章用心配的画,是我每周欣赏的重点,这些画为诗文增色不少。
亲爱的读者,感谢你们近两年来的陪伴,没有你们的阅读,就不会有这么多期的文章,更不会有这么顺利的出版因缘。每期的读者留言,我都会认真看,一一点赞。所有的读者反馈,对于我都很珍贵,我很好奇你们对这些诗和文章是什么感觉。很抱歉,我对留言回复得比较少,主要因为操作不太方便,又不想每次麻烦编辑代劳,我是很乐意和大家交流的。我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我们其实是在一起发现并激活这些诗,这些诗需要活在我们身上。
感恩一切!
新书刚刚出版,今天又是“周末读诗”2021年最后一期,我们的编辑和三书做了一次对谈,回顾了栏目的写作旅程,聊了聊她读诗的经验和方法,语音聊天最大的发现是:三书不仅极其爱诗,还爱笑。
对谈
唐诗好像是我心中的家园
新京报:我们“周末读诗”栏目的读者经常留言要求出书,现在书终于出来了,你有什么感想吗?这应该是你的第一本书吧。
三书:是的,这是第一本阅读笔记,挺感恩的。去年你开始跟我约稿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这些。(不过)一直想写一些读诗的阅读笔记。我比较喜欢我们古代文人那种即兴的(评论),比如金圣叹,感觉他们的评论更直觉、更即兴,不需要一套什么理论系统支持。本来我们读诗就是直觉的、即兴的、感性的。
我一直认为古诗词挺现代的。现代人和古代人在生活经验上肯定不一样,但我读唐诗,越读越觉得现代。以前上学时没有觉得。那时候我的心并没有敞开,因为你在一套那样的教学体系下,自己的心灵深度也还不够,所以没看出来。现在我也经常听到一些讲现代诗歌的人,说古诗比较简单,我觉得他们说的“简单”可能和我以前的感觉一样,他可能只是从字面意思上、甚至包括意义上觉得古诗比较简单,我却觉得古诗是以一种简单抵达了某种深度,就是万物的在场。
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派会有那么大的启示,甚至形成现代诗歌中的一个流派,就是庞德以他的天才读懂了古诗词,(能看出)这就是艺术啊。把意象并列在这儿,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真正的感受,我们平时感受东西就是这样,通过意象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感受一切。我们生命真正的感受就是直觉式的,而不是要从中理出个“意思”,这“意思”很简单,但我们的唐诗宋词(的重点)不在于那些“意思”。古典诗歌真正的艺术和我们的现代经验是共通的,我们应该从那里借力借光,这要求你先要感觉到它的现代性。我也不知道这些阅读笔记有没有做到,但这是写作的初衷和方向。我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让大家感觉到古典诗歌其实并不简单,也不属于古代,而就在当下。
新京报:读诗栏目的读者留言也是很大的看点。你对古诗词的阅读分享引发了不少读者内心诗意的共鸣或联想,很多留言写得也很好,很真挚,也很有诗情。
三书:我蛮感动的。写这样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和读者交流。我写东西不是在发表什么观点。我就是一个读者,这些诗怎样美、怎样让我觉得感动、触发了我怎样的体验,我们的读者在读了我的这些体验文字后,在他们身上也引发出感触或回忆,或者某一段文字、某一首诗留在了读者心里,这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
我现在比较关注“能量”,现在的确觉得所有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在能量的层面上运作。就我自己说,不管是读古诗还是现代诗,或者别的文字,这些文字不只是传达“意义”,它本身就以能量的方式在滋养我。
我们经常会把事情分成什么是虚幻的、什么是真实的,(会觉得)文字给了你一种虚幻的体验,其实这种体验并不虚幻。怎么能说自己的体验是虚幻的呢?你在诗歌里体验到某些事物、名词,它就已经把你和这些事物联系在一起了,那些事物的能量就已经传递到你身上了。我们从小被教育或被灌输的那些信念,比如想象的东西就是虚幻的,梦就是虚幻的,所谓的现实就是我们五官真正接触到的一切。其实所有的体验都是真的。我读古诗词,古诗词就已经在滋养我的生命,就已经是我的生命,而且在发生一种交流。再把这些写出来,读者读了以后有留言反馈,我再反馈给读者,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所有发生在心灵层面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就像《金刚经》里说的,能以量计算的福德都非福德性,真正的福德是无法用量来估计的。所以我觉得哪怕只一个读者,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他/她觉得被安慰,或者这些文字让他/她觉得不那么孤单,这个力量就已经很大了。
新京报:有时候过了糟糕的一天,晚上翻看两首诗,好像整个人就好一点了。
三书:对,它在能量的层面给你力量,也会净化我们内心的噪音。你会感觉你和你自己在一起,你和你的灵魂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时候人是最幸福,会感到一种被修复、完满的感觉。我们在外面三维的世界,尤其是这些年,大家可能都是破碎的,有创伤,文学在这方面确实扮演着治愈(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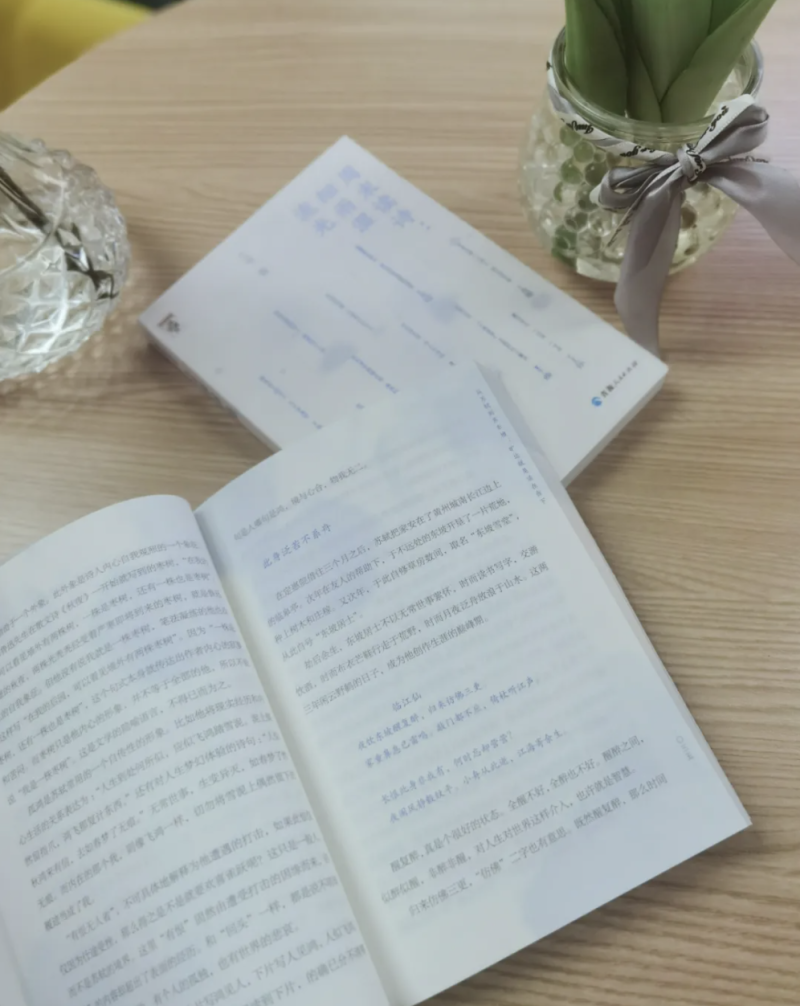
新京报:现在栏目已经更新八十多期,回头看来是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每期都是早早来稿,而且保障这样的质量和频率,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你在总结里也说有压力。在写作层面,有没有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
三书:这个问题我预料到了。我从来不拖稿,这是我最大的优点(笑)。如果我认定做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但平时生活中是个很拖沓的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能找到某一件这样的事,你觉得特别有意义,可以让你全力以赴的事。说到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其实每周一期这个节奏是比较轻松的,但在写的时候都有压力,因为这些诗很熟悉,但真的要下笔时,你要写什么?这时你面对的依然是很大的未知,但未知恰恰是好事。假如你已经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别人应该也知道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理念。这种未知产生的压力是好事,每次写的时候就在想我要说出什么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惊喜的东西。这是一种特别神秘的体验。
其实也有那么一个阶段,应该是咱们大概到四五十期的时候,的确有那么两三周,觉得我有点被掏空了。怎么办?当时想:要不要停,要不要停?但我特别感激,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量,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唐诗三百首》集中性地(分享)?
刚开始那四五十期基本是即兴的,我以前抄诗的时候会想某几首可以放到一起,因为觉得它们之间好像会有一种回声或者互文感。后来我就想,《唐诗三百首》我不是一直在读吗,我跑步的时候也会听,《唐诗三百首》这么流行的选本,真正读进去的有多少人?我就以这个选本为主(写文章),或许也有意思。不知道那个声音怎么来的,突然就想到了,所以又继续下去,感觉元气满满,能量又被创造出来了。我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有时候我甚至想,也许是古代的那些诗,或者说汉语本身的灵魂,或者古代的那些诗人,在以某种方式给我力量。
还有一点顺便说一下,我一直觉得我们对古代诗人有一个误解,总觉得古代诗人就是古代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挺好笑的提法,比如李白爷爷,或者几百周年(纪念)。这是对时间的非常狭隘的理解。他们并不古老,他们非常年轻,他们就活在我们的DNA里。其实所有的人类记忆从来都没有消失,包括动植物、山河、大地、季节,文化语言更不用说了。我们就是所有人。他们只是物质身体消失了,但那些记忆还以各种方式存在着。我读《诗经》时,一读就觉得我认识这些人,很熟悉的感觉。第一次触动我的不是《关雎》也不是《蒹葭》这样很美的诗,是《简兮》,写的是一个男性舞者在那里击鼓,我突然觉得这个形象我见过,无法解释,可能就是DNA被激活了,自己好像回到了那个场景。
新京报:说到《简兮》的形象,联系到你的阅读笔记,这些文章最动人的部分之一就是用文字激活了古诗中的那些场景,乍一看差不多的诗句,成为鲜活生动的、独特的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要怎么样才能激活这些诗句里的场景?
三书:这里“激活”是关键词。我们平时觉得某首诗文字很美,认为自己理解了,其实这是在大脑层面去看的,而并没有(进)到你真正的生命里,就像我们大脑层面懂了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笑)。道理明白了,可你的生命模式还是原来那样,你看到一件事情,反应还是原来那样。
新京报: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三书: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激活方式,像密码一样。你可能走的是后门或侧门,这些都可以,只要你进入(诗歌)了就行。(进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你甚至就变成了那个诗人,你就在那儿。
新京报:是不是可以这么形容,你站在了诗歌内部,以一种沉浸的方式体验其中的意象和情感,抬眼就看到了诗人所看到的东西。
三书:是这样。进入内部不是从“意思”上,而是从身体的感官上进入。得用感官去读诗,而不是用大脑读。诗人多多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诗是用词语写的,不是用情感写的。我们首先用感官直接去感受某个词以及它所指向的事物,然后去听这个词的声音。这个声音就像音乐,有很多个维度,包括声音的色彩、声音的强弱、声音的高度甚至它的亮度,包括词和词之间的节奏,这些才是诗歌的本质,才是唤起我们感觉的东西。
新京报:分享了这么多首诗、这么多诗人,你个人有没有特别偏爱的某个诗人?
三书:你有没有看出来是谁?(笑)
新京报:感觉偏向不是特别明显。杜甫算不算一个?
三书:其实也没有给某一个诗人更多偏爱,我更多的是从诗本身去选择。我爱所有的诗人。
新京报:博爱。
三书:对,博爱。诗人都很可贵,都是精灵。当学生的时候很喜欢李白,这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经验,现在他已经从我的偶像神坛上跌下来了。李白是个语言天才,读他的诗会觉得语感特别舒服,杜甫诗中人性的内容会更多。我也挺喜欢柳宗元的。
新京报:喜欢他诗文的哪点呢?
三书:他的文风比较的冷峭,是我比较偏爱的一种文风。我读了他的全集,他的游记很好,思想很独立,包括他评价上古的一些书,很有自己的见解。
新京报:如果回想一下自己的读诗经历,你是刚接触就喜欢上了古诗词,还是遇到了某种特殊体验,突然发现了古诗词的美?
三书:是突然发现的。我想可能很少有人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喜欢古诗词,而是需要一个自己发现的过程。真正能说“喜欢”,应该是研究生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是自己在读,而不是按照那些诗人被介绍给我们的方式去读。我会觉得,古诗就这样吗?表达了什么什么情感,闺愁、怀才不遇、伤春悲秋这些,让人觉得千篇一律。发现(古诗的伟大)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读博时是到现在为止我生命中非常幸福的一段体验,可以坐在图书馆的大木桌边,就在那几排古代书籍的书架旁边,外面有阳光和白杨树,看得到光影的流动,读着那些书,那样的时光很美,一坐一整天。像时光穿梭一样,那些文字会把你带到另一个平行时空,你会觉得那里的一切都特别生动。嗯,很幸福。
新京报:现在在国外生活,读古诗词会有特别的感受吗?
三书:一开始我会觉得读古诗真的好幸福,但一出去我会想,我们的汉语诗歌,对这些(外国)人、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好像什么都不意味。这也让我反思语言到底是什么,确实让我有一种巴别塔的感觉。但同时古诗词也给了我最大的安慰,它就是你可以携带的故乡。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读《庄子》和《牡丹亭》,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就不那么想家了,它们就是我的故乡。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那么美的世界,我可以随时进去,觉得特别幸福。
新京报:我们平时聊天时,你不止一次说到诗关别才,读诗需要别才吗?
三书:我觉得……写诗需要别才,读诗不关别才。我们都有这个能力。兰波那句话是对的,“在原型意义上,人人都是诗人”。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是人人都有诗心,人人都可以读诗。能感觉到诗的人,都可以被定义为诗人。不一定要写诗,人人都写诗也挺可怕的,但人人都读诗是必要的。读诗就是回到原型意义上的你,人只有作为原型意义上的自己存在才是幸福的,你会感到一种非常自在、圆满的感觉。平时我们被各种身份、标签、信念所限制,所以不管取得什么成绩,你也总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我还有一个经验,以前上课时,为了让学生不觉得古诗和我们没关系,在上课一开始的十分钟我会给他们念一首现代诗(我也很喜欢现代诗),我刚念第一句就感觉到整个教室的那种寂静,能感到(教室里的)每个生命都在特别专注地聆听,那种感觉太好了。这就有点像调频,把他们的能量的频率通过他们感觉更亲近的现代诗调到某种高度,然后带着这频率再进入古诗,他们就不会对古诗有抵触了。
新京报:这种在教室里学生们安静听诗的场景,其实也是很难得的场景。
三书:其实学生都是很渴望这些感受的,去真正聆听灵魂的声音。诗歌是一种灵魂的声音,它一发出来你就能感到不一样。
新京报:上周的读诗内容中,有一句话也很动人,讲冯延巳的《醉花间》“池边梅自早”一句,说“池边梅自早,人似乎总是迟一步,似乎永远没有准备好”。这种由古诗词引发的感触是很私人的,因此很动人。这种被古诗词引发的感触是对古诗词本身内容的灵感式反馈,还是生命经验的积累,或者二者兼有?
三书:肯定是来自生命经验的积累。老实说,我以前读这句的时候也没有把它和我的生命体验联系起来,写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啊,不就是这样的吗?我突然觉得,冯延巳,我懂你了(笑)。池边梅自早,不只是说梅花已经早早地开了,春天还没有来,可是你看,梅花已经开了,我们人的反应总是迟了一步啊,好像我们永远都没有准备好。我没有准备好,怎么春天就来了呢?这也是写作时的一个惊喜。在写的时候,你的频率已经在调整,已经进入某种生命状态,这句话突然就打开了,明明白白。诗歌需要用我们的生命经验去打开,这个打开不是通过理性思维的分析,而是一种观照。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以前那些大师说,你到了某种程度你自然就会懂。我想,你把它讲明白,我们不就懂了吗?其实就算别人讲明白,如果你生命中没有那些东西,你依然不会懂,你认为的懂,只是你的大脑了解了,并不是真的懂。我现在读《庄子》,觉得所有的文字明明白白,以前我觉得自己懂了,其实并没有。现在包括他文章里没有说的东西,都清清楚楚地被听到了。
新京报:按照这个标准,读“懂”古诗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关于古诗词,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读原文会觉得是好诗,翻译成白话就绝对不是诗了。问题在于,古诗词的诗意蕴藏在哪里?
三书:这个问题太玄妙了,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诗不是那些意思,因为用白话翻译出来也是原诗句的意思。这也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读书的时候不要只去说那是什么意思。诗是用语言写的,翻译后把诗原本的语言都毁掉了,还到哪里去找诗呢。为什么要翻译?如果不懂一首诗,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复读,或者说先生成自己的感受,再去看一些别人的讲解,别人的讲解只是辅助性的,得先有自己的感受。
有些人读不懂古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典故不熟悉。我觉得看一些简单的注释就可以了。典故方面的积累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形成比较扎实的积累,就是拿一本比如说《李太白全集》,清代王琦的注,每一个典故、名物王琦在诗的后面都会引用,但他的引用不烦琐,把这样一本书仔细读下来,包括注释都仔细读,如果能这样读几遍,你对典故就很熟悉了。这方法看上去好像很笨,其实是很快的积累方式,我们总是想速成,其实东晃一下、西晃一下,什么也留不下。
新京报:现在有些平台上关于古诗词的音频、视频点击量都挺高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三书:我觉得有些是刻板、教条的讲解,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听?后来想一想,这也不是坏事,说明大家有这个需求。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现代生活让我们感觉失去了根,失去了家园,这种漂泊感、碎片感,对家园的渴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自己读唐诗也是这样的感觉,唐诗好像是我心中的家园。
新京报:最后一个小问题。记得之前有读者留言问过类似“三书是谁”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三书:这至少说明读者对文章感兴趣,才会对作者感兴趣。我也并不是故弄玄虚,但我的确有一点想把自己隐藏起来。我很愿意和读者面对面、像朋友一样聊一聊古诗词,但在没有到那个阶段之前,我觉得作者最好隐去,不要知道他/她是谁,这样就能非常纯粹地、不带任何预设或偏见地读文字。这有一点像佛法上说的,依法不依人。现在很多时候是相反的,依人不依法。这个人头衔很高、名气很大,闪耀着各种光环,我们听的时候就都不敢对他有什么质疑。
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专业读者。记得有一次回复过一个读者,说我也只是一个读者,和你一样。其实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真心话。不要把我当成一个专业的文学阅读者或研究者。说老实话,我到现在都不会自我介绍,真的不会。就觉得很奇怪,每次写简历,每次都是那些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们人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丰富的生命存在,是多维度的。名字叫什么、生于哪里、上什么大学,这些都是标签,标签能构成你吗?你一旦说了这些标签,别人就会用这些标签拼贴出一个人,这样读者就很难真正地感受你了。
自述|三书
采写|张进
编辑|吕婉婷、张进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