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把父亲的存世哲学课程讲稿结集成书,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丘成桐谈《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的谈话录音整理,其中丘成桐介绍了父亲的教育对自己一生的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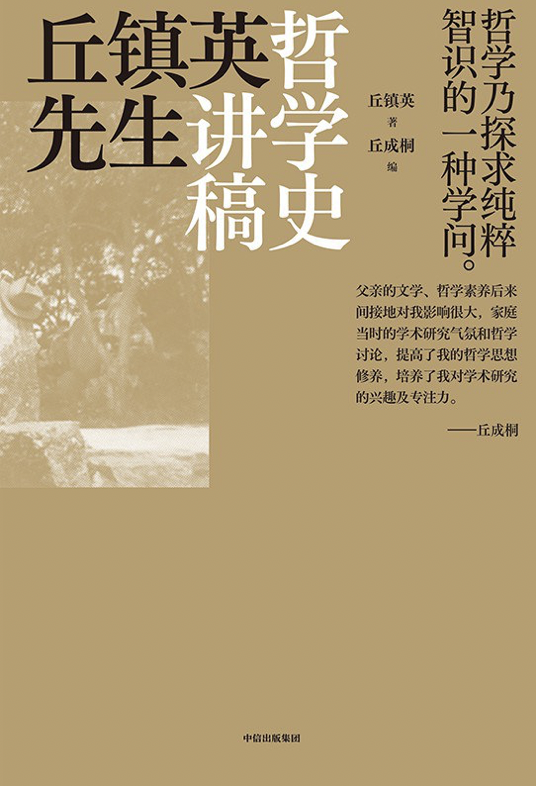
《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丘镇英 著/丘成桐 编,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
今天很高兴来讲讲关于我父亲遗稿出版的事情。我父亲丘镇英先生,他从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香江书院——的教授,他花了很多工夫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他对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重要的研究心得。原计划在1963年发表的,叫《中国哲学史》。但当时他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所以这书没有发表。但是他发表了一本书,叫《西洋哲学史》。当时的香港环境不好,所以这本书的发表并没有太多人晓得。到今天,已经过了六十年,很运气的,中信出版社花了很多工夫,将这本书重新编辑整理,花了不少的人力跟物力,将它安排好,重新整理,编出一本很漂亮、很整齐的书。我父亲故去已经有六十年了,我身为后辈,这本书的出版让我感觉很兴奋,看到我父亲这么重要的想法能够印出来,给普罗大众看看当初他做研究的一些心得。

丘成桐,当代具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美国国家科学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大奖。他成功解决了许多著名的数学难题,其研究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扑学、代数几何、广义相对论等数学和物理领域。
生活艰难,始终不忘学问
我父亲是很爱国的,他从前在厦门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政治经济学,也在日本学了很多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他通过日本的翻译,学了很多西方的哲学思想。很多海外的——无论是德国、法国、英国跟美国——重要的书籍,是通过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学习的。我父亲回国以后,主要的时间在抗战,因为他毕业的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他花了很多工夫在中国南部,宣传抗战的思想。抗战胜利之后,我父亲就在汕头住下来,管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发放救济的任务。我父亲很廉洁,他没拿过任何好处,但年终的奖金很多,因此家庭就比较好一点,也因此花很多时间在对哲学思想的研究。
1949年,我刚出生。我们家就从汕头到了香港,我在香港长大,当时也很辛苦,因为我父亲在香港刚开始没有职业。从汕头带了一些积蓄过来,但是他不晓得怎么经营,刚开始开了一个农场,两年后,农场全部垮台,所以基本上将他从汕头带的钱全部用光了。所以我父亲就到香港几个重要的学院去上课来维持生活。因为我父亲不懂得讲英文,所以进不了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培养殖民地官员的大学,讲的都是英文,不能够接受任何不讲英文的老师。所以,当时在香港的很多有名的学者都没有办法到香港大学去做教授,包括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很多当时国内很出名的大学者,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到了香港过得都很辛苦,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父亲在当时的崇基书院、香江书院、联合书院都做过教授,但是当时的薪水很低,用小时来计算,教多少小时拿多少钱。所以在50年代初期,我们家过得很辛苦,靠我父亲那一点钱不够维持全家的生活,我母亲也帮忙维持一家十口的生活。我父母之外,我们全家有八个兄弟姊妹,那个年代我们过得很辛苦。父亲想尽办法维持我们八个兄弟姊妹的吃饭和上学,但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父亲还在不停地想,中国以后的走向,从哲学的观念来看,他认为中国孔孟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要从西方的观点来比较,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什么这么好。所以他花了很多工夫研究西方哲学。他从希腊人的哲学一路研究到了康德、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他最后的期望是能够找到东西方融合的思想,这是他的志愿。所以不单是欧洲的哲学思想,他也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到了中国以后它跟儒家思想的融合的种种情形。所以他花了不少工夫研究西方跟印度、跟中国三个哲学流派的相互交流、影响,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志愿——希望能通过三个哲学流派找出对中国、对世界文明都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他思考得很深,我们小时候看到父亲花很多工夫去看书、思考,也跟很多当时他的学生讨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每个礼拜总有两天以上,家里都会来一大批他的学生跟他讨论学问上的问题,无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还是印度的哲学,也讨论西方历史、中国古代历史、中国近代史,还有印度历史。这些讨论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家里很小,家里只有一个客厅,放了父亲的书桌,这个桌子给我们几兄弟念书,所以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会看到我父亲在写文章,有时候也跟他的学生讨论学问。所以我们一路念书,一路听他跟他的学生讨论哲学的思想。那时候我年纪很小,从十岁开始,一直到14岁我父亲去世为止,我父亲写成了《西洋哲学史》。当时他每个礼拜都会跟学生讨论哲学的问题,我虽然不懂,但是讲多了以后慢慢会进到我的脑海里面去。

丘镇英怀抱丘成桐。
父亲的学问对我影响很大
哲学是能看得比较远的学问,是所有学问的提纲,也能够考虑一些比较抽象的思维,而不是很具体的应用的问题。所以从小我虽然对哲学不懂,但很习惯这种想法,能够用抽象思维想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我也比较了解什么是人生的目标。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父母从来没有要求我去赚大钱、做生意,或者做大官,权力很大,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是很重要。但是我父亲很期望我能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从他的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写《西洋哲学史》的时候,有两句话,最近被很多人引用,来自《文心雕龙•朱子篇》,讲人的一生时间有限,我们的身体总会腐化,但我们做的事要在死后能对后世产生影响。原句是:“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话是他人生的目标,“标心于万古之上”,就是要跟古代的哲学家有神交,懂得他们那些有深度的学问是如何产生的,然后我们能够将它消化;“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是讲学问要能流传下去,成为对后世有用的学问。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对我影响很大。这是在我十多岁时候父亲写文章所表达的一种重要的看法和人生的目标,所以我想做一些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不朽”。“送怀于千载之下”也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虽然我父亲并没有直接教导我哲学,但我也看了不少书,譬如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新原人》,也读唐君毅的书,但是对我讲其实是水过鸭背,就是看不懂。但是对我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父亲离开之后六十多年的今天,我还是能记得父亲当时对我的教导。
这几十年来,对真理的追求是我看得最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学好的学问,对学问的态度一定要严格,攀登学问的最高峰。至于其他的好处,名利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很想念我父亲当年对我的教训,尤其是过了几十年以后,我在学问上比从前进步了很大,也从科学的观念来学了一些哲学的思想,包括从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看法,都是一些哲学的思想,跟我父亲当年的一些看法,就是从希腊哲学家到康德,这些思想有一个比较,对我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
我做学问的观念
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父亲写这本书是哲学史,不是单讲某一个年代的哲学,而是通盘地考虑哲学思潮的一个看法。融合古今中外的思想,一同来讨论哲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所以我做学问也是同样的,我觉得做学问不能单看一个小问题,就算是考虑一个大问题,也不能单看一个小角落。就算是很出名的学者,也不能这样,我觉得一个学问要包含万有,能够海纳百川。能够将所有学问好的地方都融合在一起,让它能够产生碰撞的火花,才能成为大学问。所以我从研究生时代,做学问,我看问题的时候,就受到我父亲影响很大,我父亲要从希腊的哲学,希腊哲学包含了很多学派,有七八个哲学家不同的看法,基本上,所有的看法他们都有一定的初始的观念,这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研究数学的时候,我是做几何的,我研究几何问题,但我觉得除了几何以外,我还研究偏微分方程、物理……种种不同的学科,这些学科表面上看是不想关的学科。但事实上,深入地考虑的话,我觉得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从研究生开始就觉得,我做几何不能单做几何这一方面,也要包括种种其他的学问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这五十多年来走的路就是将这些学科融合。在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成名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从几何走到微分方程,走到分析的观念,将两个不同的学科融合,以后也跟数学物理融合在一起,一同解决很多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我做学问的看法,当然这种看法古人也有,但是,近代的发展是由我跟我的朋友带领完成的。现在,这个学科叫作几何分析,在数学界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丘镇英全家合影。
我一辈子很感激父亲
刚刚讲过,我父亲在的时候每周有两天,他的学生们会到家里来和他讨论学问,我父母会招待他们吃饭。受父亲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很喜欢邀请我的朋友或者学生到家里来一同讨论问题,所以我一辈子有很多朋友,他们对我来讲都很重要。从1973年开始,当时我博士后毕业才四年,我就开始带我第一个很好的学生Richard Schoen(孙理察),这个学生成为我一辈子的朋友,他跟我长期合作,到今天他已经是一个大数学家,拿了Wolf大奖。除了学生很多,我的朋友也很多,比如我的好朋友Leon Simon、Richard Hamilton、Karen Uhkenbeck以及Simon Donaldson,这些都是科学院的院士,一代大师。年轻的时候并不晓得他们会做院士,这是由于他们当年的成就,以后都成为几何分析的大家。几何分析这个领域本身就产生了七八个科学院的院士,可见数学界对这门学科的重视。
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研究几何分析这个项目的时候,刚开始跟鄭绍远跟孙理察、Leon Simon做的时候,慢慢就多了好几个大数学家进来,一个是Karen Uhkenbeck,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数学家,还 有Richard Hamilton,可以讲他们都是一代大师。我们在70年代创始这个学科的时候,融合了不同方面的学问进来,他们当中有些是在微分方程方面专业能力很强的,有些是几何专业、有些是数学物理,三个不同学科一同进来,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终于我们完成了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这些看法解决了一大批数学上重要的难题,到了1976年,解决了卡拉比猜想的时候,用了同样的走向,引起了全世界数学家的注意。对我来讲这些是很重要的,种种的做法,我要感谢父亲写这本书的时候,让我了解到学问的思想是不能够孤立在某一个地方,应当包容、合并,能够接纳不同的想法。最要紧的是走一个求真、求美的思想,而不是为了名利,为了种种其他理由做学问。我一辈子很感激父亲教我的这些道理,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为了名利做学问,是做不好学问的。求真、求美去做学问很舒服,但是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和不满。父亲的教导我始终没有忘记,在这个原则下做学问我是非常愉快的。
我父亲到临终都不得志,这本书他写得很好,有很多自己的创见,尤其关于东西文明的看法,到现在看都是很有创意的想法,很遗憾他英年早逝。父亲始终坚持自己,这一点让我很佩服。我想我比父亲幸运一些,我一辈子都在学习,从开始到现在,我向许多人学习,向年轻人学习,我也希望能带领年轻人共同前进。我看到父亲对年轻学生的培养,让我很佩服的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花了很多工夫培养这些年轻人。当时我们一家十口吃饭都不见得能维持,到后来解决了吃饭问题,小孩子的学费又成了问题。即便自己家里再困难,父亲也还是会拿出钱来帮助学生解决吃饭问题、支持学生学业上的进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忙有困难的学生,有时候甚至我母亲都不知道,这一点我是很感动的。现在这个时代,我比我父亲当年的能力大得多,但是我父亲在最穷苦的时候,还是会帮忙年轻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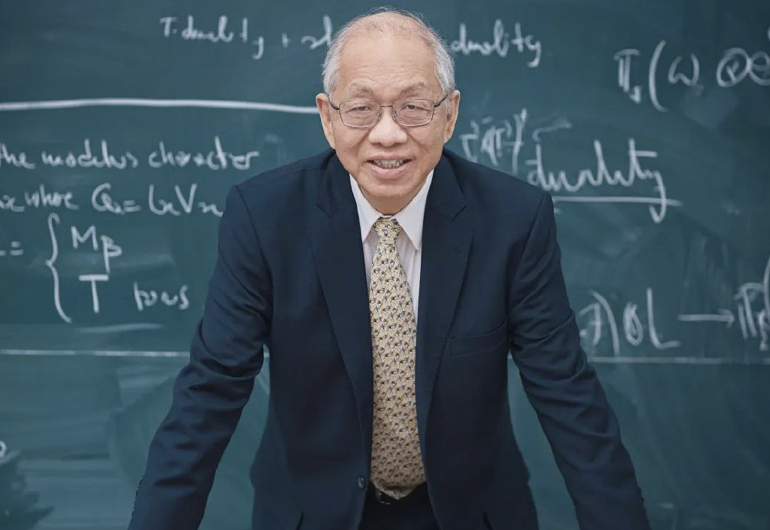
丘成桐。
中国的兴起要靠年轻人
所以我想,中国的兴起要靠年轻人,我也会尽量地帮忙年轻人。我不会让年轻人受苦,要让年轻人尽自己所能做好学问,中国才有前途,我父亲对中国的兴起看得很重要。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看法,书中从思想、从种种的观念来讲,与西方想比较,中国的兴起要走什么路。书中讲到中国传统思想,儒家的思想,有很多重要的想法,我父亲都看得很重要。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父亲在书中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儒家思想优胜的地方,他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看到东方文明的好处、缺点,也看到西方文明的缺点和好处。我们都希望看到东西方文明能够相互交融,这一点在我父亲写的一副对联里面有所体现,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门口写的:“崇高惟博雅”,崇高这个事情要博、雅,“无问东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要好好地学习。我在崇基书院念书三年,这两句话对我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每天走进校门,对联就对着我,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父亲写的对联。希望这样的包容性对年轻人,对国家的兴起产生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年轻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文明有深入的了解,我们不光是有钱、有军事,还要有千年文明支撑。所以我今天讲的关于《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很高兴,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一看,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从最深度的文明建立起影响我们国家千年的大计。
文/丘成桐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