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画像。

清末京师贡院考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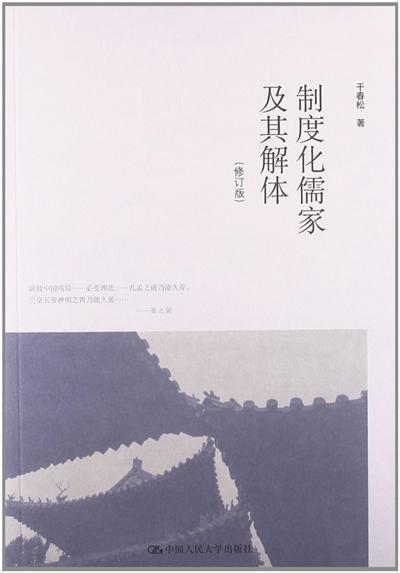
《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
作者:干春松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汉代初年,黄老道学流行。不过,要说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影响力,儒家是不遑多让的。只是,在统治者的眼里,儒家的方案因为过于理想主义和收效甚慢,所以不受待见。相比,法家那套比较注重实效的“耕战”策略取得了成功,秦国统一,建立郡县制国家。
但秦朝的速亡让统治者意识到建基于血缘的礼乐秩序对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在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教诲中,儒家开始了其漫长的对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和改造。
儒家在汉代之所以能取得优势的原因有多方面,在大的社会环境而言,汉承秦制,郡县制的垂直管理需要社会在各个断面的适度自治作为补充,因此,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组织正可以成为大一统国家中让郡县制有效运行的“毛细血管”。在这方面将儒家的伦理秩序制度化并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符合社会的需求。而董仲舒等人结合公羊学的原则,建构起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意识形态,既可以建立起大帝国所需要的超越世俗的合法性资源,又能为现实中的君主权力提供保障。由此,通过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建议被吸纳。
固然,在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并没有真正的“独尊”,但是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制度的确立,事实上使儒家获得了汉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的优势地位,并由此建构其儒生和政治权力之间的“通道”。对于儒学而言,其代价是难以再像孔孟儒学那样彻底的理想主义,而是与权力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合谋。这个时候,儒家已经是“于道为最高”。先秦时期的诸子争鸣的状况,转变为儒家吸纳诸家而独尊的局面。
自汉代到清代
儒学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双向互动
儒学的最基本的目标是“修己安人”,所以进行社会教化,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是其核心的使命。汉代以后,儒家对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虽然自汉代到清朝,历经一千多年,其中也经历过数次外族入主中原的事件,但儒家的价值却始终被历朝统治者所接受,而一般百姓也习焉不察,为人伦日用之常道。何以如此?
首先,从政治秩序方面:通过对自然状态和伦理秩序关系的建构,儒家以天道证成仁道,并由此来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因素。因此,奉天承运,既是自我标榜,也是自我要求。而儒家对于礼制的建构,也提供了国家秩序的符号系统的核心内容。尤其从博士制度、察举制度到隋以后的科举制度,儒家经典成为进入官员序列的重要途径,并借此确立了儒家教育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制度性通道。
其次,从地方秩序来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的形成,意味着社会的垂直管理体系的建立。但鉴于国土面积的广大和管理能力的限制,“天高皇帝远”,统治权力难以真正深入到社会最基础部分。如此,家族制度一直以来是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将之概括为“地方自治”。儒家伦理的基础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儒家的礼制就是通过对血缘的远近、长幼的区分来确立每个个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家族不仅是在自给自足社会中的基本生产单位、而且也担负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赈济的功能。而家训、族规以及祠堂、谱牒等作为家族制度的有机构成,也承担有维持地方秩序、推动道德风化的作用。
按照我的概括,自汉代到清代,儒家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儒家制度化”与“制度儒家化”的双向互动关系。所谓儒家的制度化就是儒家思想通过建立起经学博士和科举制度这样的方式保证了儒家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而制度的儒家化则是儒家的观念不断渗透到具体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法律制度中。他们之间的互相促进,则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价值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儒家虽然坚持道统对于政统的优先性原则,但在现实的政治权力的制约下,也呈现出与现实政治的妥协化趋势,由此构成了儒家理想中的民本思想和现实政治中的君本思想之间的紧张。儒家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作为民本思想的基础与皇帝、君主将天下视为一家之私产的矛盾的后果,多数情况下的结果是权力对于价值的压制,这经常导致儒家的理想成为统治者笼络人心的“幌子”。所以朱熹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儒家的王道理想无一日得行于天下。
清末民初
大变局之下失去制度依托
清朝末年,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格局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形成的时候,中国社会依然是处于农耕小农经济形态中,这种发展上的差异导致当资本的外溢波及中国的时候,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以殖民运动为依托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真正危机到来了。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直面西方的军事和经济的挑战,囿于对西方的了解程度,所以最初的反应是简单而直接的,就是试图通过洋务运动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甲午丧师,让我们认识到制度的变革比器物层面的模仿更为重要,逐渐地,改良和革命成为摆在知识群体面前的选择,最终更为激进的革命派推翻了帝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儒家遭受了什么样的挑战,并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晚清的儒家知识群体固然有极其保守的人士,但更多的人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依靠祖宗之成法难以应对西方的挑战。所以争论的焦点在于“全变”还是“调和”。这一时期,以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体西用”论风靡一时。张之洞努力想在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和西方的先进科技、管理“技艺”中寻求平衡,力争在维持纲常的前提下进行变革。这样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把张之洞看做是顽固分子是错误的,在20世纪初的新政过程中,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许多政治制度的变革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
其次,西方对于中国的冲击虽然是以军事和经济为前导,但他所摧毁的则是国人对于固有文明的信心,首当其冲的则是儒家的价值观。这一点上晚清公羊学的兴起,可以看做是儒家试图通过自身的逻辑化解文化冲突的最为惨烈的一次努力。
以廖平和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学家,特别是康有为通过托古改制的方式,将公羊三世改造为容纳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的历史哲学和制度发展阶段论,从而为中国接受民主、议会、宪政等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由、个人权力的价值观念提供基础。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新学伪经”,即对于经典系统内部分经典的价值进行否定,这种“打通后壁”的行为不但为纯正的西学派所不能接受,也遭到了经学体系内部不同经学谱系的人士的激烈反击。比如张之洞、比如章太炎。经学内部在西学的挑战面前,反而成为经学价值自我瓦解的触发点。
再次,儒学的危机还体现在其制度化的解体,儒家的观念逐渐从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剥离。最初的剥离是从教育制度开始的,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就是对以国子监为中心的传统官学体系的取代。而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儒家经典不再是中国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新的教育体系中,声光电化和外语成为核心课程,经学边缘化为“国故”。
日本学习西方成功所带来的是“立宪救国论”,意味着新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运行原则的引入。儒家所崇尚的纲常秩序遭到宪政所要求的平等、个人权利等因素的冲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晚清的法律变革中。对于父子同罪这样违背纲常秩序的新法律条文显然是张之洞等人所竭力要反对的。
最后,在资本主义影响下,城市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乡村破败。它们对家庭生产方式构成了打击,作为这种生产方式转变的后果,儒家的家庭伦理也遭到冲击,绅士群体从乡村社会中消失了。即便如此,在民国成立之后,经由新式教育而形成的新知识群体的主要批判点依然集中在“家族制度”。有人认为家是中国不平等的秩序的源头,也有人认为是难以建立起国家意识和公德意识的“罪魁”。
在这样的多重打击之下,儒家逐渐失去了招架之功,有人判定这些东西该被送去“博物馆,只是作为陈列品”。虽然儒家的伦理意识还是许多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主体,但失去了制度性依托的儒家,逐渐变成“游魂”。那么,儒家可能在未来的中国找到新的“肉身”吗?
【撰文】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儒家思想与典籍、近现代思想与人物、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出版有《制度儒学》《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等著作)。








